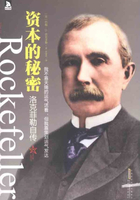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西班牙战争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当人们死去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死亡是正当的、重要的。他们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死,他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死。”
恩内斯特·海明威,1940年
西班牙内战使卡帕拿起致命武器——他的莱卡相机——在战壕里跟大家一起反抗极权主义的第一次机会。按照记者玛莎·格尔霍恩的话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希特勒作斗争,与纳粹作斗争,与所有希特勒的效仿者正在实践着的不道德思想作斗争的地方。(卡帕)并没有指望能够参加战斗,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摸过步枪。他指望自己能够拍摄一些照片,迫使大家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人们去为之战斗的。”
卡帕和格尔达刚刚听说弗朗哥暴动的消息,立即就决定应该两个人一起去西班牙。卡帕为人民阵线报道,这已经在同情共和党人的一些出版物内引起相当大的注意,比如《今夜》、《看到了》和《注视》。他猜想,找到去西班牙拍摄的任务估计不会太困难,因此很快与各处编辑联系。
《看到了》杂志的路西安·伏格尔同意派卡帕和格尔达两个人去西班牙。他将租用一架小飞机送他们去巴塞罗那,他本人也将同他们一起去:他准备为自己的杂志组织一期特别报道,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实情。卡帕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于8月初动身飞往西班牙,同行的还有格尔达、伏格尔和另外一些记者。那是一次不吉祥的开头。飞越比利牛斯山区以后,他们的飞机突然失去高度,结果在巴塞罗那郊外的一个田野里强行着陆,飞机撞得七零八落。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伤亡发生。卡帕和格尔达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两人惊恐万状,但竟然没有受伤。同时,在加的斯港以南约60英里处,纳粹装运的第一批飞机和士兵也登上西班牙国土。
8月5日,已经很晚了,卡帕和格尔达到达巴塞罗那郊外。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中心,气氛达到疯狂的程度,人们很快便忘记了飞机失事的震惊。在一条街上,卡帕和格尔达发现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伙伴,他们穿着蓝色的连衫裤工作服,一起欣赏午后的太阳。这些人兴高采烈,因为突然之间,巴塞罗那庄严的大楼和政府机构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众手里了。城里大部分的工厂主要么已经逃跑了,要么是跟共和党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大批杀害的数千修女、僧人和牧师一样遭逢了厄运。
1959年,德国作家居斯塔夫·雷格勒生动地描述了因反对弗朗哥而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的情形:“人们的内心有一个陶醉的想法,那是具有传染力的急切的献身精神,是对自由热血沸腾的信仰……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那些民兵也许会被法国革命推上街头,毫无疑问,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发生的暴力行为,有许多是由无意识地模仿无裤党这样的激进革命者而产生的。”
也许,卡帕在巴塞罗那最早的接触对象是约姆·米拉维特斯,他是左派艾斯格拉党的总书记,当时才28岁。米拉维特斯回忆,他帮助卡帕和格尔达获取在巴塞罗那拍摄的许可证以及正式的法国媒体通行证。他还清楚地记得,卡帕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而陶醉。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极权主义纲领,以颓废主义者的态度拒绝所有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规范和法律以及道德信条,在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卡帕只是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之中的一员,这些人还包括乔治·奥威尔和安德雷·马尔罗。对他们来说,西班牙内战是他们一生最感人的经历。对于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志愿来到西班牙反抗弗朗哥的其他年轻男女来说,那场战争还代表着针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斗的前线。如果弗朗哥在西班牙击败民主的阴谋得逞,那么,在世界别处狙击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战场的获胜希望就极其渺茫了。卡帕和格尔达之后去了一些银行和大宾馆,这些地方被一些反弗朗哥的活动者包围起来,这是令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组织CNTFAI建起了一些没有组织好的营地,散乱地围绕在卡尔拉耶塔那一带,而这个地方后来很快就更名为维亚杜里迪。托派POUM组织把基地建在猎鹰旅馆,那里离卡塔隆尼亚广场很近。在其中一个广场,卡帕和格尔达遇到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格尔达看到了很多角色模范,卡帕看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可供销售的故事。他正确地预测到,法国和英国的杂志一定会想办法拿到这些作战妇女的照片,她们如同象牙一样白净的面孔、长长的卷发以及时髦的新马裤。他们拍摄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兵,她坐在咖啡馆的石级上,正埋头看一本妇女杂志——一把枪从她双膝间露出来。
在巴塞罗那火车总站,卡帕和格尔达看到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军人,他们正准备赶赴北部地区,与阿拉贡前线的暴乱分子作斗争。他们拍摄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描写恋人们难分难舍的告别情景的,而是反映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告别家乡,要去粉碎弗朗哥臭名昭著的摩尔人集团的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一节车厢的侧面,有人用白色油漆写着这样的字:“看着这些友爱的字眼发誓,与其容忍暴政,不如速死。”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热情洋溢地挥舞着拳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巴塞罗那。
8月末,卡帕和格尔达驱车150英里到了离休艾斯卡最近的前线,这座小镇躲藏在比利牛斯山脚下,正好就在地中海与大西洋海岸的中间。但是,因为没有行动发生,而他们又急于拍到共和党人胜利的照片,因此就继续南下。他们得知,为POUM民兵工作的数百名德国共产党人就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在撒拉哥沙东北面的莱琴伦那,卡帕和格尔达很快找到了一个作战组,整个冬天,乔治·奥维尔一直就在这个组里,之后他受了伤,于1937年春天离开了西班牙,他感到失望,内心里体会到一种幻灭。
他们又失望了:这个小组全是些五花八门的杂烩士兵,其中大部分人戴的帽子都不合大小,手里拿的都是破枪,七零八落地斜躺在地上。但是,后来他们又得知,马德里的共和党政府已经下令,准备对弗朗哥的军队发动第一次重大进攻,就在科多瓦地区弗朗哥的追随者正在酝酿一场同族相残的恐怖战争。每当有一座城镇落入叛军手中,都会进行数十场当众行刑的枪杀活动。。9月初,他们出发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拍摄到实际的战斗,运气好的话,还会拍到法西斯的第一场失败。
途中,他们在托利多停靠。几个星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围困着城市中央著名的城堡。叛军上校莫斯卡多以及他的数百名跟随者抵抗住了对这个城堡无数次的进攻。当卡帕和格尔达到达的时候,他们得知,共和党人正准备用炸药炸开城门,但是,要把足够量的炸药埋到城墙下面,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这样,这两个人只好继续南下,朝科多瓦的方向接近。最后,在叫做塞罗墨里安诺的一个小村庄附近,这两个摄影者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战场。
9月5日清晨,法西斯分子轰炸塞罗墨里安诺。当天下午,卡帕和格尔达拍到了惊惶失措的人们逃离这个小城的几张照片。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叛军将领奎波德勒安诺的叫嚣,说他的人马很快便会到来,然后强奸这个村庄里的“女性赤化分子”。当天,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个地区,此人是德国作家弗兰茨·波克劳,他后来在他的著作《西班牙战场》中回忆说,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奔逃中,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在逃跑,有徒步的,有骑驴的,有开车的,有坐运货汽车的”。波克劳还惊愕地看到,有很多CNT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也像“懦夫一样”跟着逃跑。“面对炸弹和炮弹,步枪根本不顶用”,其中一些人这么喊叫。
波克劳进入塞罗墨里安诺村以后,发现万人空巷,门扉紧闭,无人照料的牲口在街上游荡。在前线,他发现“有三四个人”死掉了。当天下午,他看到更多人在逃跑,“只有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小规模民兵组,而阿尔科依是墨西亚省的古老的革命中心……他们挺住了轰炸……有让人自豪的勇敢精神和大无谓精神……但是,这里纪律松弛,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当天下午,有人认为,卡帕加入了前线的阿尔科依民兵小组,之后奇迹般地拍到了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倒下的士兵”。该照片描述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民兵被炮弹击中,倒地而亡之前的不到一秒钟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