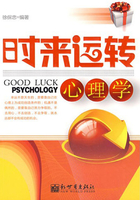教书先生颜真白天在学堂设坛讲学,晚上在自家炕头上打坐说古。学堂那件事是养家的营生,晚上的呢?是热闹。看别人的热闹,打发自己的人生。颜真却从未说破。
舍不得点灯熬油,颜先生端坐黑暗当中,他的听众密挨挨地和他一起拓展暗夜,浓烈的蛤蟆烟和不明的臭气交织,欺压着几点忽明忽暗的烟星儿。西北风刮得正猛,让人无法忽略,所以那一股超越狂风的悲号刚一响起就被众人听到了:啊……我的列祖列宗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空空空”……听众游离了颜真先生架构的时空,仔细辨析大墙的回声中,哪个声音是头的撞击,哪个是手的拍打。
颜先生停下了,等大家已经猜测出那哭声的来历,便咳嗽一声,高声说:这次讲个大家伙从来没听过的故事。
话说吉林陶赖昭有个吴家,穷,起先是佃户,租种杨家大院的地。这样的家没有闲人。老吴给杨家赶大车,老吴的三个儿子,吴一吴二吴三种地,老吴的老婆,吴老太在家喂猪、养鸡、伺候园子、收拾家务、做饭。老吴还有个闺女,傻,干不了细活儿,给杨家放牛。
有一天,傻丫头放完牛回家,进屋之后顺手“嘭嘭”扔炕上两个东西。吴老太一看,“妈呀”一声,是两个金元宝!吴老太一把抓住傻丫头,吓得声音都变了:“丫头,这东西哪来的?”
傻丫头说:“捡的,牛总乱跑,我拿黄土坷垃打它们,剩下两块,拿回家了。”
吴老太问:“哪儿捡的?”
傻丫头说:“就那儿呗,破玩意儿,还有一大锅呢。”
当晚,老吴向东家借了大车,谎称傻丫头病了,去瞧郎中,把丫头摁在车上,蒙上大被子就出了村子。出了村子,老吴驾马车,吴老太拥着傻丫头仔细询问,一路赶过山脚,来到一处他们从没有来过的地方。撇下车,他们小心地穿越一片老林,老两口就傻眼了:星光下,一个破败的城郭出现在眼前。
虽然到处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和高高矮矮的草,可是断壁残垣还是依稀可见。傻丫头来到了自己的领地,显得很兴奋,领着二老就去找盛黄土坷垃的大锅,指着它有些得意地说:“看,还说我傻不?我没瞎说,是一大锅!”
那一锅金元宝合该现世,暗夜也没奈何,它们闪闪发光,不可阻挡。
老吴和吴老太有如神助,胆量和力量倍增,一大锅的金元宝一个不差都运回车上,给它们捂上大被,一回头看到傻丫头顶着大锅从树林子里出来了,她还喊着:“妈,看我多有劲儿!”
老吴赶紧奔过去接住丫头的大锅,看看实在没处扔,又担心随便扔了不吉利,就一把扣在被子底下。
从此,吴家悄无声息地富了起来,好大的一个家业,好兴旺的人丁。不出几年已成有房有地的大户人家。等到吴十八当家,吴家的买卖已然遍及吉林,还开到了北京。
有些奇怪的是,傻丫头自从这个变故之后就更呆更傻了,没有找婆家,自然也没有子嗣,一直熬成白头发白眉毛的老姑奶奶。吴一吴二吴三临终的时候都着意嘱托了后人善待傻丫头,可是他们一撒手,哪管得了后面的事情。
傻丫头其实也并不多事,只有一样,就是对那口大锅情有独钟,每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当家的都安排妇女们烧一大锅热水,给傻丫头洗个澡。今年却没人张罗这件事。傻丫头那天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动静,她一趟趟去厢房一间闲置的房间看那口大锅。当时当家的是吴一的大孙子吴十八,明明知道老姑奶奶的心事,但是多有不耐烦,假装不知道。后来就听见一声巨响,大家纷纷朝着声音奔去,原来,那口大锅被老姑奶奶拿斧子砸碎了,真是难为她怎么弄碎的。
不管怎么说,大过年的,这种事到底让吴十八吃了一惊,感觉不舒服。他生气地大声问:“老太太,你这是干什么?!”
傻丫头自言自语:“完啦,这回是完啦。”
当夜,傻丫头无疾而终。
可是悄悄地,就像吴家突然富起来一样,又突然败落下来。而一旦败落,竟像瘫倒的大墙,“轰隆隆”来势汹汹。
等到吴三十六当家的时候,吴家的买卖终结了,房产和土地也失去过半,但依然是个大户。
传到吴四十,这孩子胸怀大志,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学最时髦的经济,准备振兴祖业。去去二年有余就打道回府,回来时,落魄不羁,更兼毒瘾深入骨髓,已然没了人形,那振兴家业的宏图大志也随大烟成灰了。转眼之间,如同瘦死的骆驼似的家业也不能继续支持,最后的七间卷棚滚脊式气派祖屋被迫卖给了别姓,吴四十把祖屋钱换成阿芙蓉过瘾。可怜那一表人才的吴四十啊,只有在月白之夜,掩了面子,伏在祖屋的墙上痛哭流涕了。
颜真口中“啧啧”有声,结束了故事,听众顿足颔首,听得很是动情。此时,屋外狂风又起波澜,吴四十的哭声被风送出高高低低缠缠绵绵的悲号,最后彻底隐匿于沉沉的黑夜当中。有个嘴边长着一圈细软绒毛的年轻人,公鸭着嗓子说:颜先生,为什么吴家不能守成,而杨家大院却能代代富贵相传呢?颜真大喝一声:问得好!我正想考考你们呢。要我说,一句话,来路不正!
颜先生舒了一口气说:你们品去吧!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那大风里捡来的,可不又被大风吹跑了嘛!何故之有呢?一开头就缺乏砥砺和磨炼,后辈们自然涵养不足,难以承继啊!
第二天起,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吴四十,谁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