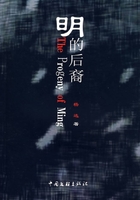平原,丘陵,这些词他们还不会说,他们说,这大荒地呀,那个大那个长哟,没完没了!寻思这辈子也走不完了呐,咬着牙走到头,就进了山了。他们说起这个眼泪汪汪,偏转了头,眯了眼,像是躲避什么。他们没有留在大荒地上。他们为什么不在大荒地上建一个肥沃的家呢?他们谁都不说。他们进山了,从此成了山里人。
隐去年代。
山里一个平常的夏天。正午。
贤明贤良兄弟俩呼呼大睡,轰隆隆鼻鼾,咯吱吱磨牙,塔头墩垒砌的小屋微微震颤。毒辣辣的阳光透过破窗户煎烤着他们,两张如盆大脸汪出一层油。苍蝇轮番扑上来开洋荤,洋荤开过,就两两一边去摞在一起,不动了。吊在大梁上的一串灰嘟噜,在又一阵突起的呼噜声中,终于忍熬不住,倏地坠地。
屋外一只芦花大母鸡,瞪着两只圆眼,伸长脖子,一边愣呆呆地转动着它那半粒稻壳般的红耳朵,一边慢而迟疑地向墙根移动。突然,它耷拉下两只翅膀,半蹲着“喔喔”叫着跑起来。
屋里,此起彼伏的鼾声磨牙声同时终止,贤明贤良兄弟俩睁开眼,对望了一下,支起上半身,向屋门望去。门打开了,一下推到最大,门的外边“咣当”一声抵在大墙上,回不去了。屋门大开,一个人进来了。
我找个人,走到你们这儿了。那人搓着手,坐在贤良让出来的地方。贤明下地,给那人舀来一碗凉水。来人接过,喝了,却并不急切。把碗放在炕沿上,他掏出怀中的长杆烟袋。
贤良问:老哥,哪儿来的呀?
外头。那人回道。
到哪儿去呢?
里头。那人的下巴向山谷方向扬了一下。
咋称呼老哥呢?
那人却莫名其妙地说:有点账算,找个人。
这人说话金贵。兄弟俩又对望了一眼,屋里忽然静下来。
贤明给他点上烟,那人重新把话头提起。
他问:你们是干啥营生的?
贤良说:采蘑菇,挖药材。
怪不得墙上没挂枪呐。那人来了这么一句话。
兄弟俩没吱声,不接话。那人于是说:山里有枪的人家,手里都攥着人命!
说完,不再言语,只顾大口抽烟,一会儿工夫,满屋烟雾。直到烟雾散尽,那人说:水也喝了,脚也歇了,我给你们讲个新鲜事儿就走人。
山里人烟稀少,消息闭塞,过路人常把一路见闻留在途中,以此答谢允许他们住宿、打尖、歇脚的人家。
他说:昨儿晚啊,有个老客,整了十斤大烟土,他寻思自己挺精——那人指指窗外,稍作停顿,一股微弱持久的轰鸣声远远传来。
听见没?他问贤明贤良兄弟俩,然后自顾自地说,就像这条河,水流急些,倒是不深,能蹚着走。老客要蹚着河水走到山外去。你们猜怎么着?来人并不等兄弟俩回答,只是看了看兄弟俩冷漠的面孔,继续说,他背着十斤大烟土。又重复道,像是赞同谁的话似的,就是扛着一座小金山嘛!这老客寻思他自己想得挺周全,不走山路,走水路。哈哈,算计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那人陡然停住了故事,转而问贤明贤良,昨晚是几?
贤良说:十六。
对呀,十六!那人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老客失算了,他寻思十六的月亮只成全他呢!一片水亮亮,好走呀!劫道的人埋伏在山路上啊,逮不着他呀!可是,他失算了,还有一步,这老客就出山了,我寻思着,这老客可能就要乐颠馅儿啦。
那人哈哈大笑,小屋马上哆嗦起来。他笑啊笑,突然就绷了脸,阴冷冷地说:“啪,啪,啪——”这三枪从树林里钻出来,那叫一个准,一下子就干碎了老客的脑袋瓜子!
贤良霍地一蹿要扑出去,贤明却一把将他按在炕上,他挡在贤良的前面,对峙立即发生了。贤明算是看清了这个不速之客的模样了,他们的眼睛都瞪到了最大,死物一样,连眨都不眨一下。苍蝇嗡嗡地在两个人之间来回飞舞,四只眼睛只想从对方那里强取豪夺些什么。
最终贤明挪开了眼睛,他爬到炕梢去,推开一堆杂物,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油布包袱。那人接过来,转身就走。
贤明贤良兄弟俩冲上去,重重摔上屋门,门后两支长枪倚墙而立,他们一人抓过一支,贤明却伸出手再次拦住贤良,低声说:就一个人,他也不敢。两人右手提枪卧倒,耳朵贴地,马上,踢踢踏踏的马蹄声传来,他们仔细辨识,踢踢踢……踏踏踏……兄弟俩脑门上全是汗,交换着他们的判断:
少说四匹马。
少说四个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阳光又从破窗户钻出去了,塔头墩垒砌的房子暗淡下来,兄弟俩坐在地上,呆若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