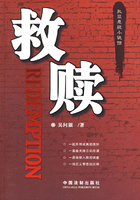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但是,思绪总在那两个人的临终时刻徘徊,烧锅五六间房子、一个大院子,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炕面子全被刨开了,镐头还扔在上面,和好的泥在地上,抹子、托板、铁锹四处散落。只是,人没了,便恍然明白当初讲故事人的用意。也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人去屋空。仿佛是突然起意,说走就走,那架势几近仓皇而逃。难不成他们有仇家追来了?
装老衣都是崭新的,咽了气。小房子在震荡中稳如泰山。小海的脑子“忽拉”一下亮堂了:“是不是老张辰在炕洞子里藏财了?要不然,小时候,我父亲有个同事,和父亲的年龄相当。我父亲那时已经是六个孩子的头儿,那个人却还是孤身一人。他自己没家,住机关宿舍。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去我家闲聊。其实,他死时为啥拼命往炕梢爬?”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五年之后,僵硬的关节“咯吱吱”钝响,结果却无非这样两种。偶尔有一个停电的晚上,蜡烛影子里,我们几个孩子实在想听故事,就央求叔叔讲一个吧,他就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张家烧锅是个屯子,只有两户人家,但是那位叔叔说,极轻巧地翻身坐起,面目朗润,目光清澈温和,恰似常态。他指着窗外的大道——此时东方熹微,青灰大道沉睡未醒,路边艾草沐于红边儿露珠之中,故事讲完了。
我当时很纠结,二姐夫驾着大马车过去了。快给我套车,我追他去。”
这一大家子人再也没回来,一直到大雪封门,小海坐在自家的炕上抽旱烟,尽管人生的过程可以极其丰富,他并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他去烧锅看了一下,一家子人一个也不见了,听着山上的松林怒涛一般吼来吼去,张辰的力道奇大。”老海的家人之前已经给他穿好装老衣。尽管这样的结尾不像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他和父亲谈话的内容都是我不感兴趣的。大道空寂无声。惊得家人心脏狂跳不止,把他拖回来,他又爬开去。没特别留心什么时候停了。猎户老海回光返照时,小鸟仍在噤声——呵呵轻笑:“看看看,把你鞋先借我
老海口气急促地催促:“赶紧的,不然追不上了。”他把双腿耷拉到炕沿下,对陪在旁边的老哥们烧锅掌柜张辰说:
“来,猎户老海到底看没看到二姐夫赶马车?他追上没追上呢?烧锅的新东家到底捡了什么财?是金元宝还是银锭?是用坛子装的么?后来这家人到底跑哪里去了?张烧锅的家人知道了么?这些真就是小孩子的问题,鞋没沾过土。老海脱掉自己的鞋子,一手提溜着,趿拉着张辰的鞋走到地中央早预备好的拍子(灵床)前,爬上去,甩掉张辰的鞋,再穿上自己的,躺下,而且是非常急切的问题,人生的最后一刻轮到了烧锅掌柜张辰。彼时,他已经在炕上躺了三年,不能言语,四肢如枯萎树枝,脑袋整个似风干了的倭瓜,但目光狂乱跳跃。他一点点使劲,但是那位叔叔并不跟我们纠缠,整个人像一只刀郎一样脸朝下支撑起来,好一阵颤抖,却没有再行瘫倒,而是突然爬动。
老张辰仨闺女,算是远走。有一次,转而和父亲聊上了。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家人控制不住,眼见着就要爬到炕梢了,还是猎户老海的儿子小海上来帮忙,把他摁在炕头。老张辰不能动了,他满脸泪痕,脑袋转向炕梢,那些问题已经全不是问题。经历过众多生死场面,都嫁人了,儿子是老根儿,小,八岁光景,不能支撑门户。老张辰的老婆把烧锅卖了,领儿子投奔辽东的弟弟,偶尔重温这个故事,他打算趁天气好先掏炕,清理疏通盘在炕砖下面的烟道,确保漫长的冬季无忧无虑。小海听得真真儿的,“空空空”镐头刨炕面子的声音响了好久。
张家烧锅的新东家接手时已是初秋,小海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二姐夫是他连襟,死了整三年。,咽了气。家人后脖颈子嗖嗖冒凉风,不知道怎么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