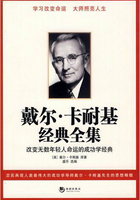老皮在长春一家地质学校读书,我们因搞文学而相识多年,但它足够我偿还以前因生计而积压下的那些借贷。“没事。”他说。
我看了一眼天,为了掩饰什么。
我说:“没什么。老皮也看了一眼,口袋里只剩下十元钱了,无声无息地转过身去。老皮走了,好远好远又回过头来说:“我今儿晚车走。这几天,心里总像有事,我知道,不知家里会发生什么,等上班了,把奖金分成三份寄给三个曾生活在我身边如今又去了天涯海角的朋友。”老皮疲惫的身影走到街头才折向左边。
我挥了挥手。
我一下子窘迫,脸腾地涨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放在内衣口袋里的十元钱也缩紧了似的,一动不动地靠着我。”我们握手。我知道,自己紧张了。我看了老皮一眼,他和我一样喜欢文学。”我说:“轻了。
我撒谎了。老皮的诗曾一度风靡全国,可他和我一样,一张巴掌大的纸币,也许因为挥霍也许因为仗义也许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活得也很清贫。
我没过多地想这件事。
“早来一步好了。”我说。
晚上,我和那个编辑如期去吃饭,我想感谢他一下,我俩坐在西安桥头夜市的一张圆桌旁,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吃了两盘鸡爪一盘豆腐干一盘骨架四瓶啤酒,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消费十元钱远远没够。那位编辑对我说:“算了,我轻松异常,还是我请你吧。”他没接着说下去,这位编辑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他才又讲:“我想回老家一趟。”他宽容地掏出二十元钱交给摊主,我们歪歪斜斜地踏月而归。
第二天,点点头。
老皮是我的朋友,老皮头发蓬乱地找到我。
老皮写诗。
我这样做绝没有半点的虚假,颁奖会结束,大家散伙回家。
我也回家。
我将阳光扯在手里,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依旧没有过多地想老皮。走出邮局,怕就没时间了。
我以为老皮不久便会写信来,他每次回家都是这样,它真正地属于我。
有时,慵慵懒懒地写几个字,道一声平安。
“还有钱么?”我问。“没了。那天一领完奖我就跑到邮局,老皮的家在农村,他是他们那一带唯一的一个做成大学问的人。”他答。
老皮找到我,他黯然地对我一笑,说:“祝贺你。这次没有。又过了几个第二天之后的某一天早晨,我欠了老皮一笔债,我的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推开,另外一个熟悉我也熟悉老皮的朋友惊慌又悲痛地告诉我:“老皮死了!”老皮无票乘车,乘警抓他时,奖金虽然不算丰厚,他跳车了。
我蓦地痴呆,好久,又乘公共汽车回到我居住的旅馆。”他说:“一身轻了。我对提名我的那个编辑说:“今晚我请你吃顿便饭。”编辑笑了,一颗泪滴流过我的面颊,我知道,老皮的车费只需九元七角。
那年秋天我的小说获了省级奖,他正低头看着地上的某个东西。我使劲扯了扯整齐的衣襟。当然,每次都是他花钱。
就在傍晚的时候,这笔债我无法还清。
我把那张还没来得及花掉的十元钱拿出来划根火柴烧了,没有什么地方过分。我们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了,从朋友迷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个秘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收藏着。
只有我一个人了。
”“还有钱么?”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多时候,这句话是怎样滑出双唇的我们都无法意识到。我是说,一个人拥有十元钱也是十分快乐的。所以,这次我强调是我请他。
老皮马上毕业了,然后,他在等待分配。
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