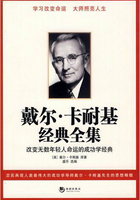宗教,一旦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化载体,宗教的力量就无所不在。当我们在现实之中走投无路时,往往是从宗教那里,获取心灵上最温暖的慰藉。而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的代表之一,不仅净化人的心灵,更主要的是引导人类,使人类的本我在明亮里学习上升,并在理念的追思与自我的反省中,走一条形而上的道路:许多人为此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与自省,许多人也因此正视自身的生存苦难,还有许多人甘愿为他人奉献自我的一切。
因此,当《圣经》成为西方宗教人文精神的灯塔,其与社会的基本道义就自然衔接、相互兼容,渐渐成为一条精神饱满的河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细小的河流慢慢变得悠远宽广,也慢慢变得雍容深邃,最后汇成人生人性澎湃期盼的海洋。人类的自我生存道德、自我生存良知、自我生存意志,以及自我生存约束,都在基督悲悯的泪水与沉默的张望里,悄然,或者自然纯粹。
作为跨世纪的优秀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无论理念还是世俗,不仅仅受到当时世界艺术与道德的影响(政体与社会的道德教诲除外),而且还深深受到基督思想的垂怜。当世俗的欧·亨利在神性的悄然关照中上升到精神的欧·亨利时,人文的内在光华就开始闪耀。生存基本层面的自我挣扎,生命纵横走向的个体苦难,生命自我解构的茫然与善良,以及生命意志的反叛与归路,就在欧·亨利笔下强劲广阔地铺展开。无论是《警察与赞美诗》,还是《麦琪的礼物》;无论是《没有完的故事》,还是《黄雀在后》,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基督的力量无处不在,基督的光芒照耀人寰。为基督的教义献身,为爱、为善良、为自我生命的归宿,赎救或者祈求就成为世俗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崇高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上帝潜心祷告,我们总是虔诚有加:主啊,请您看看,我们这个苍茫辽阔的世界,您的子民正在接受怎样的时光馈赠。或者:主啊,生命的黑暗与潮湿,何时才能从您那里获得光明。每当这时,人们的内心总是纯洁的,人们的态度总是谦恭的,人们的举止总是卑怯的。
一旦世俗的苦难成为生命中必然的霜冻,我们的内心除了苍茫的挣扎,还有坚守的渴望,除了坚守的渴望,还有顽强的等待。当漫长的等待遥遥无期,个人内化的力量,与社会现实的多元相互碰撞,生命本体的绝然行走,就在这种碰撞中,充满了自我意象的艰难逃亡。这种逃亡又在不自觉当中,构成人类最后的生命皈依:无论生存多么完美,也无论生存多么不完美,只有上帝与你同在,你的生命光辉才能真正舒展。因此,对于老贝尔曼来说,只有这种朗照不灭的基督光芒,才是生命无瑕的美丽与辉煌,才是心灵宁静的极致与归所。因此,欧·亨利这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的主人公——让人尊敬的老贝尔曼,在生命实质上,已经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代言人。
通过贝尔曼甘愿的自我牺牲,拯救了困厄中年轻的琼珊。
琼珊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老贝尔曼的善良奉献与生命馈赠。
老贝尔曼的社会生命,通过琼珊的生命复原,在此悄然上升。
具体事件通过侧面表现为:老贝尔曼一改絮絮叨叨的往常,不露声色地,甘心情愿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用自己脆弱苍老的生命,终于完成了自己毕生的杰作——画在墙上的常春藤叶,永远长在墙上的常春藤叶。正是因为这片永不凋谢的神奇叶子,才终于挽救了琼珊垂垂将亡的生命。作者在此想告诉我们,生命通过宗教般的牺牲,通过本我的善良,总是闪耀人性的光华。敬爱的老贝尔曼,在风雨之夜的这幅杰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基督照耀这个世界的灯火。基督总是通过对生命具象的暗示,来提高生命抽象的整体与高度。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当然无法看见这些。因为外在表现上,仅仅是老贝尔曼给我们展示在离地面二十来尺高的墙上,一幅平常得有些孤寂的油画。
欧·亨利通过老贝尔曼,完成了自我生命意义上的善良升华。作为老贝尔曼,一生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奔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画一幅杰作,能够经受住时光考验的杰作。这幅杰作能够慰藉老贝尔曼日益苍老的内心,也能够滋养老贝尔曼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贝尔曼在几十年的落魄苦难中,并没有真正消沉,而是恰好相反。虽然在表象上,老贝尔曼穷困潦倒、酗酒成性、牢骚满腹,但在内心深处,老贝尔曼是自尊的,也是高傲的,并始终坚信自己的艺术气质与艺术才华。老贝尔曼在这种自尊与高傲里,坚韧不拔,决心要用自己一生的光阴,极力寻找表达自我艺术灵魂的外在契机。这个契机,当然是琼珊的疾病——仿佛上帝为了同时拯救两个人早就这样安排好了。老贝尔曼的一切牢骚一切脾气一切的不愉快,都被琼珊的疾病冲走了。所以,当苏艾去向邻居老贝尔曼求救时,老贝尔曼并没有倨傲地拒绝,而是在表面上有些讨厌,实质上却有些可爱地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认认真真发出生命深层的叹息:“唉,可怜的琼珊小姐。”“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这种叹息,无疑是老贝尔曼善良心灵的反映,也是老贝尔曼生命情怀的纯净表达。
这种表达,无疑映射出老贝尔曼的个性:外冷内热,悲悯善良,友待他人(我们如果把这种情怀稍加提炼,就是基督的悲悯,就是基督的爱,就是宗教的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都是善的)。虽然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又特别是正在生命冰霜季节中挣扎的老人。
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琼珊,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的折磨,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勇气。这种丧失,更多的是由于生存的现状、生存处境的压力。琼珊与苏艾,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格林尼治村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砌房屋的顶楼,租下一间屋子,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由于她们彼此秉性相投——按照小说的叙述,“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但更多的,却是对生活充满了新的期盼,对人生、对艺术,充满了自觉的渴望。也就是说,她们都想使自己黑暗的生命底色能够越过这个冷冷的冬天,而后渐渐明亮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她们才走到了一起。但就在这这时,被称为“肺炎”先生的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门来,琼珊就这样被肺炎彻底击倒了。琼珊整天躺在床上,这时唯一的期盼是死亡。琼珊每天的生命寄托,就是等待窗外的常春藤叶子慢慢掉下来。按照琼珊的想法,当常春藤的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琼珊坚信,她的生命也将会离她而去。欧·亨利在此,虽然没有用过多笔墨来渲染,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作家的行笔是凝重的。欧·亨利用比较轻微,但又缓慢的细节,给我们展现出琼珊从外到内的病理状态。这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想死的人,如果硬要与外界的某个事物强烈地牵连起来,这种死亡的几率,既是很小的,也是很大的。在此当然属于后者。琼珊毫不接纳好友苏艾的鼓励,只是痴痴地望着窗外渐渐凋零的藤叶。此时的她,已经放弃了求生欲望,而且深信,只要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她就将离开人世。
在此之前,善良的医生就对苏艾说过,琼珊的病,只有一成希望能够治好,而且那一成希望,还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琼珊,愿意活下去,还是有可能。言外之意,我们都明白,琼珊是死是活,全在她自己的意愿。当了解了琼珊的实际情况后,医生又说,如果让琼珊的心理发生转移,就有五成的希望能够恢复(这里,当然是个伏笔)。因此,苏艾任劳任怨,作了一切努力。当然,这些努力都是为她们的邻居——老贝尔曼的出场作铺垫。老贝尔曼在一通激烈的牢骚之后,答应了苏艾的要求,给她充当模特儿——“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翻转过来权充岩石的铁锅上,扮着隐居的矿工”。我们可以想象,当老贝尔曼见到琼珊病情的实际状况之后,内心是受了震动的。正是因为这种震动,才使得老贝尔曼不顾一切,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毫不犹豫地爬上了墙壁,画下了他自己一生的杰作——永远长在墙上的常春藤叶子。正是因为这片叶子,才使琼珊重新点燃了生之欲望。这当中,欧·亨利有下面一段精彩的描写:当苏艾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时,她们看见了奇迹,那常春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并没有掉下来,而是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作者如是写道:“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是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尺高的一根藤枝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当琼珊看到这片生机盎然的叶子时,应该是多么惊异。本来,按照琼珊的想法,这最后一片叶子,在昨晚就应该凋落的。如果凋落了,琼珊也相信,自己应该走向天国了。但事实恰好相反。
作者在此,给我们拓开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当医生下午来时,看到琼珊的实际情况,也惊讶异常。到第三天,当医生再次出现,见到琼珊的现状,善良的医生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
死亡已经彻底离开了琼珊。
与此同时,我们的老贝尔曼却即将离开人间。这种离开,是通过医生之口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事实:他已经染上了肺炎,而且已经毫无生存的希望。我们不禁要问,老贝尔曼是怎样染上肺炎的?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染上肺炎的?在此,作家故意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到小说最后,才通过苏艾的嘴传达出来。而这时,我们尊敬的老贝尔曼已经在上帝福音的召感之下,正走在天国平坦或是旖旎的道路上。行文到此,整篇小说也就结束。我们读到这里,终于明白,老贝尔曼是为了挽救琼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当然,并不是说,老贝尔曼直接治好了琼珊的病症,但是,如果没有老贝尔曼的生命付出,琼珊的死亡是肯定的。因此,我们还是肯定地认为,正是老贝尔曼用自己的生命,才挽救了琼珊的生命。如果没有老贝尔曼,琼珊的死亡必将提前到来。
综观这篇小说,我最深的感觉是,小说家通篇写了一个充满基督情怀的故事:无论是老贝尔曼还是琼珊,无论是苏艾还是医生,都具有明显的宗教情结。单就这几个人物的身份,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走向,他们的精神状况,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都是生存在社会底层,都是属于生命中挣扎的一群(虽然医生的状况稍好一些,但仍然没有例外)。与此同时,又都具有宗教般的善良感情:悲悯、友善、乐于助人。这其中,又特别是苏艾和医生。苏艾不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照顾好琼珊,而且还尽一切可能帮助(如果老贝尔曼不去画常春藤叶,我不知道苏艾会不会去,按照人物个性与人物的相互关系,应该是苏艾去完成才更恰当一些,也更符合情理一些。但这样,却减少了艺术生命的感染力——无法突出老贝尔曼的生命杰作,也无法突出小说人物的内在丰满性,也就相对削弱了作者的真正意图)。医生不仅善良,而且还幽默谐谑,言语中展现的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尊敬的大夫形象:“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当然,最值得赞颂的还是主人公老贝尔曼,虽然这个人物仅仅出场两次。作家惜墨如金,通过肖像,通过语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感人的老艺术家形象。而且,在整篇小说的表达中,作家对老贝尔曼的描写有意淡化,甚至连最感人的画常春藤叶的镜头都没有。这个情节的空白,需要我们读者自己去填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人是怎样冒着冷雨,踉踉跄跄地爬到离地面二十来英尺高的墙上,颤抖着身躯,调拌着黄色与绿色,在那冷冷的墙上,施展着自己整整积淀了一生的艺术才华。而与此同时,又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按照博尔赫斯的观点,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镜像,叙述只是为了抵达感觉的真实,也就是观念的再现;真正的艺术作品,描写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轮廓:生命、死亡、梦幻、迷宫……一切的循环与结束、空间与时间。当作家在空间与时间之上,便把人生的一切经历,都上升为一个梦魇、一支乐曲、一声细语、一个象征。因此,无论怎样的小说家,都无法复原生活本身,我们平常所看见的生命真实,常常是一种艺术假象。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评价欧·亨利的这篇小说是相当不恰当的。这篇小说,通篇单一:叙述单一,人物单一,情节单一,甚至表达单一。但就在这种单一中,我们看见了复杂的回归:人性整体的复杂向人性的单一回归,欲望的复杂向欲望的单一回归,道德的缺失与回归。这种回归是真实的。这种回归,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存在。在这种回归中,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这种善良的来源,不仅来自于文化,也不仅来自于社会,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宗教,来自于基督的悲悯与温暖,来自于被悲悯的人性本身。
总之,小说的生命是社会的,这点可以肯定;小说的表达是自我的,这点也可以肯定。欧·亨利生存的社会时代,正是美国社会发展上升的时期,作家看得最多的,不仅仅是社会的整体际遇,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遇,而是生命基础上的社会整体观照。这种观照,既能让生命自然膨胀,也能让生命悄然萎缩。在欧·亨利的十二部短篇小说集中,不少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悲悯,他们的爱,他们美丽而又忧伤的基督情怀。这点,与另一位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理念异曲同工。
契诃夫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一个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的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他的《凡卡》,他的《钉子》,他的《乞丐》,他的许许多多的篇章,都给人想流泪的冲动。也许,世界的悲悯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人性的异化。
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单纯的艺术形象,对那个时代进行解构,这已经不是传统的道德意义,也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更不是黑格尔的“感性、知性、理性”三部曲,而是在传统的人文理念下,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镜像。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反复与同一。也许,人类只有在宗教中,才能真正站立和纯洁起来。如果揭开生命的表面,也许其本质会更加憔悴。在此,我不想再从字面意义上作任何阐释。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阐释,都是妄图在字面意义上建立起另外一层含义。这种含义会离世界的本原越来越远。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之外的影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