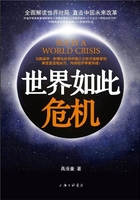睡得正香,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嗡嗡:太阳都照着半边屁股了,快起来练功去!懵懵懂懂睁眼一看,爹咧着一张嘴站在地中央。
我这才想起自己是在老家,昨天黄昏,我刚刚从省城回来。
愁绪和沮丧又一次包围了我。我不耐烦地把自己的脑袋埋进被里:爹,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您让我睡个懒觉……爹哑着嗓子嘿嘿笑起来:怎么,成腕儿了连爹的话都不听了?成腕儿了就可以不练功了?
我忽地坐起来,想跟正冲我较劲的爹发火。娘这时跟进了屋,她下意识去拉爹的手,爹却狠狠甩掉了娘的手……我说:好吧,我去练功!跟着话音,我看到了爹的笑脸。
嗯,虽说你小子又上电视又上报纸的,还去国外演出,可爹的话该听还听,是我儿子!
沿着村路,听着不知名的鸟叫声,我并没有心情练嗓踢腿。想到自己面临的困境,想到和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姐妹们,朝天叹一声,低下头,又下意识叹出一声。
走了几个来回,只是活动了下胳膊。
回家,看到爹在院里擦锄头,那锄头油光锃亮,几乎能照见人影。
我诧异道:一把锄头擦那么亮干吗?它不过就是个种菜的家把式嘛!
爹看我一眼,递过一条毛巾让我擦汗:这锄头可是我种地的武器,它就像你平时在舞台上用到的那些兵器,亮亮堂堂精精神神的,你看着不高兴呀?离开它你玩得转吗?
爹文化不高,想不到比喻倒很贴切。
第二天,又是在相同时辰我被爹叫醒。
我只有苦笑:爹,我是回家休息调养的,不需要见天就练功,那些本事都在您儿子身上长着呢,跑不了!
爹拍了下我光着的肩背:甭跟爹说这个。爹只知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哪轻哪重,你应该比爹明白。
没奈何,我只好听从爹的话。这次为让自己多流汗,我改为跑步。
其间,遇到几个同村的人,他们面露喜色:瞅老秦父子俩,爹种地勤快,儿子练功也不落后!
经村人这么提醒,我才想起应该到自家的地看看。
到时,我看到爹像一个伟人,正掐着腰和娘站在一起,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种下的果实。我这才惊诧自家地里的热闹非凡:芝麻、黄瓜、扁豆、红薯、丝瓜、南瓜,应有尽有,一个品种套着一个品种。我瞪大眼睛看爹:您这功夫不简单啊!
爹抿嘴笑:怎么样,小子,不比你演戏的功夫差吧?咱的地盘咱说了算嘛!
爹洋洋自得的神情像个孩子。娘在一旁捶了下爹的肩:瞧把你美的!
第三天,爹照例准时叫醒我,不过这次娘硬把他拉开了。
我像小时候一样,把屁股半翘起来,头抵在枕头上,想让自己多眯一会儿。
爹没好气地冲进屋,毫不客气地一个巴掌拍在我屁股上:快起来,练功去!娘进来还要阻止爹,爹把眼睛瞪得溜圆。
这次,我站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真正吊起了嗓子,我摇头晃脑的样子马上吸引来几个同村的孩子。我没有丝毫羞涩,继续字正腔圆一展歌喉,远远地便看见爹也走了过来。
有村人对爹夸奖:你这儿子的功夫,了不得呀!爹嘿嘿笑:他老子也有功夫嘛!秋后的庄稼,提早就收完了。把大家说得都笑了。
一周后,我把电话打给朋友,告诉他苏州那家公司我不去了。
朋友诧异地问我怎么了。此时,我正站在山坡上,目视着生机勃勃的村庄,我说:剧团解散了,可我不能让人心也散了。我要回去,找他们!
离开村庄那天,爹像个将军站在远处目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