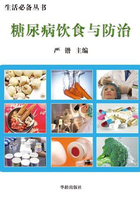第五节 汉字与美国诗学
1.罗厄尔与艾思柯的拆字
并置的产生,还有另一个源自中国的“理论基础”,那就是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对汉字结构的误解——认为汉字是意象的组合。由这种误解推导出一整套理论和实践的人,不止庞德一人,埃米·罗厄尔关于“拆字法”(split-up)的喧嚷,当时比费诺罗萨论文更耸动视听。
罗厄尔并没有读到过费诺罗萨论文的手稿。1918年夏,她的朋友弗罗伦丝·艾思柯从中国回美作关于中国诗的演讲,并展出她收藏的中国字画。她留住于罗厄尔家里时,两人花了几天时间欣赏这些字画,埃米·罗厄尔突然“发现”中国文字实际上是“图画文字”(pictogram)。据艾思柯说,罗厄尔作出了“天才的伟大的发现”:分解中国文字可得其意象组成。艾思柯向她提议她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合作译一卷中国诗,罗厄尔反应热烈。我怀疑这就是她下决心译一本中国诗选最初的原因。她可能知道,她的译文本身不可能超过她的对手庞德。但有了这个发现,她就能压倒庞德。
《神州集》出版,正是在她把意象派的领导权抢过来之时,庞德译诗的成功使她妒意正浓。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她在通信中宣称,对中国文字之意象组成的理解,“正是费诺罗萨所不可能了解的东西”,因为费诺罗萨从日本人那里学中国诗,而艾思柯直接向中国教师学。
罗厄尔并不知道局面与她说的正相反,费诺罗萨不仅了解“拆字”,而且搞出了一大套理论。但有一点她是对的,在《神州集》的译文中庞德没有做任何“拆字”。当代“庞德学”权威休·肯纳认为《神州集》中译的李白《古风第十八》(“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中的第三行是拆字译出的:
At morning there are flowers to cut the heart.
肯纳说,这里有一个汉字形象分解:一把刀与一个内脏。他搞错了,庞德此行是“朝为断肠花”的逐字翻译。肯纳所说的这个被拆的字看来是指“断”字。但这句诗翻译中显然没有拆字。“割开心的花”是“断肠花”的准确而且生动的翻译。
埃米·罗厄尔在给哈丽特·蒙罗的信中宣布了这种“拆字法”翻译原则,她说:
我作出了一个发现,先前西方所有关于中国诗的著作从未提及,但我相信在中国文人中此事尽人皆知,我指的是:每个汉字的字根使此字带上言外之意,就像我们语言中的形容词或想象的写作。我们不可能按汉字的字面意义译诗,每个字都必须追寻其组成,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用这个字,而不用同义的其他字。
又是典型的“埃米式”自信。埃米·罗厄尔鼓动艾思柯先写一篇文章宣传其理论。此即《诗刊》上发表的“中国书写画”(Chinese Written Pictures)。但在此文中,艾思柯阳奉阴违,主要谈了中国书法艺术与诗的关系,对“拆字”问题没有深入讨论。实际上懂中文的艾思柯在这问题上比罗厄尔本人谨慎得多,似乎只是由于罗厄尔的过分自信,而她不得不借重罗厄尔的声望,所以她才跟着跑。
艾思柯-罗厄尔理论,如果也是一种理论的话,只是想从汉字组成中挖掘顶替西方语言形容词的意义。艾思柯在《松花笺》的序言中写道:
这些笔画神妙的结合,我们称作汉字,实际上它们是完整思想的独立的图画文字式的表现。……正因为字在组成上有描绘性的暗指,全诗才从字的结构的意义潜流中丰富了其意义。
艾思柯-罗厄尔的拆字论与费诺罗萨-庞德理论很不同,它并没有朝美学-哲学维度展开,而只是在翻译时挖出汉字组成中的潜在的意义。而且,在翻译实践中,这方法马上就碰壁。艾思柯曾设法劝性格过于顽强的罗厄尔放弃这个方法,她在从中国写回的信中婉转地说: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信不疑我们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将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诗的全部意义转达给西方读者,我感到失望,简直不可能……实际上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汉字已不显示解析意义……
最后她们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可拆的时候拆,不方便即不拆。弄到最后,《松花笺》1921年出版时实际上只剩下十多处拆字,这才很幸运地挽救了这本译诗集,使它不至于完全无法阅读。
我们可以举此书中几个译例:李白《怨情》“深坐颦蛾眉”句:
She sits in an inner chamber,And her eyebrows,delicate as a moth"s antennae.
And drawn with grief.
杜甫《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句:
Wind weaves,of forest shadows and fallen moonlight,a pattern white in warp and black in weft.
恐怕连美国普通读者都会心里打问号:中国诗句真那么长?形容得那么复杂?比喻那么古怪?
罗厄尔为了证明她的方法正确,曾经拖赵元任帮助,并且由于赵元任的介绍,写信要在中国的艾思柯找胡适来撑腰。宾纳当时是与罗厄尔竞争中国诗权威宝座的最主要对手,但在对《松花笺》的评论中,宾纳的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中国诗人)他们的文字中含着比喻,但我们的文字也一样,只是程度少些而已。如果在译中国诗时要把象形文字组成的比喻拉出来,那跟译英语诗要翻出词源一样,是错误的。”
他指出,艾思柯-罗厄尔这种中国诗翻译法其结果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也曲解了中国诗的基本风格。
在诗歌语言上中国诗供应美国新诗人一种理想的简练诗风。罗厄尔反其道而行之,无怪乎《松花笺》当时受到如此多的非议。拆字法使中国诗浓浓着笔,色彩繁复。
由于罗厄尔在当时作为新诗运动领袖的声望,“拆字法”还是引起人们相当的兴趣。霍尔曾指出,他在华盛顿大学执教时,不少学生学罗厄尔从中国文字解析意象组成,并以此写成英文诗句,“就像解字谜,或解代数题。”
2.费诺罗萨论文
与艾思柯一样,厄内斯特·费诺罗萨最早认为中国文字是拼画,来自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误解。他在研究中日绘画时,经常接触到诗画,尤其是日本足利(Ashikaga)时代所模仿的宋画。费诺罗萨的第一个直觉的反映,是这些书法本身就是精美的绘画。
但费诺罗萨的中国文字观,看来还有一个来源,即汉赋。费诺罗萨的中国诗歌笔记中有几篇相当长的汉赋的详细译注,如《风赋》和《鸟赋》。在森海南讲授这些赋的过程中,他发现文字意思“随着字形相续的改变而带着许多意义”。例如偏旁“日”在许多字中重复,即与各种别的偏旁配合,产生连续的变化,而其隐含的意义,在费诺罗萨看来是“在眼睛前振荡”。
利用同偏旁字排列而达到某种形象效果的句子,的确在汉赋中有不少:
柔桡嫚嫚,妩媚孅弱。
——司马相如《上林赋》
或许汉代文学家对汉字的构成还比较敏感,但这种做法也只见于很少一些汉赋篇章。
费诺罗萨理论尚有更重要的思想背景:即他的“逻辑与科学对立观”。在他看来,(欧洲)“中世纪的逻辑”是一种“暴政”:
根据这种欧洲逻辑,思想是一种砖窑里的产品,用火焙烧成概念的硬块单位,然后按形状大小垒起来,贴上词的标签以备用,使用时即拣出几块砖,每块砖带着传统的标签,砌起一堵我们称之为句子的墙,用白灰浆即肯定系词“是”,用黑灰浆即否定系词“不是”。
费诺罗萨认为中世纪逻辑暴政,使语言不再具有表现物象的能力,而变成任意的、专断的符号。由此费诺罗萨跃向一个大胆的结论:正是由于欧洲语言的这种纯符号性质造成的孤立概念思想方法,“欧洲这么晚才懂得了进化论”。
他提出应该用“科学”来代替“逻辑”,而科学就是返回事物,返回事物的复杂功能与事物间的关联。“科学斗争着,直到它到达事物本身……科学发现事物中的各种功能如何结合。诗与科学一致,而不与逻辑一致。”
费诺罗萨的所谓诗与科学统一观,对于新诗运动,乃至对于整个美国现代诗歌,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他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经验主义,他是用一种模糊的经验主义来反对欧洲大陆上传统的理性主义。
我们这里不准备深入讨论哲学问题,费诺罗萨也没有进行如此深的哲学思辨,他谈的还只是诗学。所不同的是,当其他人(柏格森等)用直觉论来反对艺术中的理性主义时,当印象主义等艺术派别返回直接感受,返回经验本身时,费诺罗萨提出经验即科学,因为经验返回事物本身。
而汉字,费诺罗萨提出,从来没有失去表现事物复杂功能及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它是由象形的图案组合而成的,它不是符号。因此,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符合科学,它“到达事物本身”。这样,中国诗在本质上与庞德诗学的基本出发点一致了。
3.庞德的“汉字诗学”
要反驳这一点是容易的,任何对汉语知识稍多一些的人都知道汉字早就失去了直接表现物象的能力,早就成为索绪尔所说的“武断符号”。组合式的汉字,大部分原先就不是形象的组合,而是属类符号与发音符号的组合。费诺罗萨-庞德理论的语言学立足点一眼就可以看出不值得一驳,这篇论文自从1920年初次面世后,一直受到不少人的讥嘲。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篇论文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被当代美国反学院派诗人视作《圣经·旧约》[恰尔斯·奥尔森的《放射诗》(The Projective Verse)一文被认为是《圣经·新约》]。
实际上,细读费诺罗萨论文,就可以发现,他自己是明白他的语言学立足点成问题:“的确,许多中国象形字的图画起源已无法追溯,甚至中国的词汇学家也承认许多组合经常只是取其语音。”
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庞德从来没有从语言学角度为费诺罗萨辩护,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汉语知识可能从来没达到哪怕是费诺罗萨的低水平。他只是急于用费诺罗萨理论来引出一套诗学-美学观点。他明确声称:“我们面前这本书不是讨论语言学的,而是一切美学基本原则的研究。”
费诺罗萨提出的各种看法,庞德实际上是有所取舍的。例如费诺罗萨提出研究(翻译)中国诗“六原则”:大部分是迂阔的空话,至于寻找汉字组成中的语外义,虽是费诺罗萨论文的立足点,庞德却几乎从来没有付诸实践,直到他晚年译《诗经》时,才做了一些拆字式翻译,那可能有特殊原因:《诗经》句太短。
庞德所需要的,实际上是为美国新诗运动中既成的事实找辩解理由,为结论找推理,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诗学,这种诗学要求语言直接表现物象以及物象本身包含的意蕴。他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为现代诗的(“科学”的,非逻辑的)组合方式寻找理论支持。虽然英语已无以挽回地变成了符号,不再具有如费诺罗萨和庞德心目中“中国象形文字”那样直接表现物象的能力,但通过各种办法,还是能使英语取得美国现代诗要求的效果——“直接处理事物”。
庞德并不满意意象派那种静态的,图画式的素描诗,1915年他转向“旋涡主义”,提出了意象的新定义:“一个放射的节点,或一串结节……我能称之为旋涡,而思想不断地奔涌,从它里面射出,或穿过它,或进入它。”
庞德说得很玄,但谈到底,他要求的不过是动态的意象,反对静止画面。费诺罗萨似乎又为他从中国找来了根据:
一个真正的名词,即一个孤立的事物在自然界并不存在。事物只是动作的终点,或是会合点。同样,一个纯粹的动词,一个抽象的动作,在自然界也不可能存在。我们眼睛看见的是名称与动词的合一,是动态的事物,或事物的动态。而中国的概念正是把两者合起来表现。
费诺罗萨最荒唐的看法,那是汉语中有大量及物动词(每个字都是动态的)。上文说过,现代美国诗歌语言发展趋势是动词日见其少,名词孤立并置呈现越来越多,正合庞德的动态意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下文将有较详细的说明。庞德以费诺罗萨论文为根据,的确扩大了意象派的静态绘画式诗,或称为雕塑式诗。
如此形成的诗学,比休姆为意象派所建立的理论基础宽得多,因此不少论者认为埃米·罗厄尔等人可以说是休姆式的意象派,而庞德是费诺罗萨式的意象派。
费诺罗萨理论的精华正在于指出,“中国文字式”意象并置直接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1897年费诺罗萨在日本时,他昔时学生,著名学者有贺永雄把他引见给日本研究《易经》的权威根本道明(Michiaki Nemoto,1822-1906)。一席之谈,使费诺罗萨对《易经》的哲理大感兴趣。《易经》以形象和抽象结合的图符来说明世界永恒的运动变化使他叹服,他称之为“东方黑格尔主义”(Oriental Hegelianism)。正因如此,当他试图从中国文字中抽萃出中国诗学时,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事物之间联系的辩证思想。
4.“汉字诗学”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