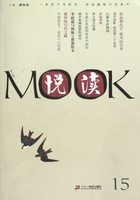第二节 中国影响与美国现代诗之“叛逆倾向”
1.后维多利亚诗风
在20世纪初,美国依然是个文化上落后俗气的暴发户。
而美国人自己也多半这样看,伦敦依然是英语文学的首都,美国诗人还得到伦敦去打天下,以便在美国成名。庞德到1912年左右在美国国内有点名声了,原因就是他的作品出现在英国一些刊物上。当时美国报刊提到庞德时,总要说明这位青年诗人“赢得英国文学界承认”。《文学文摘》的一篇题为《英国发现的美国诗人》的文章把美国文化界这种攀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笨拙》(Punch)杂志拿你的名字开玩笑,然而又补一句说是你的诗,‘是罗伯特·勃朗宁以来最杰出的作品’,应当说,这就够保证你一举成名了。”
当时的美国诗,只能算是英国诗的一个分支,一个附属部分。美国民族诗歌的伟大先驱者沃尔特·惠特曼和爱米丽·狄更森生前寂寞,身后也寂寞,他们的作品被人多年忘却。实际上是在现代诗运动中他们才被美国人重新“发现”。
世纪初,控制着美国诗坛的是所谓“高雅派”诗人,以模仿英国诗为能事,而模仿的,也只是维多利亚浪漫主义的末流,他们是一批“写十四行诗的侏儒”。
新诗运动,是一个相当自觉的使美国诗美国化的运动。庞德指出:“活的英语文学或美语文学的出版中心,在1917年至1919年左右移到纽约。”
而哈丽特·蒙罗说得更透彻:“当美国诗歌不再像是一种殖民地文学后,英国诗相比之下就好像是外省文学。”他们的说法都很夸张。夸大其词是文学运动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美国这个把借来的英国文学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文学传统始终是个不舒服的压力。英国文学是异国的,但却不是外来的,迄至当时为止,它一直是英语文学的主统,是美国人不得不接受的强加于他们的传统。
尤其是,在20世纪初,英国文学的特点是保守,比19世纪都保守。波尔战争掀起的沙文主义狂热结束了热闹一时的拉斐尔前派,唯美主义,帝国主义诗人吉卜林之类的“爱国”作品风靡一时。想成功的作家,似乎都得迎合市民乡众的口味。庞德曾经这样描写英国诗:“1890年至1910年,一般的英国的诗歌是一个可怕的肥料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模仿之模仿,伊丽莎白时代铿锵语言之模仿的模仿的模仿,毫无锋芒,软得不成形状。”
1912年起,英国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这就是“乔治诗派“(The Georgians)。此派以1910年新即位的英王乔治五世命名,其串线人物爱德华·马什(Edward Marsh)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秘书,政界中人。马什本人与庞德互相敌意很深,实际上庞德在1912年底搞意象派的动机之一就是与乔治派唱对台戏。理查德·奥尔丁顿辛辣地描述乔治诗派的特点:“乔治派诗人的视野是地方性的,喜欢小题材,他们在周末小小旅行一段,到一个小别墅,在那里就一个小题目写一首小诗。”
从今天看来乔治派可算是维多利亚浪漫主义余波的最后一个浪花。乔治派实际上也是英国诗歌从追赶甚至超越全欧文坛的架势退回英国地方文学的开始。乔治诗派这种恪守传统,小处着眼,略求新意的诗路,对一部分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人还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英国诗坛保守力量之大,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1913年册封70岁的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为桂冠诗人。此人诗风属正宗,株守成法,精雕细琢,他的论文全是研究格律与辞藻,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遗老。选他做桂冠诗人这件事使美国现代诗人对英国诗正统更为鄙视。《诗刊》社论抗议说:“布里奇斯先生追求的理想是18世纪理想;布里奇斯先生写的诗是18世纪诗歌。”
布里奇斯访美时,美国诗坛很不热情,与叶芝访美所受到的欢迎恰成对比。有人请布里奇斯念诗,他拒绝了,报上标题竟是:“皇家金丝雀不肯鸣唱”。而《诗刊》抨击他做了桂冠诗人后的创作更是尖锐:“英国的桂冠诗人感到自己的责任是,至少其一部分诗要写爱国主义的题目,在其位谋其政,而布里奇斯履行职责倒也忠心耿耿。这种人与大众无法感情相通,他写诗像在做命题作文。”
美国诗人与英国传统派互不相容的关系,在庞德的一则有趣的逸事中可见一斑。1913年庞德写信给蒙罗说:
奎勒柯奇(Arthur QuillerCouch,当时英国诗坛主要批评家)几星期前给我写来一封老派的令人高兴的信,他希望我不要鄙视维多利亚这个伟大的名字,他希望在他编的牛津维多利亚诗选中收入我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誉——至少我应把它看作英国批评界对我的承认。但是他选中的两首,正好是我在自己的底本中做了记号“删”,准备下一版就不要的诗。我把这点告诉他,恐怕他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至少此事从此没有下文。
2.中国诗在英国的冷遇
作为美国新诗运动一大特色的中国热,在英国诗坛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作为意象派源头的休姆(T.E.Hulme)的“诗人俱乐部”,曾经热衷于写俳句,这股风气在英国未曾扩大,也未能持久,只是传给了美国诗人。英国当时也有一些认真严肃的汉诗翻译家,如克兰默宾(CranmerByng),但他作风守旧,把中国诗译得像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诚然,为把中国诗影响传到现代英语文学中做出最大最持久贡献的阿瑟·韦利是英国人,而且是当时著名的高雅文人集团“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中的人物。但此集团中人对韦利并不敬重,韦利似乎是个边缘人物。相反,韦利当时与庞德、艾略特等美国诗人却过从甚密。
韦利的第一本译中国诗集,1916年曾计划由其好友,美学家罗杰·弗赖主持的出版社出版,弗赖找同事商量,大家认为最多只卖得出60本,这就是当时出版界对中国诗在英国接受程度的估计。韦利无奈,只好自己花钱印了100本,自己装订成册,分赠亲友。
尤妮丝·狄任斯曾想把她那本当时在美国很受欢迎的书《中国剪影》在英国出版,美国出版商告诉她这本书在1916年“曾推荐给所有的伦敦出版商,但都被谢绝了”。
我们并不想把这种英美对抗局面说得太过分,因为英美诗歌无法摆脱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时的确是兄弟阋墙,要分家的时候。
3.中国诗引发的激进、保守之争
在美国国内,这种革新与传统的斗争,这种跟随英国传统亦步亦趋的势力与创造美国新诗歌的斗争,表现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前面已讲到过在新诗运动前控制美国诗坛几十年的“绅士派”诗风。这些诗人,占领了发行量很大的正统杂志,如《哈泼氏》《大西洋》等;在大学文学系里,则有学院派批评家作为其理论喉舌。现代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进入这些杂志的版面的。
新诗运动,是以一些发行量不到几千份的小杂志为阵地发起的一场反体制运动。新诗运动之反“大杂志诗”是有意识的,充分自觉的。哈丽特·蒙罗在创办《诗刊》之初,到处通信搜寻新作者,但她决心不与任何已成名的“杂志诗人”联系。
另一份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杂志《小评论》,其编者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回忆说:“《小评论》开头几年刊登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那时全世界没有一家杂志肯刊登的。到后来,他们就抢着刊登我们这些作者的作品,并且付高稿酬。”
她说的情况的确如此,新诗运动迫使大杂志节节后退,逐步让出阵地。
我们可以比较几本标准的诗选。新诗运动之前美国诗人最大规模的结集是爱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Edmund Clarence Stedman)1900年所编《美国诗集》(An American Anthology)。全书共收六百多诗人,其中第四部分,即当代部分,亦有104人,可谓盛极一时。但是,1918年霍华德·威拉德·库克(Howard Willard Cook)所著《今日诗人》(Our Poets of Today),共选85位诗人,其中在斯特德曼选集中也入选的诗人只有12人,只剩40%!而库克这本书总的倾向还是比较保守的。1919年杰西·B·里登豪斯(Jessie B.Rittenhouse)所编《当代诗选》(The Second Book of Modern Verse)共选92人,其中只有6人在斯特德曼的诗集中出现过,只占6.5%。
诗人一向易受历史无情而公正的淘汰,但像新诗运动这样大规模地扫荡诗坛,引出一代新人,也引出绵延至今的美国现代诗歌新传统,的确不常见。
而中国诗似乎是现代诗运动这种胜利进军的前锋。
大杂志在1915年前并不是不登中国题材诗或仿中国诗,然而,刊登的往往是19世纪东方情调的仿中国诗,威廉·罗斯·倍尼特的《神州归来的商人》就是首先刊登在《麦克鲁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彼得森(Frederick Peterson)以中国花鸟为题材的风格古旧的组诗《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在出单行本之前,也是出现在“大杂志”《哈泼氏》上的。
对于风格比较新的中国题材诗,或简单地说,用自由诗写成的仿中国诗,大杂志是不愿刊登的。
英国诗人厄普瓦德发过牢骚,他那组大受美国新诗运动欢迎的仿中国诗在大杂志那里挨了几次退稿,“我偷偷诅咒他们是西洋鬼子。”
狄任斯想请埃米·罗厄尔给她的《中国剪影》写篇评介文章,刊登到《耶鲁评论》这样的大杂志上,罗厄尔回答说:“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发一篇评论,但恐怕只能是比较激进的小杂志。你建议《耶鲁评论》,这话使我忍不住一笑。《耶鲁评论》让我来评诗,就像让他们请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写篇政论一样不可能。”
庞德也曾经想请耶鲁出版社出版费诺罗萨文稿,但毫无结果。费诺罗萨论文最后还是在《小评论》上连载。
再举一个例:《日晷》(The Dial)杂志原是芝加哥一家老资格的杂志,创刊于19世纪80年代。1916年前,它在芝加哥与《诗刊》俨然作为一旧一新两阵对垒,那时它几乎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中国诗的评论或中国题材诗作。1916年这份著名的保守杂志改组,1917年迁往纽约,变成一家激进杂志,到1922年为止,它发表了有关中国诗的评论和仿中国诗创作共15篇。这个对比太明显。
大杂志不得不接受新诗运动的胜利,其标志之一是它们紧跟小杂志发表中国诗的翻译。
韦利翻译的中国诗第一次发表的是1917年第六期《小评论》上发的《白居易诗八首》,10月份英国享有盛名的大杂志《新政治家》就刊登了7首,此后韦利的译文在这两家杂志轮流发表。
宾纳译的《唐诗三百首》首先也出现在《小评论》上(1920年3月号6首,5、6月号7首),后来才发表在大杂志《书人》(Bookman,1921年12月),《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1922年1月)上。
小杂志编者对大杂志抢“发现中国诗的荣誉”很不高兴。1917年,伦敦《泰晤士报》刊文《中国诗人能教我们什么》,美国《文学文摘》立即转载此文。《诗刊》编者哈丽特·蒙罗在社论中写道:“众所周知,《诗刊》从创刊起就注重东方,早在三年之前就刊登了庞德先生从费诺罗萨笔记改译的中国诗——李白的《羁客信》——而《文摘》的编者偏偏就忘了提这个事实。”
《小评论》好斗的编者玛丽特·安德森则用中国诗作武器来向大杂志进攻。1917年6月号这家小杂志刊登了麦克斯威尔·波登海姆与日人佐佐木合作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这批译稿原是被大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退回的。安德森抓住这个好题目来向大杂志进攻。她在一条辛辣的编者按中写道:
《新共和》这家伟大的杂志——我没法说这是一家伟大的当代杂志——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面前,当这些颤颤巍巍的宿耆走过来时,我们敬畏得不敢置一词。
可是现在从《新共和》的档案中来了这么一张退稿条,拒绝刊登一些中国诗,……我们感到我们这次发现了一些对考古学家和一切对历史的神秘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十分有趣的东西。很可能李白本人就在《新共和》编辑部里,只是现在年老昏聩,写不出诗了,只能在他的专家班子里尸位素餐。
安德森这一席话中的话是很明白的:我们对各种可尊敬的传统不敢置一词,那是你《新共和》的专长,但对于中国诗,你《新共和》没资格发言,你不识货,自讨其辱。
《小评论》是当时最“激进”的杂志,遭受的物议也特别多。1917年10月号,该杂志被邮局全部没收,因为“内容诲淫”。问题出在该期刊登的温德姆·刘易斯的小说《堪特尔曼的春日伴侣》(Cantleman"s Spring Mate)。《小评论》编者向法院控告邮局,迅速败诉。在12月号上玛格丽特·安德森愤怒地表示抗议,号召其读者捐款以弥补亏损,并且,为了证明被没收的10月号是多么出色的一期,她在12月号上重新刊登了10月号头条:阿瑟·韦利译的《白居易诗八首》。她在按语中说:“如此好诗,岂容埋没。”
这位安德森小姐没有重印被没收的10月号其他内容,也很策略地一字不提刘易斯的小说。在她看来仅仅扣押中国诗这一项就足以向读者证明邮局与法庭是多么浅陋无知而又蛮横无理。
很难断定中国诗在为现代诗运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没有中国诗,现代诗运动也会成功。但是中国诗至少是现代诗运动首先获得承认的成果之一。现代诗没有长期成为在几个先锋派小杂志上孤芳自赏的运动,而较快地成为美国诗歌的主流,对此,中国诗是起了相当大作用的。
4.中国诗与反战立场
新诗运动期间,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美国诗人与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隔了一层,美军到1917年才正式投入欧洲战场,美国文人没几个人在军队中,本书提到的诗人只有狄任斯志愿去做军中护士。而英国文化人死于战场的人之多则令人吃惊。
美国新诗运动诗人,大部分是反战的。宾纳就是由于对世界大战感到厌恶而从欧洲文化传统转向中国文化的。弗莱契曾说,奥尔丁顿与庞德反目的原因是奥尔丁顿与H.D.夫妇俩反战,而庞德想激发起对战争题材诗歌的兴趣。这显然不确实。早在1914年大战刚爆发时,庞德就认为:“这可能是两个同样令人憎恶的势力之间的冲突。”
战争环境使伦敦不再适合于诗歌的发展。奥尔丁顿回忆说:“文学刊物无声地消失,文学论文无人需要,而诗歌必须是爱国主义的。”英国诗坛这种局势实际上帮助美国新诗运动成为英语新的诗歌潮流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