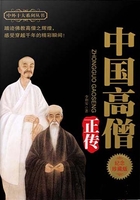总之,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并没有就党的组织改革进行战略性的规划,清党标志着他对党的领导的破产。就任总统以后,罗斯福把不干预“地方”选举搞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当候选人——其中许多人是坚定的新政派——急需白宫支持时,麦金太尔或是厄尔利就拿“总统不参加地方选举”这条“牢不可破的”戒律来抵制他们。当政府的好朋友基·皮特曼1934年面对共和党和麦卡伦派民主党的联盟时,罗斯福只是说:“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在会议上公开发言,告诉内华达州,我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但是,“像对预选保持沉默这种事情正是我的工作对我的许多惩罚之一。”在1934年的选举期间,内阁成员向他请示他们是否能发表竞选演说时,罗斯福回答说,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州内,其他地方不行。
罗斯福过去一直比较谨慎,但是在1938年却一改常态,把政府的全部政治砝码——金钱、宣传、报纸影响、联邦官员以及他本人的声誉——都投入了地方选举,力图把他的政敌清洗出去,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早期的政策。在遭受白宫五年的冷遇后,地方候选人和党内集团都不服从总统的管教了,因为白宫并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好处。
清党本身就是罗斯福的应急措施。虽然背叛党的问题好几个月来已很突出,清党的想法早在1938年冬天已经形成,但是当局的做法绝大部分都显得在最后一刻是匆忙的、不合式的,甚至是十分笨拙的。在有的州,白宫的干预只是使得党内反对派更加对立,却不足以保证使之落选。罗斯福自己采取的策略更是鲁莽行事与犹豫不决、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与诡谲的幕后活动二者奇怪的结合。
然而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其主要失败还不在于清党,而在于他当了六年民主党全国领袖以后各个州的民主党的状况。在宾夕法尼亚州,劳工、新政派、民主党保守派吵得不可开交,罗斯福把它比喻为但丁的地狱。深刻的分歧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大伤元气;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等州的民主党因为在1934年和1936年两度被白宫遗弃而无所适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党则分裂为有组织的民主党、“每星期四赚30美元”运动的支持者和许多其他派别。
更重要的是纽约州民主党的情况,因为罗斯福对他自己那个州的政治形势知之甚详,而且也没有禁止干预该州事务。对于1933年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的干预是非常巧妙的,若干年后政治家们仍在争论他支持的究竟是民主党的哪一派,他是否非常想让拉瓜迪亚当选。1936年他鼓励纽约州成立工党以便有助于他再次当选。法利、弗利和其他的民主党人指出,工党总有一天会反对该州的民主党,而他却嗤之以鼻,但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到1938年,纽约州的民主党比过去许多年更加削弱,而且更加四分五裂。
罗斯福把1938年选举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各地民主党候选人和领导人的弱点。其实原因要复杂得多。他没有从基层起建立更强大的党的体系,没有使之更直接地响应全国性的领导和更紧密地配合新政纲领及措施,这就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很快就被以在位的或正在争夺职位的州或地方领导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所填补。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大大巩固了地方党的集团,也大大巩固了他们组成的利益集团。新政在全国范围内使各种利益集团摆脱了懒懒散散的状态而成为有可能破坏罗斯福联盟的政治势力集团,与此同时,新政也促使地方集团脱离白宫的控制。
在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威廉·艾伦·怀特给法利写信说:“如果我们亲爱的领袖在约翰·刘易斯和卡特·格拉斯两人之间找不出共同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抡起大锤把两人间的巨石打碎,不再管什么党不党,而是在大锤下的一片碎石上去拼凑他的政策吧!”这位有眼光的堪萨斯州人的评论很能代表当时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总统已经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了那么多只兔子,难道就不能再变出一只来吗?
清党事件表明,他变不出来了。帽子是空的。但是怀特的建议对作为党的领袖的罗斯福是一大考验。总统还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他有无可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党?美国政党制度的性质,特别是民主党,是否排除了为实现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更广泛的新政而必须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习惯势力相当强大。美国的党派制度并不容易改变。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就是一些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的控股公司,而这些集团又以这样一些人为中心,他们掌握着或正在争夺无数州的或地方的职位——例如州长、县长、州立法委员、市长、地区检察官、美国参议员、县政专员、市政委员等,大家又通过党的传统、总统的领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主张而松散地联系起来。只要美国宪法制度还创造值得各州和地方通过选举去占有或争取的东西,那么政党就会一直无纪律无中心。
长期沉溺于复杂的美国地方政治的罗斯福,对于政党改革方面存在的障碍是一清二楚的。他不愿与令人不快的地方领袖如黑格和凯利之辈闹僵,就是他无意实行显而易见的改革的明证。总统或许也低估了自上而下地给党注入活力的可能性。
有的新政派担心民主党的衰败使它不能成为实行进步政治的支柱,因此主张建立忠于新政的总统派,这种派系可以把党从地方性的争吵中拯救出来,使之致力于全国性的纲领。组织总统派的尝试夭亡了。然而,如果总统给予指导和支持的话,本来是可能成功的。新政已经在党内激发起生气勃勃的因素,它们把纲领放在地方利益之上,它们关心的主要是改革和复兴的全国性政策。通过与这些力量合作,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他对全国党的机构的控制,总统足以对付新政的反对派,而且也是可能使中立分子转而支持新政。
这样做究竟会不会成功无法回答,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尝试过。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清党本身表明,长远的、经过良好组织的努力可能在许多州起作用。因为清党确曾在两种情况下奏效了——在北部城市区,在那里曾有所规划而不完全是仓促上阵;在南部某些州,在那里白宫帮助的是地位巩固的在职者如奥康诺,而不是想搞掉某个地位巩固的反对派如佩珀和巴克利。清党的结果的确划出了总统力所能及和无能为力的区域的大致分界线。
要是总统在第一届任期内曾经认真培育党内的新政派势力的话,前一种区域无疑地是会大得多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总统没有重视他所领导的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的潜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为争取1932年的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作了巨大让步,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种让步对他的约束,包括接受加纳和其他保守派进入内部核心。他在第一届任期内的成功,使得他的那种个人领导的方式看来似乎可行,凭着他无穷的智慧和吸引力,他克服了一次一又一次的危机。于是,罗斯福就不从长远着想去花工夫把党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政治家,罗斯福关心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选举地位,而不顾党要付出多大代价。运用他自己的政治手腕,总比去改善摇摇欲坠、散散漫漫的党组织要容易得多。
然而,罗期福之所以未能把党建设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充分承担党的领导义务,在于他始终想保持选择策略路线、包括退却路线的自由。罗斯福的许多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策略家——他的敏锐、他的善于扮演各种角色、他的能攻能守、特别是他个人的吸引力和诱人的魅力——但这些特征却不适合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坚定的努力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支持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后一种情况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一种既定的战略——而这正是罗斯福所不愿承担的义务。
他从未忘记伍德罗·威尔逊的深刻教训,他脱离了他的追随者,前进得太远了。不过,也许他也没有充分领会威尔逊的教导:“如果总统带头,党就不能不跟他走。”如果罗斯福曾按照精心择定的目标来领导和组织党,如果他曾唤醒农民、工人、领取救济者、白领工人、宗教和种族的少数集团等广大群众并使他们与党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他能运用他自己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来对付利益集团的联合势力,那么在第二届任内,新政在国内战线上的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不管罗斯福权宜之计有多少缺点,但是,也正是这种变化无常的特点使他具有应付多变局势的灵活性。1939年在世界事务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需要的正式这种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