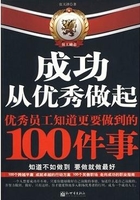安东尼诺从座位上跳起来。“我要走了,”他说,“这位姑娘今早和神父一起从索伦多来,今晚就得回去照看她生病的母亲。”
“啊,不忙,天色还早哩!”渔夫说,“她还有时间喝一杯的,喂,太太,再拿个杯子来。”
“谢了,我不喝酒。”劳蕾娜说,依然离他们有几步。
“尽管斟,太太,斟吧!她是不好意思。”
“算了,”年轻人说。“她脾气犟,说不愿意就是天主也没办法。”说了就匆匆告辞,跑下船去,松了绳子,等待少女。她向店主人和他妻子再次挥一挥手,然后向船走去,脚步有点踌躇。她先向四周看看,好似期望有别的客人同行。然而小码头上半个人影也没有;渔夫们有的睡觉,有的出海捕鱼去了,几个妇女在门口或是睡觉或是纺纱,而早上渡过来的那些观光客要等天气凉些才回去。她没张望太久,安东尼诺猝不及防地便像抱小孩似的把她抱上船,跟着他也跳了进来,摇了几桨,船便出海了。
她坐在船首,半转过身背对着他,他只能看见她的侧面,现在她的样子比平常更严肃,头发垂落在额头上,纤巧的鼻子鼓着一份执拗,芳唇紧抿——船在海上默默航行了一阵子之后,她觉得太阳炙人,便从包巾里拿出面包,把包巾罩在头上,一边以面包当晚餐啃起来,她一整天都没进食。
安东尼诺看见这情形,立刻从早上装橘子的筐子摸出两个橘子说:“喏,劳蕾娜,这是给你解渴吃的,不要以为我是特别为你留下。它们是从筐子里掉出来的,当我把空筐子放回船上时发现了。”
“你吃吧,我有面包就很满足了。”
“你吃点解渴;你走太多的路了。”
“我在上面已喝过水,不渴。”
“随你便。”他说,随手把橘子丢回筐里。
又是一阵沉默。海面波平浪静,几乎听不见龙骨破水的声音。甚至栖居在岸上岩洞里的白海鸥,都寂静无声地觅食。
“你可以将这两个橘子带给你母亲。”安东尼诺再次开口道。
“我们家里还有,如果吃完了,我就去买。”
“你可以拿给你母亲,代我向她问候。”
“她又不认识你。”
“这个,你可以告诉她我是谁啊!”
“我也不认识你。”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否认认识他。一年前,就在那位画家来到索伦多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安东尼诺和几个镇上的年轻人在大街附近的广场上玩滚球戏。画家就是在那儿初次邂逅劳蕾娜,当时劳蕾娜头上顶着水壶从他身边不经意地走过。那个那不勒斯人看见她,虽然只要再走两步就不会挡着人家的游戏,却愕在那儿瞧着她。他的脚踝被滚球击中,才想起这不是发呆的地方。他看看周围,仿佛等着人家来道歉。掷球的年轻船夫倔犟地站在伙伴中间,没有说话,于是那个观光客便识相地走开了。但是这件事被人传开了,尤其是当他公开向劳蕾娜求婚时,人们更是议论纷纷。当他问她是不是为了那个无礼的家伙而拒绝婚事时,她气愤地说,“我不认识他。”然而她也已听到人们的话,从此以后,只要看见安东尼诺,她一眼就认出了他。
现在他们俩坐在船上,却像仇敌一般,心里都很气。安东尼诺平常温和的脸涨得通红;他用力击着水面,溅起了泡沫,偶尔双唇颤抖着,仿佛要骂人了。她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一副无知的神气,俯在船舷上,任海水从指间溜过。然后她取下包巾,掠一掠头发,好像船上只有她一人,只是眉毛仍在颤动,她徒然举起湿淋淋的手敷在烫热的脸颊上,想让它凉爽凉爽。
现在他们身在大海中央,远近一艘船也没有。小岛已落在遥遥的后头;热气中隐隐可见海岸线躺在那儿;船与岛之间是一片深深的孤独,海鸥不会飞过来的。安东尼诺环顾四周,心里似乎有了主意。他的脸色突然显得苍白,丢下了桨。劳蕾娜不由自主的转过头来看他,紧张但没有恐惧。
“这件事非得有个了结不可,”年轻人气汹汹说道。“我可忍得够多了,奇怪的是我竟没有因此而毁灭。你说你不认识我?难道你不见我像个疯子似的从你身边走过,满肚子的话要向你说?你却摆出一副凶巴巴的脸孔,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要说什么呢?”她简慢地回答。“我当然看见你想同我来往,但我不愿别人无中生有地说我闲话,因为我不想嫁人,不仅是你,任何人我都不嫁。”
“任何人都不嫁?这话你不会说一辈子的。是不是因为你拒绝了那个画家?哼!你那时还只是个小丫头。将来有一天你觉得孤寂了,恐怕第一个碰到谁就嫁给谁,你真是疯了。”
“谁知道将来的事。也许我会改变主意。这干你什么事?”
“干我何事?”他脱口怒言,从椅板子上跳起来,以致小船摇晃不止。“干我何事?你明明知道,还要问?但愿你善待别人,不会让他像我这般死得凄惨!”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自己发狂,我有什么办法?你凭什么干涉我?”
“哦,”他大声说道,“当然,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我知道:只要我是出于正经之心,对你便有权利,就像我有权利可以升天堂一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你和另一个男人一同进入教堂,让那些女孩子们对我耸肩吗?我要忍受那种侮辱吗?”
“随你便。你吓我不了的。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种话你不会说得久的,”他浑身发抖,“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不会让我的生命毁在一个像你这样顽固的人的手里。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我的手掌里,只有听话的份。”
她微微动身,盯着他。
“如果你敢,就杀死我。”她缓缓地说。
“要做就做到底。”他说,声音比较柔和些。“大海上有的是足以容纳我们两人的空间。我不能救你。”——他几乎同情地说,仿佛在梦里一般——“但我们俩必得都下去,现在就下去!”他大声喊叫,突然抓住她的双臂。但随即又抽回右手。她狠狠地咬了他,血流了出来。
“我不必听你的话!”她叫道,突地一扭身,推开了他。“你看我是不是在你手掌里?”说罢便从船上跳入海里,顷刻间便在水里不见了。
不久,她又浮了上来,裙子紧紧地裹住身体,头发都给浪打散,紧贴在脖子上。她奋力划动双臂,闷声不响地向着海岸游去。他愕然得发了好一会的呆。他站在船上,屈身向前,两眼盯视着她,好像眼前发生奇迹一般。然后他浑身摇动,抓起桨,使尽全身的气力追赶,这时候船底因为不断流出的血而染红了。
虽然她游得很快,但不一会儿他便追到了她的旁边。“老天!”他叫道,“上船来吧!我刚才发了疯;天晓得,我怎么失去了理性。好像是晴天霹雳,把我烧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劳蕾娜,我不求你宽恕我,只求你上船来,保你一条命。”
她置若罔闻,继续往前游。
“你游不到岸的,还有二公里远。替你母亲想一想,万一你发生意外,她会惊骇而死的。”
她算了一下海岸的距离,而后不声不响地游到船边,双手抓住船舷。他站起来拉她,船倾向一边,铺在椅子上的夹克便滑落水里。她敏捷地攀了上来,爬回原来的位置。他见她安全了,便又抓起桨。她自顾将身上的水扭干,当她低下头看着船底板时,才发觉血渍。她迅速地往他的手瞥了一眼,他仿佛没有受伤似的仍在摇桨。“哪!”她把包巾递给他。他摇摇头仍旧划着桨。她终于站起身向他走去,把包巾绑在深深的创口上。然后,不管他的抗拒,便从他手上夺过一把桨,看也不看他一眼地在他对面坐下来,两眼专注于那染满鲜血的桨,奋力地划着。两个人都面色苍白,默默不语,当他们将近陆地时,遇见几个正在撒网准备夜里捕鱼的渔夫,他们高声对安东尼诺呼叫,还对劳蕾娜揶揄,他俩既不抬头也不回答。
当他们进入码头时,太阳仍然高高挂在普洛西达岛上。劳蕾娜抖抖那几乎干绉在一块儿的裙子,跳上岸。早上看见他们出海的那个纺纱的老妇人又站在屋顶上。“安东尼诺。你的手怎么啦?”她对着下面喊道。“老天爷,满船都是血。”
“没什么,老太太,”青年回答,“我被一根突出的钉子刮破肉,明天就会好的。我这该死的血,一碰就流,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
“我就下来给你敷一点草药,孩子,你等一下。”
“不麻烦您了,老太太。已经包扎过,明天就会好的,什么事也不会有。我的皮肤健康,复原得快。”
“再见!”劳蕾娜说,转身就向坡上的小径走上去了。
“晚安。”青年在她后面喊道,但没有看她。然后他收拾船里的工具和篓筐,登上石阶回家去了。
两间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来往地踱着。有着木窗板的小窗子是开着的,吹进来的风比平静的海面还要清凉,孤独中他感到一股慰藉。他在圣母的小神像前站立良久,虔诚地望着圣母头顶上用银纸贴成的光圈,然而他却想不出要说什么祈祷。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还祈祷什么呢?
白日好像停止了下来。他多么渴望黑夜的来临,他太疲倦了,血流得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他感到手上一阵剧痛,便坐在凳子上,解开绷带,原已遏止的血又流了出来。伤口的四周肿得很厉害。他小心地加以洗濯,又在冷水中浸了好一会。当他再看伤口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劳蕾娜的齿痕。“她是对的,”他说。“我是畜牲,罪有应得。明天叫吉士皮把这条包巾送还给她。我再也不要看见她。”——于是他仔细地把包巾洗净,用另一只手和牙齿把伤口再度尽量包扎妥当,然后把包巾摊在太阳底下晒。之后,他便倒在床铺上,闭起眼睛。
明亮的月光和手上的疼痛,使他从半睡中醒了过来。他刚刚起身,正想把手浸入水里止痛时,门口响起了一阵声音。“谁啊!”他边喊边去开门。劳蕾娜站在他面前。
她没多说什么就走进屋内,解下头巾,把一只小篮子放在桌上。
“你来拿你的包巾?”他说,“其实你可省下这趟麻烦,因为明早我就会找吉士皮拿去给你。”
“我不是为包巾而来的。”她连忙回答。“我到山上去给你采了一些止血的草药。喏!”她揭开篮盖。
“太麻烦你了。”他说,声音里没有刺耳的意思。“太费心了,我已经觉得好多了,好得多了。何况不好也是自作自受的。这时候你来做什么呢?万一给人瞧见了!你知道,他们将如何喋喋不休,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
“我不怕谁说话,”她激动地说,“我要看你的伤口,替你敷上草药,这是你的左手做不来的。”
“我对你说,不必要的。”
“那么让我瞧瞧,我才相信。”
她不再多说,拉起他的手。他没有反抗,让她解开了绷带。她看见肿得厉害,害怕得尖声叫道:“天啊!”
“只是肿一点点,”他说。“一天一夜后就会消了。”
她摇摇头,“一个星期内你是无法出海的。”
“我想后天就可以了。再说,这有何关系?”
这时她端来一盆水,重新替他洗过伤口,他像个孩子似的任她摆布。然后,她把草药敷上,炙痛立刻缓和了,她又用带来的麻布条把他的手包好。
绑妥后,他说:“谢谢你。如果你还肯帮忙的话,那么听着,请原谅我今天发狂时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并请忘掉一切。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会发生这种事。你一点错也没有,绝对没有。以后我不会再说话冒犯你了——”
“是我应该向你道歉,”她打断他的话,“我应该好好的对你解释,不该因我的沉默而激怒了你,害你受了伤——”
“你是出于自卫,而我那时候正是应该恢复控制的时候。像我刚刚说的,这点伤算不得什么。不要再说什么宽恕了。你帮助了我,我要感谢你。现在你回家休息吧——还有,那条包巾你可以顺便带走。”
他把它交给她,但她还是站在那儿,显然内心里正在挣扎。终于她说:“你的夹克也因为我而损失了,我知道你卖橘子的钱放在里面。我是在回家路上才想起这件事。我目前无法还你这笔钱,因为我们没有钱,就是有钱,那也是我母亲的。但这里有一条银十字架,是那个画家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留在桌子上的。我向来不去看它,也不愿它放在盒子里。如果你把它卖了——我母亲当时说,它还值几块钱——也许可以弥补,如果尚不够,我想晚上母亲入睡后我会纺纱赚来还你。”
“我不要。”他简单地说,并把她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光亮的十字架推还给她。
“你一定要收下来,”她说,“谁知道你这只手何时才再能赚钱。拿去吧,我永远不再看见它。”
“那么丢到海里去吧。”
“这并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有权收下来,这是我欠你的。”
“权利?我无权拿你任何东西。如果以后遇到我,请你不要看我,不要使我想到你还记得我的不是。好了,我就说到这里为止,晚安。”
他把包巾放进篮子里,把十字架搁在旁边,然后盖上盖子。当他抬起头看她的脸时,吃了一惊。一颗颗豆大的眼泪正滚落她的双颊。她没有伸手揩拭。
“老天!”他叫道,“你不舒服吗?你全身都在发抖。”
“没什么,”她说。“我要回家了!”她摇摇摆摆地走向门口。她忍不住呜咽起来,把前额倚着门框,接着大声啜泣,浑身抽动。但没等他上前扶她回来,她蓦地转身,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我忍不住了,”她哭着,仿佛垂死的人攫住生命不放似的搂住他。“我不能听你对我说好话,教我心怀愧疚地离开。打我,践踏我,咒骂我吧!——或者,如果你真的是爱我,甚至我这般对待你之后还爱我,那么便接纳我,收留我,你要怎样就怎样。就是不要这样子赶我走!”——她喘了口气,又啜泣起来。
他把她搂在怀里,好久没有说话。“你爱我吗?”他终于喊道。“老天爷!你以为这一点伤便要教我心里的血都淌干?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正在我的胸口捶击着,好像要进跳出来,向着你去?如果你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试验我,或是可怜我,那么你去吧,我会忘掉这一切。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痛苦而认为你有愧于我。”
“不!”她坚决地说,抬起头,以濡满泪水的眼睛盯视着他的脸孔,“我爱你,我要向你坦白,只是我一向怕爱你而顽固地反对你。现在我变了,因为当你在街上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再也忍不住不看你。现在我也要吻你,”她说,“当你怀疑的时候,便可以对自己说:‘她吻了我,劳蕾娜只吻她要嫁给他的那个男人。”’
她吻了他三次,然后才放手,说:“晚安,亲爱的。去睡吧!好好照顾你的手,不用送我,因为除了你之外我谁也不怕。”她说罢便溜出门,隐没在墙影里。但他站在窗边许久,眺望着大海,海上的星儿仿佛都在跳舞。
小神父从劳蕾娜跪了很久的忏悔室里走出来,微笑着。“谁会想到,”他自言自语说,“天主这么快就怜悯这颗奇怪的心?我还责备自己没有好好责备过这个顽固的小丫头。我们凡人的眼睛对于天路太近视了。啊,但愿天主保佑他们,也但愿我能活到劳蕾娜的长子代他父亲渡我过海的那一天。唉,唉,骄傲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