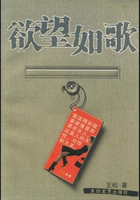因贾母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宝钗等吃过早饭,也到贾母处问过安,返回时,走到分路之处,宝钗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要问你。”黛玉便跟着宝钗,来到蘅芜院中。进到房内,宝钗便坐下笑道:“你跪下,我要审问你。”黛玉不明其意,便笑道:“你这宝丫头疯了!审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你个千金大小姐!好你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什么?你现在实说便罢。”黛玉不解,只管笑,心里也疑惑起来。口里说道:“我何曾说过什么?你不过是要捏我的错罢了,倒是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傻。昨天行酒令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从哪里来的。”
黛玉回想,这才想起来,昨天失于检点,行酒令时从那《牡丹亭》《西厢记》中说出了两句,不觉脸红了,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是我不注意随口说的。你教了我,我再不说了。”宝钗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起来怪生的,所以向你请教。”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给别人听,我以后再也不说了。”宝钗见她羞得这样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再往下追问,只拉她坐下喝茶,款款向她道来:“你以为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孩子。从小七八岁时也够缠人的。我们家算是读书人家,祖父那时也爱藏书。先前人口多,姊妹兄弟在一块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有爱诗的,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偷偷背着我们看,我们也偷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们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这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倒好。男人们读了书仍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何况你和我。就连作诗写字这类事,也不是你我份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的份内之事。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说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反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将书糟蹋了。所以还不如耕种买卖,倒没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对,偏又认得些字,既认得些字,拣那些正经的书看过也罢了,就怕看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垂头喝茶,心中暗服,口内只答应着“是”。
黛玉每年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咳嗽;今年又遇到贾母高兴,多游玩了几次,不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开始咳嗽起来,更觉较往常又重,所以总不能出门,只在自己房中休养。有时闷了,极盼望能有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等到宝钗等人来看望她,说不了三五句话,却又厌烦了。众人体谅她在病中,且平日便形体娇弱,禁不住些许委屈,所以她招待不周,礼数忽略,也都未苛责。
这天,宝钗来看望她,又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来的几个太医,虽然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点的人来看看,治愈了岂不好?每年闹一春一夏,又不是老,又不是小,成什么样子了呢?这样不是个常法。”黛玉道:“没用的。我知道这病是好不了了。且不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样的情形,也可知了。”宝钗点头道:“古人说‘食谷者生’,你平日吃的都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啊。”黛玉叹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以勉强的。今年比起往年又重了些。”说话间,已咳了两三次。宝钗道:“我昨天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都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了。按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主,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便可以养人了。每天早起时,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习惯了,比药还强呢,最是滋阴补气的。”
黛玉叹了口气道:“你平日待人,原本都是极好的,只是我是个最多心的人,只当你是心里藏奸。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劝我的那些好话,我是十分感激的。往日都是我错了,实在误会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姊妹兄弟,长到了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像前日那样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常见她夸你,还不大受用,昨日我亲自经历,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是不轻放你的;你却不介意,反劝导我那些话,可知我竟一直误会了。若不是前日看了出来,今天这话,我也不会对你说。你刚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因我这身体不好,每年犯这个病时,也没什么要紧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儿我又兴出个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姨这三个人即使没话说,底下那些婆子、丫头们,不免会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的一些人,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她们尚且虎视眈眈,背地里说三道四的,何况是我?况且我又不是她们这里的正经主子,只是无依无靠投奔了过来的,她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若还不知进退,何苦叫她们咒我呢?”
宝钗道:“这样说来,我和你也是一样。”黛玉道:“你怎能比我?你有母亲,又有哥哥,在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钱,要走便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全都和她们家的姑娘一个样,那些小人岂有不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不过多费一副嫁妆罢了,如今还愁不到这里。”黛玉听了,不觉脸红道:“人家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难说给你听,你却拿我取笑儿。”宝钗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有我在这里一日,便与你消遣一日。你再有什么委屈烦难的,只管说给我听,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清楚的。只有个母亲略比你强些。咱俩也算是同病相怜。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你刚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天回家去和妈妈说说,只怕我们家里还有,给你送几两过来,每天叫丫头们熬了,既方便,也不必兴师动众的。”黛玉忙笑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如此多情!”宝钗道:“这有什么好放在嘴里的!只怪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只怕你又烦了,我先回去了。”黛玉道:“晚上再来吧,和我说句话儿。”宝钗答应着去了,不在话下。
黛玉喝了两口稀粥,独歪在床上,不料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雨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黄昏,且阴得黑沉,兼着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道宝钗不能前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由得心有所感,不禁发于章句,写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律,为其取名《秋窗风雨夕》。其词如下: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寒烟小院传萧条,疏灯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吟完搁笔,正要就寝,只听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了,只见宝玉头戴大箬笠,身披蓑衣进来了。黛玉看得不禁笑了,说道:“哪里来的渔翁?”宝玉忙问:“今天好些了吗?吃过药了没有?今儿一天吃了多少饭?”一边说,一边摘了笠,脱下蓑衣,又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一照,觑着眼,细瞧了瞧,笑道:“今天气色好了些。”
黛玉看着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着半旧的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穿着蝴蝶落花鞋。黛玉便问:“上面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么?倒也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身是全套的。穿了一双棠木屐来,进来时脱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他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便问道:“是什么草编织的?难怪穿上去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我的。他闲时下了雨,在家也是这样。你若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给你。别的倒也罢了,独有这斗笠有趣,上头这顶儿竟是活的,冬天下雪,带上帽子,就把这竹信子抽了,去掉顶子,只剩了个圈子。下雪时,男女都能戴,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时戴。”黛玉笑道:“我才不戴它。戴上了它,成个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子了。”还不及说完,想想自己的话未经忖度,与刚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莫及,羞得满脸飞红,便伏在桌子上咳个不停。
宝玉却未留心,见案上有诗,便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禁称好。黛玉听了,忙起身夺过来,就灯火烧了。宝玉笑道:“我已经背熟了,烧也无妨。”黛玉道:“我也好些了,多谢你一天来看我几次,下雨也来。这会儿夜深了,我也要歇息,你先请回去,明儿再来吧。”宝玉听了,随手便怀里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金表来,瞧了瞧,那针已指向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进怀里,说道:“是该歇了,又搅得你劳了半天神。”说完,披蓑戴笠出去了,又转身进来问道:“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向老太太回报,岂不比老婆子们说得明白些?”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到了,明天早起时告诉你。你听,雨下得越发紧了,快回去吧。有人跟着没有?”两个婆子在外答应:“有人,外面撑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能点灯笼?”宝玉道:“不要紧,是明瓦的,不怕雨的。”黛玉听说,伸手向书架上把一个玻璃绣球拿了下来,命人点一支小蜡来,递给宝玉,道:“这个又比那个亮些,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一个,怕她们失脚滑倒打破了,所以没带来。”黛玉道:“是跌了灯值钱,还是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习惯木屐子。那灯笼叫她们在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本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了这个,岂不更好?明天再送来。就是失了手也不要紧的,怎么突然又有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宝玉听了,忙接过来,前面两个婆子打伞,提着明瓦灯,后面还有两个小丫鬟打伞。宝玉便将这个灯递给小丫头捧着,宝玉扶着她的肩,一径离去了。
又有蘅芜院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过来一大包上等的燕窝,还有一包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说:“这个比买的好。姑娘说了: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过来。”黛玉道:“回去说‘费心了’。”叫她外头坐下喝茶。婆子笑道:“不喝茶了,我有事先回了。”黛玉笑道:“我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凉夜长,越发好会个夜局,痛赌几场了。”那婆子笑道:“不瞒姑娘,我今年可大沾光儿了。反正每夜各处都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既坐了更,又解了闷儿。今晚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一关,就该上场了。”黛玉听了笑道:“难为你了。误了你发财,冒雨送过来。”便叫人打发了她几百钱,打了些酒喝,避避雨气。婆子笑道:“又破费姑娘赏酒吃。”说完,磕了个头,外面接过钱,打伞离去了。
紫鹃收好燕窝,然后将灯移到帘下,服侍黛玉睡下。黛玉又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慕她有母兄;一会儿又想与宝玉虽平日和睦,终究怕人嫌疑。又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帘,不觉又滴下眼泪来。直至四更时分,这才渐渐地睡了。
宝玉素来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子,尚且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忽见她俩日渐亲密,有些闷闷不解,心想:“她俩平日不是这样的,如今看起来,竟更比别人好了十倍。”
这日,宝钗姊妹进了薛姨妈房内后,湘云便往贾母处来,林黛玉回房歇息。宝玉过来找黛玉,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也曾说了几句明白的取笑,你还曾恼我。如今想来,还有一句不理解,我这就念出来,你讲给我听听。”黛玉听说,便知内有文章,笑道:“你就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得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了。‘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七字,原是现成的典,难得她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得有趣儿。是几时接了?你说给我听听。”黛玉听了,不禁笑起来,笑说道:“这原本问得好。她问得好,你也问得好。”宝玉道:“先前你只怀疑我,如今你也没得说。反是我落了单。”黛玉笑道:“哪知她竟真是个好人,我平日只当她藏奸。”便把说错了酒令,宝钗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地告诉了宝玉。宝玉这才知道缘故,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呢,原来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拦时’就接了案了。”
黛玉一时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滴下泪来。宝玉忙安慰:“又自寻烦恼了。你看看,今年越发比去年瘦了,还不好好保养着!每天好好的,必要自寻烦恼哭上一回,才算过完了这一天。”黛玉拭泪道:“近日来我只觉得心酸,眼泪却像比去年少了些的,心里只是酸痛,眼泪却流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习惯了,心里怀疑的,眼泪岂有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