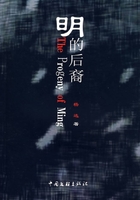上尉从小就被训练成一匹战马。他的第一个主人是个骑兵队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他说自己很喜欢跟别的马儿一起接受军事训练。他们一起小跑,一起向左转、向右转,一听到命令马上就得停下来,号角响起或是长官发出信号就得全速往前猛冲。年轻的时候,他是一匹黑色的、有铁灰色花斑的马儿,长得非常英俊。他的主人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绅士,一直都很喜欢他,而且非常细心、友善地照料他。他跟我说,他觉得战马的一生非常舒适。可是,当他要被送到国外、得坐着大船漂洋过海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那段经历,”他说,“简直可怕极了!我们当然没法自己从陆地走到船上去,所以,他们先用结实的皮带捆住我们的身体,接着不顾我们的挣扎就把我们吊起来,我们在半空中晃来晃去,越过水面,最后降落在军舰的甲板上。我们被安置在船上的小隔栏里,长时间看不到天空,也没法舒展一下腿脚。遇到海上刮大风的时候,船就摇晃得厉害,我们也跟着来回摇晃,那种感觉真糟糕。最后,船终于靠岸了。我们再次被吊起来,从船上摇摇晃晃地拉到地面上。当我们又一次感觉到脚下坚实的大地时,我们高兴极了,喷着鼻气,欢快地嘶叫着。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个国家跟我们自己的国家完全不一样,除了战争,我们还得忍受别的煎熬。许多人很喜爱自己的马儿,不管碰上雪天、雨天,还是别的什么恶劣天气,他们都尽力使马儿过得舒服一些。”
“那么战争怎么样?”我问,“是不是比这些还残酷?”
“呃,”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听见号角的声音,然后大家集合起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时候,我们得站上好几个小时,等着冲锋的命令。一旦冲锋的命令传达下来,我们就憋足劲朝前冲,好像前面根本没有炮弹、刺刀或子弹什么的。我相信,只要能感觉到我们的骑手坚定地坐在马鞍上,他们的手牢牢地抓住马笼头,我们就不会感到害怕退缩。就连那可怕的炸弹从空中飞过,炸成无数碎片,我们都没害怕过。
“我,跟随我那高贵的主人,一起参加了好多场战斗都没有受伤。我看见过很多马儿被子弹射中,被长矛刺伤,被军刀割伤。他们把受伤的马儿留在战场上,或是让他们在伤痛中死去。可是,这些都没有让我感到害怕。主人用欢快的声音鼓励士兵,让我觉得好像我跟他都不会战死似的。主人指挥我前进的时候,我非常信赖他,随时准备朝敌人的炮口上冲去。我看见许多勇敢的士兵倒下了,还有许多受了伤,从他们的马鞍上摔下来;我听见许多垂死的人在惨叫、呻吟;我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奔跑,还得避免踩到受伤的士兵或战马。这些都没有让我觉得害怕,直到那可怕的一天到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说到这,老上尉停顿了一下,长长地吸了口气,我等着他继续讲下去。
“那是个秋天的早上,破晓前一个小时,我们的骑兵团跟平常一样,不管今天的任务是战斗还是等待,都已经武装完毕。士兵们站在自己的战马身边,等待着上级下达命令。天渐渐放亮,军官们好像很兴奋。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的时候,我们听见敌人朝我们开火了。
“接着,有一个军官骑着马向士兵们传达命令。不一会儿,所有的士兵都已经骑到马上,每一匹战马都期待主人甩动缰绳,或是磕碰脚跟,发出冲锋的信号。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战马,除了咀嚼一下马嚼子或不耐烦地甩脑袋外,全都安静地站着。
“我跟亲爱的主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所有人都一动不动站着,提高警觉。他把我被风吹向一边的鬃毛稍稍梳理了一下,拍拍我的脖子,说:‘我们今天得好好打一战啦,巴亚德,我的骏马。我们要全力以赴。’我觉得,那天早上,他把我的脖子抚摩了很长时间。他显得很安静,好像在想什么问题。我喜欢他的手抚摩我的脖子,我自豪、欢快地挺起胸膛。我静静地站着,因为我了解主人的心情,知道他什么时候喜欢我安静,什么时候喜欢我活跃。
“我没法说清那天发生的事。可是,我还记得我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冲锋。我们要穿过敌人大炮右前方的山谷。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轰轰作响的枪炮、不停地朝我们开火的步枪和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的子弹。以前我从没在这么激烈的炮火中前进。子弹和炮弹从我们的左边、右边、前面射过来。许多勇敢的士兵倒下了;许多战马也摔倒了,把背上的主人扔到地上;许多马背上没有士兵的战马疯狂地到处乱跑,可没有骑手的指挥,他们又都吓坏了,只好紧挨着同伴,朝前冲锋。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没有人停下来,没有人退缩。我们的队伍每分每秒都在缩小。当战友倒下去时,我们就互相靠拢,团结起来。当我们靠近笼罩在白色硝烟中的大炮以及时而闪现炮火的红光时,我们并没有放慢脚步,反而加快速度朝前跑去。
“我的主人,我亲爱的主人,高举着右手,激励着他的士兵向前冲去。这时,一颗子弹从我脑袋旁边擦过,射中了主人。他没有叫出声来,可是,我感到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我试着放慢脚步,这时,军刀从他的右手滑落下来,缰绳也从他的左手松了下来,他的人往后一仰,从马鞍上摔了下去。其他士兵飞快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冲锋时猛烈的势头使我不得不离开主人落马的现场。
“我想待在主人身边,不想让他受到其他战马的践踏。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我已经没有主人,也没有朋友了。在那个大屠杀的现场,我感到很孤单。突然间,我觉得很害怕,我吓得浑身发抖,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我也像自己以前看到过的战马那样,拼命地想要回到军队中,与其他战马一起奔跑。可是,战士们拿着军刀把我赶开。就在那时,有一个已经死了战马的士兵抓住我的笼头,骑到我的背上。驮着新主人,我又可以继续向前冲锋了。可是后来,我们英勇的骑兵队战败了,那些经过激烈的战斗还能活下来的士兵都回到原地。有些战马伤得十分严重,因为失血过多没法移动;有些战马试着用自己的三条腿往前挪动;还有一些他们的后腿被子弹射中,就用前腿挣扎着爬起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凄惨的呻吟声,也忘不了人们对他们弃之不顾时他们眼里流露出来的哀求眼神。战斗结束之后,受伤的士兵被带回去,战死的士兵就地埋掉。”
“那么受伤的马儿怎么办呢?”我问,“让他们等死吗?”
“不,随军的兽医身上都带着手枪,他们到战场上,把那些伤得很重、没法救活的马儿打死,把有些只受了点轻伤的马儿带回医治。可是,大部分战马从那天早上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在我们的马房里,只有四分之一的战马能够活着回来。
“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主人。我敢肯定,他从马鞍上摔下来就死了。我再也没有爱过别的主人。后来,我又参加了很多场战斗,只受过一次轻伤。战争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了英国,身体又像我刚出发时那么健康、强壮了。”
我说:“我以前听人们谈论战争,他们好像觉得战争是件好事。”
“啊!”他说,“我想他们肯定没亲眼见过战争。要是没有敌人,只有军事演习和阅兵式,那么战争当然很好。是的,确实很好。可是,当成千上万英勇的士兵和战马战死沙场,或者一辈子落下残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挑起战争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回答道,“马儿没法理解这种事。可是,我们大老远地漂洋过海去杀死他们,要是这么做没错的话,那么敌人一定是很坏很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