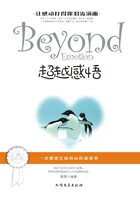还有一种开火车式的驾驭方式。这些赶车人大多数来自城里,他们自己从来没拥有过一匹马儿,经常是坐火车出门。
他们好像总是把马儿当成火车,只不过体形小了点。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只要自己付了钱,马儿就得听他们的话:要他们走多远就多远,跑多快就多快,拉多重的东西就多重的东西。不管道路是潮湿泥泞还是干燥整洁,是布满石头还是平坦通畅,是上坡还是下坡,都一个样——你必须得前进、前进、再前进,不能放慢脚步,不能休息,也得不到一点关心。
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下车去爬那些陡峭的山坡。哦,不会的,他们既然付了钱,租了马,就要一直坐在车上!那马儿呢?哦,反正他已经习惯了。要是不把人带上坡,那要马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走路!真是开玩笑!于是,马鞭一次次抽上来,缰绳也被拉得紧紧的,还常常有难听的话等着我们。“快走,你这头懒畜生!”紧接着,又狠抽我们一顿。那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灰心丧气了,可还是没有怨言、非常顺从地尽量做到最好。
这种开火车式的驾驭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容易消耗我们的体力。在这种赶车人的驾驭下,我只能走十英里;可是,在一个懂得体谅马儿的赶车人的驾驭下,我能走上二十英里,而且不太会消耗我的体力。
还有一件事——不管下坡的路有多陡峭,他们几乎从不拉刹车闸,因此常常会发生重大事故。就算他们记得拉刹车闸,可到了山脚却又忘了松开刹车闸。这样的事情我碰到过不止一次。当时,我拉着一个轮子被车闸卡住的马车,吃力地爬着下一个山坡,爬到一半的时候,赶车的人才想起没有松开刹车闸。那对马儿来说,真是非常吃力。
这些伦敦佬不像绅士那样,一开始先让马儿走得慢一点、稳妥一些;而是还没出马房前面的院子,就开始让马儿全速奔跑。当他们想停下来的时候,先是用鞭子抽我们一下,然后猛地拉住缰绳,差点让我们一屁股坐下来,嘴巴也被马嚼子划破了。他们把这种紧急停车叫做干净利索!转弯的时候,他们的动作很猛,好像路上没有左行道和右行道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和罗伊已经出去跑了一整天。(罗伊通常跟我配对拉车,他是一匹善良、诚实的马儿。)赶车人对我们一直很体贴、温柔,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傍晚的时候,我们迈着轻巧的步子往回赶。前面有一个左转弯,因为当时我们离旁边的树篱很近,还有很宽的地方可以走,所以赶车人并没有拉住我们。当我们接近转弯口的时候,我听见前面山上传来一匹马和两个车轮朝我们快速跑来的声音。树篱很高,我什么也看不清。可是,我们很快就碰上了。我很幸运,站在树篱的那侧;而罗伊站在车辕右侧,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马辕可以保护他。对面驾车的人笔直朝转弯口冲过来,等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把马车拉到靠自己的那边了。整个马车一下子撞到罗伊身上,马辕正好撞在他的胸口上,他跌跌撞撞地发出一声惨叫,那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一匹马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根马辕撞断了。原来这匹马儿跟我们是同一个马房的。这个年轻人很喜欢让他拉着轮子高大的双轮轻便马车。
这个赶车人就是那种冒失的、没有经验的家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走路的哪一侧;或者他知道,可他根本不在意。可怜的罗伊,他的皮肉已经裂开,还在不停地流血。他们说,要是受伤的地方再稍微过去一点,那他准没命了。可怜的家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这也算得上是幸运的话。
罗伊的伤口花了很长时间才愈合,之后,他就被卖去拉煤车了。只有马儿才知道,在陡峭的山坡上,拉着煤车上坡下坡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我以前看到过这种场景:马儿不得不拉着超重的双轮马车下坡,却没有刹车闸,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辛酸。
罗伊受伤以后,我就和一匹名叫佩吉的母马配对拉车,她就住在我旁边的隔栏里。她很强壮,体形也不错,浅褐色的皮毛上还有漂亮的斑点,鬃毛和尾巴都是深棕色的。她的血统并不纯正,可是长得相当漂亮,还很温顺、听话。可是,她的眼神很焦虑,我知道她碰到过麻烦。第一次跟她一起出去,我觉得她的脚步很奇怪。她看上去像是在小跑,又像在中速跑——先小跑三四步,然后向前小跳一步。
跟她一起拉车很不舒服,也让我觉得很不安。等我们回到家,我就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走路的姿势这么奇怪、这么难看。
“啊!”她说话的口气很不安,“我知道自己的脚步很糟糕,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真的不是我的错。只不过是我的腿脚短了点。我站着的时候几乎跟你一样高,可是你膝盖以上的腿比我长了三英寸,你的步子当然可以比我迈得更大,走得也更快了。你瞧,我也不想长成那样。真希望我的愿望可以实现,能有四条修长的腿。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的腿脚太短了。”佩吉沮丧地说。
“可是,怎么会这样呢?”我说,“你这么强壮、温顺、听话。”
“哦,你瞧。”她说,“人们总想让马儿走得快些,要是他的马赶不上别的马,那就只有挨鞭子,一直不停地挨鞭子。所以,我不得不尽量赶上其他的马儿,于是就养成了用这种难看的步子走路的习惯。可我并不总是这样的。当我跟第一个主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总是跑得很规矩,而且他骑马的时候也并不匆忙。他是乡下一个年轻的牧师,也是一个善良的主人。他得在两个教堂之间来回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可他从来不会因为我走得慢而骂我或是鞭打我。他非常喜欢我。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他身边,可是他得离开那儿去大一点的城里,于是我就被卖给一个农夫。
“你知道,有些农夫是极好的主人,可我觉得这个农夫是个很差劲的人。他一点都不关心怎么养好一匹马,怎么赶好车,只关心怎样才能让马车跑得快些。我已经尽量跑得很快了,可这还是不够,他一直用马鞭抽打我,所以我就养成了这种向前小跳的赶路方式。在赶集的那几天晚上,他通常在旅馆里待到很晚,然后驾着我一路飞奔回家。
“在一个黑漆漆的晚上,他像往常一样驾着我飞奔回家。突然间,车轮被大路上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马车立即翻倒在地。他被远远地甩了出去,胳膊也擦破了,我想可能还摔断了几根肋骨。不管怎么样,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在一起,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可是,你瞧,要是人们想让马车跑得快些,那么对我来说到哪儿都一样。我真希望自己的腿脚能再长一些。”
可怜的佩吉!我为她感到难过,也没法安慰她,因为我知道想让步子小的马儿赶上那些步子大的马儿是多么困难。他们忍受了无数的鞭子,可还是没用。
她常常拉四轮马车,因为脾气温顺,深受女士们的喜爱。那次聊天以后,过了段日子,她就被卖给了两位女士。她们自己赶车,想要一匹安全、可靠的好马。
后来,我在乡下碰见过她几次。那时她的步伐很稳健,看上去也很漂亮、知足。我很高兴看见她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这是她应得的。
佩吉离开我们以后,另一匹马儿取代了她的位置。他很年轻,可是因为胆小、容易受惊而得了个坏名声,也因此离开了原来那个不错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胆小。
“哎,我自己也不清楚。”他说,“我小时候就很胆小,被吓到过好几次。要是我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就会转过去看看——你瞧,我们戴着眼罩就没法看清,除非转过去才行。而这时,我的主人老是鞭打我,这让我常常受到惊吓,没法不害怕起来。我想要是他能让我安安静静地看清楚前面的东西,知道它们不会伤害我,那我就不会那么容易害怕了,也会慢慢地适应过来。有一天,他跟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一起驾车。突然,我旁边吹过一大张白纸或是白布什么的,我感到很害怕,朝前跳了一下——我的主人又像往常一样鞭打我,可是那位绅士大叫起来:‘不对!不对!你不该因为马儿胆小而鞭打他们。正因为他们胆小,所以才容易受到惊吓。你这么做只会让他们更害怕,让他们的胆子更小。’所以,我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的主人那样。我并不想让自己感到害怕。可是,要是不让马儿了解事情的状况,那么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呢?对于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从来不会感到害怕。我在一个庄园里长大,那儿生活着很多鹿。当然,我对他们很熟悉,就像熟悉绵羊和奶牛一样。可是他们并不是很常见,我知道有不少敏感的马儿就很怕他们,经过养鹿的小牧场时会乱踢乱跳。”
我知道我的伙伴讲的都是事实。我希望每一匹马小的时候都能碰到像格瑞农场主和戈登老爷那样的好主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能碰上懂行的赶车人。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套上一辆轻便马车,被带到普特尼大街的一户人家前,从里面走出来两位绅士。高个的那个走到我身边,检查了一下我的马嚼子和马笼头,还用手转动了一下马轭,看看它是否系得合适。
“你觉得这匹马需要马衔吗?”他问马夫。
“哦!”他说,“我应当说,他没有马衔也走得相当好。他的嘴巴出奇的敏感。他精力旺盛,也没什么缺点。只是我发现人们通常喜欢用马衔。”
“我不喜欢。”那位绅士说,“最好把它拿掉,给他戴上缰绳。让马儿的嘴巴舒服一些,这有利于赶远路,是这样吧,老伙计?”他说着,拍拍我的背。
他接过缰绳,两个人就上马了。我至今仍记得,他让我转身的时候动作是多么轻巧。他把缰绳轻轻地抖了一下,用马鞭轻轻地碰一下我的背,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我弓着脖子,迈着最佳的步伐上路了。我发现后面的这个人知道怎样驾驭一匹好马。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这让我非常高兴。
这位绅士很喜欢我,他坐在马鞍上试了我好几次,然后说服我的主人,把我卖给他的一个朋友。他这位朋友很想找一匹可靠、友善的马儿当坐骑。所以,夏天的时候,我被卖给巴瑞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