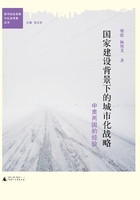南山玉走进诊室时,见一个老妇人坐在那里,新来的助理印度姑娘丽达站在老人身边,正在给她戴衣罩。这是个保养很好,颇有风度的老妇人,尽管老了,还有清秀的眉眼和很好看的嘴唇。南山玉微笑着说,今天看哪颗牙?老人说右上第一颗。不知是牙齿掉了一个茬儿,还是以前堵的银汞掉了。南山玉说那就先做个X光片吧!准备工作时南山玉问,是吃什么东西掉的?很硬的坚果吗?老妇人说不是,只是吃苹果,感到里面好像有沙子一样,我还想,苹果里面怎么会有沙子呢?南山玉脸上保持着一种亲和的微笑,说有人吃面包也会掉牙呢。不一定是硬东西,也是因为牙齿松动了,本身有问题了。
X光片很快出来了,南山玉把放在微机里的牙片给老妇看,老人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牙齿,吓了一跳,说这是我的牙齿吗?真是丑陋啊。南山玉也回头看这一排牙齿。因为牙根萎缩了,嵌在牙龈里的,是一排枯萎和残缺不全的阴影,牙根变得很细很脆弱的样子,在灰色的没有生命的底片上,能看出衰老和死亡的痕迹。老妇人说这怎么是我的牙齿呢?我以前的牙齿是珍珠贝壳般闪光的牙齿。脸上一瞬间就黯然神伤。叹一口气说,人哪,不要老,老了一点儿都不好。且不要说什么色衰爱驰,就是自己的牙齿,也不由你做主,丑陋得心惊肉跳。
这是南山玉牙医学院毕业后到附属医院实习的第一周。历经五年的艰苦学习,终于可以行医的快乐,并没有被老妇人一番人生感悟所湮灭。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南山玉望着地铁里行色匆匆的行人,却不知不觉想起老妇人看到自己牙根时那惊骇的面孔。长长的电梯一上一下,南山玉正好可以俯视那些向上滚动的人流。在八月的蒙特利尔,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亚洲人,都有一张疲惫的睡眠不足的面孔。南山玉在感慨这行色匆匆的人流时,突然感慨人生苦短岁月无常,同时对这个环境有了一种逃走的渴望。于是,在他迈进地铁的一刹那,他有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请假两周,去慕尼黑去看他的妻子冷梅。
他与冷梅约好在维也纳见面。原因是他与冷梅都喜欢古典音乐,而维也纳是他们心仪已久的圣地。南山玉从蒙特利尔出发,在一片苍茫中飞机进入了欧洲的门户——阿姆斯特丹。重上飞机时,就是在欧洲上空飞翔。靠近维也纳时,南山玉很惊讶地发现,在上空看维也纳,比他印象中破旧而拥挤。一瞬间,他居然有重回亚洲大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吓了一跳。当他在这里时,他一直是视它为异乡的。
是不是个人感受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辗转挪移呢?那就是说人的感情也很难恒久稳定了?在急于与冷梅相会的时刻,突然而来的感慨让南山玉在惊讶中有一丝丝的不快。他把脸贴在舷窗,俯视下面的风景,以冲淡这突如其来的不快。
冷梅从慕尼黑赶来,只用几小时的路途,所以比他先到。当南山玉看到在机场下层等待的冷梅时,心中涌起一股热情的潮涌。冷梅穿着浅绿色的紧身牛仔裤和一件绒黄色的毛衫,站在一排自动出票机旁边,显得格外亭亭玉立而充满生机。她靠在身后一个绿色的旅行包上,好像一株春天的树,又像一簇迎春花树。南山玉禁不住三步两步跳下电梯,在偌大的机场里奔跑起来。
然后是忘乎所以的拥抱。南山玉把冷梅抱在怀里时,如果有人问他,你想到什么,南山玉会用白边眼镜后面那对真诚的眼睛告诉你,我什么都没想,因为快乐的脑子是空白的。
他们的计划是在维也纳玩儿三天,然后沿途去布拉格和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之后,他们进入德国,到冷梅生活的慕尼黑。他们把最后一周留给慕尼黑,留给平静而休闲的时光。在那里,他们可以谈谈未来——是冷梅来蒙特利尔,还是南山玉寻找机会再返欧洲。
两个人都是正在脱贫的学生一族。当年从国内考出国,因为欧洲留不下,南山玉才转道去了北美。冷梅当时学业未完,两人才棒打鸳鸯各一方。本来打算在北美会师,如今冷梅意料之外的一份工作,给两个人出了难题。
坐机场大巴到市里已是黄昏,路过一个街角看见一家中餐馆,大红灯笼高高挂。南山玉一如既往地肩负重担,一人背着两个旅行包,手里拎着两个旅行箱,还不忘一只手拉着冷梅的手。冷梅却坚持背自己的旅行包,在她的坚持中,南山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冷梅的理由是自己也有手和肩,南山玉却看到冷梅长大了的精神。的确,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女孩子们都是自己背行李,但是在中国,女孩子却是喜欢让男人们帮忙,甚至是一只小小的手袋。
南山玉端详着冷梅,他看到这个小妻子越来越漂亮了。也许是因为稍胖的原因,冷梅比三年前显得婀娜多姿,也丰腴秀美,尤其是眼角眉梢,带有一种成熟女人特有的丰韵。
与三年前相比,三年前的冷梅很骨感,而现在的冷梅就丰满一些了。让南山玉开心的是,冷梅看见他,居然还有一份新娘子的娇羞,南山玉盯着她看时,她就嗔道,看什么?然后转过身去。
他们预订的旅馆是学生宿舍,空间很小。这对南山玉和冷梅不是问题,两张分开的床,有用的也只有一张。黑暗中南山玉能感到冷梅的半推半就或者说是欲拒还迎。三年的分离,南山玉能理解新婚之后漫长的分别意味着什么。新婚的生涩还停在那里,他们在黑暗中重新享有的其实是新婚之夜。因为新婚之后他们没有熟稔没有默契就分开了。那场婚礼好像只是为了当年即将分离下的一份决心。他们在一起短短的三天,然后是漫长的三年。所有的肢体语言都生疏了,留下的是某些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回忆。后来回忆也远了,好像一幅画因为年代有点褪色,在南山玉的回忆中,还因为想象增加了某些玫瑰的色彩也未可知。如今月光是那样明亮地照着,他们就这样相拥在一起,这才是今天真实的图画,也是南山玉渴望已久的图画。
之后就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游玩,白裤黑衫的南山玉与彩裙白衫的冷梅牵着手走在维也纳古老的街道上。有时出来得早,能闻到古老建筑与街道中那种气息,那是因为人居住的时间长而散发出的气息,一种古老的烟火油腻的气息。而这种清晨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嗅到的隔夜的热闹,隔年的温暖,还有跨越时间的人文气息,让南山玉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的故乡。在清晨帮妈妈把小食摊摆在街头时,城市还像一个困乏的老人一样安静地睡着,然而,你依旧能闻到他的体温,因为你依然在他的怀抱中,而这时的气息,只是他白日里被人潮的涌动遮盖的气息而已。也许白天被忽略不计了,但是,当他睡着时,他的精神,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依然在那里,从没有遗失过。
南山玉被这种熟悉的气味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在北美的三年,他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流连在维也纳的剧院和金色大厅之间。对于这座皇宫之城中的皇宫,他们倒没有多少兴趣。那些死去的政治和皇帝好像从没留下来,南山玉和冷梅最早的接触就是对艺术相同的爱好,莫泊桑的喜剧,歌德的《浮士德》,还有马拉的乐谱,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曾来到这里,为艺术孜孜不倦。
中饭他们就那样站在某个街角,一块披萨一桶可乐。他们看重的是那份下午茶,一定要去一个好的咖啡店,要一杯卡布奇诺和一块甜点。
冷梅点甜点的熟稔程度让南山玉惊讶,而喝咖啡时她对黑咖啡的偏爱也让南山玉感慨。南山玉记得第一次带她去咖啡店时她狼狈不堪的样子。那一杯咖啡,她兑了半杯百分之十的奶油,后来咖啡杯泛出发白的汁液,连咖啡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你已经完全欧化了。南山玉感慨说。
是啊。冷梅笑道。笑的时候,嘴角现出两个圆圆的小酒窝。咖啡不喝不行,上课坚持不下来呀!你知道的。她简短地说。
已经完全是那个样子了?南山玉问。
是的。完全是了。
他们相视而笑。那个样子,是冷梅刚到欧洲时对南山玉的定义。那时他们还不相识。南山玉因为来得早,已经染上了咖啡的瘾。每天早上去上学都看到他端着一杯咖啡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
冷梅就对室友小柳说,那个高个子的男生,她顿一下,说,他是中国人吗?小柳说是啊,医学院的。大概大三了吧。怎么,他不像中国人?冷梅说也不是,就是他那个样子——小柳探头向楼下望,说什么样子,就见南山玉端着一杯咖啡匆匆而过。
于是这就成了他们的笑谈。中国学生很少是那个样子,那需要最少两年旅欧经历。
告别维也纳后他们乘车去布拉格。只是一辆小巴,车上人不多。到捷克境内时上来两个胖胖的警察,简单地看了一下证件。车子在夏天的原野上驰骋。一望无际的原野在八月里居然有了干草那样的金黄。在后来的岁月里,每次南山玉想起这段往事,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天阳光下金黄色的原野。那在东欧应该是晚秋的颜色,为什么一次次地出现在自己盛夏的记忆中?是当时自己那种温暖干燥的收获一样的心情,还是当真在捷克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着这样一片金黄色的原野?
在金黄色的原野上,还有着那些零零散散的农舍,那些暖色调的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栋栋盛满了幻想和幸福的童话,在南山玉的记忆中泛出一层层美丽的涟漪。那时南山玉还不知道这种丰富的阳光意味着什么。进入捷克,进入布拉格,进入德国,这在当时看去完美无瑕的计划,正在把他和冷梅带进一段凄美的时间。那金黄色的美景,是南山玉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后来,在他的生活中他努力去找,却再也没有那样的一份金黄色了。
是的,越接近德国,南山玉就越感到某种不安。开始时他怀疑自己多疑,但是,他在冷梅的行为举止中越来越发现了某种怪异。越靠近德国,冷梅的情绪越起伏不定,喜怒无常。对南山玉的态度变化越大。在布拉格他们遇到的那个高个子男子又一次在他面前出现。在查理四世大桥,那个高个子男子细瘦而文质彬彬,正在桥头的一个画家前面坐着,面对着那十六孔潋滟的波光之桥,面对着他和冷梅即将走过的地方。
南山玉第一次感到心中惴惴不安。
在德国,他和冷梅第一次去冷梅的公司,在冷梅的办公室门前,他又遇见了那个人。这是查理,他在心里重复他的名字。
冷梅说我要去老板那里一下下,就回来。
冷梅回来时,南山玉看到冷梅脸色绯红。冷梅的眼中流光溢彩,南山玉心中的痛,是同他在一起,冷梅从未有这样的目光。
回家后冷梅把头发挽在脑后,只一下,就放下了。她满面羞红地看到,耳环落了一只。
南山玉什么也没问。
离开欧洲时,南山玉发现自己在订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落地在维也纳,回程票应该定在慕尼黑,但他却把回程票也订在了维也纳。
冷梅说我会给你写信。南山玉笑一笑。他回过身,把过去和未来都放在一起,塞进行囊。他想,为什么要说呢?这样不是很好吗?
语言,是用于陌生人的。爱人之间,只有肢体语言。或者,我们用眼睛交谈吧!如果你躲开了,我们就不再相爱了。
与冷梅告别之后,他只身上了去维也纳的夜行列车。
南山玉坐在夜行车上,回想自己的三周之旅。他想起维也纳的新婚之夜,想起伏尔加河的波光。布拉格今夜的上弦月,应该已经从桥下移到了中天,而紧紧追随着月亮的土星,应该也在此时更加明亮,而位置也开始在月亮之下了吧!那一夜的月光中,谁能说那样的时光能够永驻呢?就像永远流动的恒河,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同一条河流里两次。
对面的女孩又一次离开了座位。再回来时,她的头顶顶满了卷发卡,睫毛也卸了下来,由刚才的艳光四溢的妖艳女孩,一下子变成一个睫毛光光,头上缠满塑料卷的妇人。她像在自己家里上床一样,把膝盖曲起来,有些污了颜色的白色衬裙就那样带着某种气息裸露出来。对面的流浪汉用盯着猪肉卷或牛排一样的眼光贪婪地盯着那女孩放荡不羁的身体,壮实的下颚明显地紧咬着嘴唇。南山玉把眼睛挪开,注视着窗外。
窗外的欧洲大地,无知无识地沉入茫茫黑夜。没有明亮的干草,也没有金黄的芳香,甚至令人心酸的往事,在这一瞬间,也沉入了生命的谷底。南山玉知道,这一瞬间,只有这一列坐满了贫穷、贪婪、欲望和及时行乐的夜行车,轰鸣着在这沉睡在谷底的大地上驰骋。夹坐在这充满俗世欲望的窄狭空间中,南山玉的心突然有一种饱胀的不适,他站起来,跨过横七竖八伸展开来的胳膊和腿,走到车厢之间的地方,仰头望着夜空。出乎意料,他居然在列车飞驰的瞬间,看到了上升的月亮和她身边紧紧相随的土星。那么,来自火星的男人和来自金星的女人呢?南山玉仰起的头颅看不见他们,只感到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庞。
曾经完美的牙齿的模式,就那样不堪一击地衰老如断壁残墙。南山玉知道,这列车会一直驶向那个温婉而风韵犹存的老妇人,和那让她惊骇的牙齿。当然,此时的南山玉的爱情的牙齿,还别有一番“拔掉了还痛”的空洞。
(发表于《世界华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