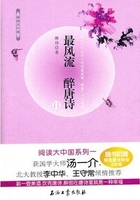我又重新检查起柜子来,虽然遭受的打击不小,但毕竟柜子还没有检查完。按着顺序我来到了最后一个检查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室。在此前多个房间里的检查中,除了卫生间里传来的抽泣声,我一无所获。卧室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里面藏着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银行卡,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证件,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还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摆在弗吉尼亚的梳妆台上,上面还摆着她中意的第五大道香水,这些东西都完好无损,摆放的样子就像我离开时的一样。正因为我知道卧室里的柜子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大干一场,尽管医生叮嘱我不能过度劳累,而我又感觉此时实在支持不下去,又快昏倒了。我还是集中意志去检查了,准备投入我全部的精力去检查。而结果是,我没费多少精力,只是打开了所有柜子的门,用最少的消耗达成了最终的目的——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即弗吉尼亚藏在哪儿的问题。我当然没有在柜子里发现弗吉尼亚,我只是发现柜子里空了一大半,她的几乎所有衣服都不见了。她只留下了一套睡衣,那是她唯一一套,只有一半被胡乱地挂在衣架上,还留下了所有羽绒服和防寒服,它们在衣柜里东倒西歪。柜子里那个樱桃红的行李箱也被拖走了。看上去她走得相当匆忙,连睡衣也没有拿,这代表她当时没有考虑到睡觉的问题,或者没有心思去考虑睡觉和住宿这些细节。果然,我去卫生间看了看,她没有拿走牙刷、牙膏、牙线和漱口水之类的洗漱用具,毛巾也还安然地挂在那儿,化妆品和护肤品一件也没有拿走,这不像是去旅游的样子。至于羽绒服和防寒服,我认为她是嫌这些东西过重,而不是打算很快就回来,看看现在反常的天气,这些东西迟早会用上的。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是整个屋子有东西不见了,那肯定是弗吉尼亚拿走的,这些柜子里充满了香水味。我打开了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里面显然被翻过,东西都明显移动了位置。我快速而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现金一分都没少,后来我又出门去查看了卡上的余额,发现金额也没有少,这说明弗吉尼亚没拿钱。但她拿走了她的护照,另外,驾照也在她身上。
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不论我再怎么呼喊,弗吉尼亚肯定都不能回答我了。她并没有在生气,而是离家出走了,原因不明,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我不知道。她可能在我早上还在上课时就走了——但今天早上我和她告别时她没有任何异样;也有可能在我昏倒后送往医院时就离开了,不管我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关她的事了。不管怎样,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仍然是找到她,把整个事情弄清楚,我只要求这样,也许就我现在的状况来说,放走她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精疲力竭地走到客厅,坐到了沙发上,按住腹部疼痛的地方。我已经无法忍受了,但我还是要找出弗吉尼亚,用这有限的时间。我环视周围,四周的场景没有任何改变,如果她从这个屋子里离开了,眼前平静的景象就像她只是出去散步一样,一到点她就会回来。
我像躺在躺椅上那样舒服地躺了一会儿,可能二十分钟,也可能有半个小时,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它在我现在所拥有的时间里已经算很长的了。我把身体靠在沙发上,借此恢复精力,我稍微感觉好了点,但疼痛还是在向我肆无忌惮地进攻,这是躲不掉的。在这段有限的休息即将结束时,我听见有人按门铃。门铃响声到后来变成了急促的敲门声。最开始,我告诉自己弗吉尼亚这时候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个行李箱,她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可能她是到某个隔得较远的城市去面试去了。在我艰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蹒跚着脚步去开门的那段路程里,我又推翻了之前的猜测,我得让自己死了这条心,说不定门外只是个问路的路人,或者是来收各种账单的工作人员。好吧,人就是那么奇怪,当我越靠近那扇门时,门外的人就越好像是弗吉尼亚,明明只是一个平常的开门动作,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紧张,以至于我忘记了疼痛。所有人在现实和理想作斗争的时候,都会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例外,于是我屏住了呼吸。
我打开了门,看见缝隙里最先出现的是棱角分明的肩膀,穿着西装,我一下就释然了。来人既不是弗吉尼亚,也不是某个过客,这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是冲着我来的。那么就让他进来吧,现在我已经无所依靠,也无需害怕了。门外那个人似乎对我开门的迅速很惊讶,他愣了一下。随后我转过身把地上散落的苹果捡到了塑料袋子里,放到了鞋柜上,再从鞋柜里胡乱拿出一双拖鞋,蹲下身,摆在了我的旁边。来人一跨步直接把脚塞进了并不合适的拖鞋里,这时候我也站起来了,于是我看清楚了他的样子,这人是菲利普,我的上司,也是一位比我身强力壮的同龄人。他面露尴尬,欠身对我笑了笑。
“请进。”尽管对他的造访我并不欢迎,但我还是乐于对他展示我的绅士风度。
我们一同来到昏暗的客厅,天色渐渐暗下来,但我没有打开客厅里的吊灯。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景象,表情看上去没有太多波澜,好像只是路过一个地方,象征性地看看那个地方而已。我邀他来到用餐的角落,然后我们面对面在餐桌旁坐下,我打开了餐桌旁边的一盏落地灯。屋子里依然很昏暗,昏黄的灯光照在我俩脸上,在他脸部轮廓上投射出阴影,我们就像两个自闭阴暗的男人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谈论女人一样。
他把拳头放在嘴边,轻轻咳嗽了几声,说:“校长让我代他来问候你。”
我的心情异常烦躁,想到弗吉尼亚,想到接下来的混乱而庞杂的事,还有一堆连缀成网的人际关系,想到屋子里一些还没被我注意的蛛丝马迹。“谢谢他。”我说。
“你脸色不怎么好,回来后感觉怎么样?”我感觉那深邃的眼神此刻正盯着我,于是我抬起头,我们的眼神撞在了一起。这也代表了我们对话的开始。
我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不是这个,而是另外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无心去知道。但菲利普不这么认为,他热衷于争权夺利,尽管他是在一个地域有限的校园里。有时候,人就是那么无奈,明明脑子里自始至终在想着一件事,却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件事,而且还要表现出很有兴趣,来迎合这件事的发展。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尽快解决眼前的事。当他说出了这句话后,我就在琢磨我的措辞,要怎么才能让这次不逢时的会面结束。菲利普外表冷静,其实是个狂热分子,喋喋不休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很好,谢谢你的关心。但你知道我的病情,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脸色不好,不过我感觉很好。今天会有什么事呢?现在的情况和场合很特殊,事情很重要吗?”我说。
我的目的是让他在接下来就讲明来意,好让我接下来送走他后一件一件完成我需要完成的事,因为我时间有限,必须节省时间。但我又不能向他说弗吉尼亚的事,更不能对外公布这个消息。根据我对菲利普的了解,如果不从我这里施压,这场谈话会持续到凌晨,直到我俩都趴在餐桌上睡着为止。
显然,菲利普还没准备好,他原本准备的满页的典故和历史事件都派不上用场了,现在他需要改变策略。他的下巴略微上扬,我对面的灯光里有个似笑非笑的幻影。那就是他了,好像很佩服我的勇气。
但他不会马上就讲,这我知道。果然,他站了起来,他身材很高大,现在我几乎是在仰望他了。他把双手张开,看着我的脸,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就像外面那些不正经的年轻人一样。现在我只能仰望他。
他转身打开了背后的酒柜,整套动作没有一点停滞,就像受过专业训练一样。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流畅不流畅的问题,关键是这是在我家里,他怎么知道藏在他背后的酒柜?而且酒柜里还有酒的?看来他是个聪明人。酒柜里空荡荡的,只有两瓶从中国带来的白酒,还有一瓶威士忌,以及若干玻璃杯和小酒杯,但他并没有为此抱怨什么。我对酒的好坏一窍不通,因此威士忌既不是顺风,也不是芝华士,而是趁超市打折时顺手买来的。后来喝的时候,不经意间我瞥到了印在酒瓶上的品牌,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拿的是一瓶波本威士忌。按照西方人的喜好,他拿了一瓶威士忌出来,这是一瓶开过的酒,还剩下一半,但具体是否剩了现在这么多我也不清楚。酒瓶里已经解决的部分是我和弗吉尼亚喝掉的,这是我们几天的成果,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某个固定的时刻就是我们享用威士忌的时间。那时候弗吉尼亚恰好对中国的饮酒文化感兴趣,我为了让她明白这种文化里面的诗性和豪放,就每天晚上和她小酌。她受不了白酒的烈度,那种感觉让她作呕。所以我们权衡再三,就选择了威士忌来小酌,我们把这种洋酒倒在小酒杯里,谈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坐在公寓里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每家每户闪烁的橘色灯光逐渐暗淡下去,然后慢慢把威士忌喝下,所以酒消耗得非常慢。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我忘了我们到底喝了多少。只是现在看到这样一件能把我拖入回忆的物件,我心里面的焦急和恐惧又泛滥起来。
把半瓶威士忌放在桌上后,他又从酒柜里拿出了两个玻璃杯,在我们面前各放了一个。不出一分钟,他就倒好了酒,每个瓶子里只倒了三分之一,而酒瓶里还剩了一点。他重新把那瓶威士忌放回了酒柜,这个看似多余的动作其实很细心,几乎每个女人都能因为这样一个小细节而对他动心。“宴会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是品酒会吧。”他又张开双手,晃着身子说。这不是讽刺挖苦,对菲利普来说,这只是示好的手段而已,他被长年累月的社交活动浸染了。他坐了下来,努力想像个朋友一样和我谈心。
他和我坐在一起谈了些什么,我怎么也没料到我会以失声痛哭来结束这次交谈,给这次难得的见面平添了几分悲伤的色彩。要是比起世界上那些混乱的地区的人民,他们周围充满着瘟疫、战乱、恐怖袭击、政治恐怖,我以往的经历还算得上是一帆风顺,那么我现在的状况就像是所有悲哀和混乱全都落在了我头上。人只有死去才会获得平静,而世界只有遇到了世界末日才不会发生那些以前都发生过的悲惨事情,世界每天都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好在在这场谈话里,菲利普的身份更倾向于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讲述者或者是一名安慰者,这些身份始终是游离在悲伤的当事人之外的。这次菲利普不像往常一样,只会说一些没用的信息了。这次交谈引起了我的注意,尽管他说得斩钉截铁,我也相信了他,但我认为我还是要自己动手,自己动脑筋。但我说了,我已经相信了他,这意味着真相已经大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只不过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调查,就算没这次交谈,我也会这么做,就当是找到一些证物。不,或许叫物件更合适一些,每个人都有一些恋物的倾向,特别是当物件跟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牵扯上关系的时候。就像那个威士忌酒瓶一样,不管那瓶子里还剩多少酒,但每当我凝视它或抚摸它,总是能把我拖入回忆。甜蜜而深刻得能让我深陷于幻想,不借助外界力量,我便无法自拔。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奇妙的地方就在这方面。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看了看客厅里的挂钟。但菲利普似乎拿出了所有的诚心,他比我抢先一步,在我俩互相沉默的时候瞟了一眼手表,他说:“快十一点了,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吧。我们聊的很愉快,但聊的东西却不怎么令人开心。这是事情本身决定的,不能怨任何人。你早点去休息,失眠了就想想生活中的希望,因为我也会因为很多事情失眠,工作上的,感情上的。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时你能比现在看上去更好。”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客气地和我道了别。我原来对菲利普抱有一种厌恶感,或许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就像他对我说的一样,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我接受了。这不能怪我毫无原则,也不能怨我不择手段,这只能怪事情本身——它把我打入一个深渊,让我也许永远也爬不出去。我需要吸收一点阳光,所以要有一个人为我抛下绳索,固定好绳子,让我往上爬一段距离。我在深渊底下是看不到上面的人的,所以我当然也就不知道抛绳索的人是菲利普,我也不会料到是他。
我们约定好第二天下午三点在医院某个偏僻的办公室碰面,兑现我们今天交谈后达成的共识。这些都是经过我慎重考虑了的,我确定它们都对我有所帮助,才答应了菲利普。而据他所说,这也是“学校的意思”,所以我应该说成是我答应了他们。
我没到门口去送他,听到菲利普有力的关门声后,我开始着手接下来的事了。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这就给了我空闲时间,从现在到明天下午三点之前,还是有足够的时间供我支配。我该做些什么事呢?我不顾肉体上的疼痛开始思考,这对一个文学教授来说是件难事,但没办法,生活中充满了逼迫,就连我去做个文学教授,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活在逼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