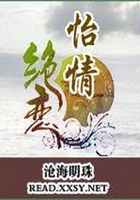枪生说,是我讨来的红苕。
道人说,我饿了。能给我吃吗?
枪生解开包袱,拿出红苕递给道人,说,师傅,你吃。
道人说,我问你,我要是不收你,你会给我吃吗?
枪生说,师傅,你吃。我下山后再去讨。
道人流着泪望着枪生。
枪生说,师傅,你哭什么?
道人流着眼泪说,孩子,我哭善根未断。
枪生说,师傅,我吃一个,你吃一个。你不吃,我不吃。
道人说,我吃,我吃。我吃,你也吃。
道人流着眼泪吃红苕,问,孩子,你姓什么?
枪生说,我姓罗。
道人说,孩子,你不姓罗。
枪生问,你说我姓什么?
道人说,你姓王。
枪生问,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姓王?
道人说,师傅算出来的。
枪生问,师傅,你会算。你算算我娘姓什么?
道人闭上了眼睛,泪水流到脸上。道人说,孩子,你娘她姓傅。
枪生高兴了,说,是的。我娘姓傅。师傅,你算得真准。你太高明了。你真是神仙。师傅,你姓什么?
道人说,出家人不论俗姓。
枪生问,师傅,你没娘没父亲吗?你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变出来的吗?
道人说,对,孩子,师傅,无父无母,是神仙。
枪生说,师傅,我跟你,也做神仙。
道人叹了一口气,问,孩子,山下怎么没有枪炮声?
枪生说,红军走了。白军也走了,白军追红军去了。
云根问,啊,都走了。他们走了,山下的人在做什么?
枪生说,在烧火做饭吃。
道人问,是吗?
枪生说,是的。一烧火,烟就升起来了,我就闻到了饭香。
道人流着眼泪笑了,说,孩子,我们不当神仙了。还当什么神仙?你随我下山去,我们还俗,种田种地,生儿育女去!
枪生问,你收我?
道人说,我给你做父,你给我做儿,我俩合成一家过日子好吗?
枪生说,好!
道人进后屋,将被子捆了出来,叫枪生驮在背上,拿过枪生驮红苕的包袱,牵着枪生的手,说,孩子,你替我驮被子,我替你驮红苕,你随我下山去过人的日子!
枪生高高兴兴随云根道人下了山。
云根带着枪生下山后,在山下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附近的人们不究云根的根底,也不究枪生的根底,都传凤凰观的道人还俗了,还带了一个道童做儿。云根带着枪生开山种地,搭砖造屋,日子里有了烟火,有了生机。还俗的云根找了山里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做老婆。结婚后,云根的老婆,给他十年生了两儿两女。
日子里枪生慢慢长大了,长成了十八岁的小伙子。云根张罗给枪生说了一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枪生的儿与云根的小女儿同年同月生的。乡亲们都来祝贺,当做盛事传。
枪生的儿子满月后的那天夜里,云根同枪生将前因后果说破了。
真相大白。枪生泣不成声,叫了云根一声,舅。云根叫了枪生一声,外甥儿。双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云根流着眼泪,笑了,仰天一叹,此生别无它求,一声足矣!世事风云变化,变也好,化也罢,万变不离其宗。既然各知根底了,我们就各落各的根吧!
于是云根带着家人,搬回了夫子河边的傅兴垸。
傅兴垸人认出了他,接纳了云根和他的一家。
于是枪生带着家人,搬回了石槽冲。
石槽冲人唏嘘不已,接纳了枪生和他的一家。
枪生带着一家搬回石槽冲的那一年,老婆又一肚子生了个龙凤胎。枪生已是五口之家的一家之主了。枪生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中一件大事。他历尽千辛万苦,把他所有亲人的骨殖都找到了,背回来,背到王姓的祖坟山上。枪生将亲人们挨着祖父和祖母,立碑安葬了。枪生在父亲的墓碑上刻着父亲的绝命诗:马列思潮沁脑髓,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正,甘心直上断头台。枪生在母亲的碑上母亲的绝命诗:白云性高远,野渡生荒情。秋风无着处,河水两岸清。
枪生跪在祖母的坟前,对祖母说,祖母啊,孙子把亲人都找回来了,找回来挨着您了。您的一家又团圆了。
九月重阳,枪生带着他的老婆和孩子到坟山上举行隆重的祭祀。枪生带着老婆和孩子,依个给他的亲人磕头,叫他们安息。枪生给他的亲人,每座坟前烧很多很多的纸钱,将纸钱堆起来烧,让他们在阴间有钱用。
山风吹来,纸钱的灰,像漫天的蝴蝶儿,飞。
七十一
王幼刚是十六年后,一九四八年春天刘邓大军南下杀回大别山的。
十六年历尽艰辛,十六年枪林弹雨,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晨光。
百万雄师过大江。身为师长的王幼刚带着部队在阳逻作渡江作战的准备。阳罗是倒水河、举水河的入江口。面对浩浩长江,王幼刚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忆起了群山里的石槽冲,那里是他的家乡。十六年音讯全无,估计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他嫂子,他的两个妹妹,他的一个侄儿,都死在天台山那场大火里了。他不知道那重重的大山里还有没有他的亲人?他记得当年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时,他的一个侄儿,被一个姓罗的领走了。他记得他的侄儿叫枪生。十六年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他不知道他的那个侄儿,枪生还在不在人世间?
思亲难忍。于是他就叫一个侦察员化装成买布的,进山到大山里去打听。他告诉那个侦察员,他的家乡地名叫石槽冲。他不知枪生是死是活。他拿出随身带的一张当年的他大哥设计的油布票,叫那个侦察员带着,为了怀念大哥,他将那张油布票一直带在身上,珍藏了十六年。他对那个侦察员说,若是找到王枪生,就把这张油布票拿出来交给他。叫他带着这张油布票,到阳逻找我。这张油布票就是见面的凭证。
那个侦察员带着纸条进山去,费尽了周折,问到了大山里的石槽冲,找到了枪生。
那个侦察员对枪生说,你是不是姓王?枪生说,我是姓王。侦察员问,你是不是叫枪生?枪生说,我是叫枪生。侦察员说,你还活着?枪生说,我还活着。侦察员拿出那张油布票说,有人找你?枪生问,谁找我?侦察员说,给油布票的人。枪生拿着纸条一看,泪就出来了。枪生见了那张油布票就像见到了父亲。枪生问,是谁找我?侦察员说,不要多问,去了就知道。大战在即,我先走了。你带上这张油布票,按我说的地方去。
侦察员走了。枪生不知是福是祸,拿着那张油布票到夫子河傅兴垸找云根舅拿主意。云根看了那张油布票,对枪生说,这是你至亲的人啊!不是你至亲的人,拿得出当年的油布票?叫得出你的名字?你去吧!
枪生就带着那张油布票,顺着光黄古道走。一路的兵,一路的哨,检查过往行人。哨兵拦着,枪生就拿出那张油布票给哨兵看。哨兵见了那张当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的油布票,知道是自己人,就放行。
枪生拿着那张油布票来到了长江边上的阳逻。王幼刚的师部就在那里。枪生找到了师部。王幼刚正在开会布置渡江战役。那个先回的侦察员等着枪生了。见枪生来了,那个侦察员进了师部,在王幼刚耳边低声说,一号,外面有人找。王幼刚问,谁?参谋说,你要找的人。王幼刚听后通身热血沸腾起来,对参谋说,叫他等一会儿,等我开完会。
王幼刚开完会,就出来了。春天的阳光格外的明媚,格外的亮。太阳下,王幼刚看见太阳底下站着一个后生。那后就像他的大哥,就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王幼刚问,你是枪生吗?
枪生望着王幼刚楞住了,问,你是谁?
王幼刚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三叔啊!枪生,你还活着?
枪生咧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枪生一下子扑进三叔的怀里,说,三叔,我还活着。
王幼刚拍着枪生的背,泪流满面,说,真没想到我们王家没死绝!还留着一个“人种”啊!
枪生拿出那张油布票,说,三叔,这张钱我还给你。
王幼刚说,侄儿,这就是你父亲啊!三叔给你,你留着。传下去,传给子孙后代!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一九五四年,全军授衔,王幼刚被授为共和国的将军。大别山里出的将军多,二百多个。王幼刚是其中的一个。王幼刚死后,骨灰按照生前遗嘱送回家乡石槽冲安葬。将军没有葬在祖坟山上。将军的墓建在大路边上,只要走进石槽冲就能远远地看见。
几十年过去了。鄂豫皖革命博物馆重修了,广阔,辉煌,灿若星河,聚集着革命英烈。广场高耸的纪念碑上,用大理石塑着手擎铜锣的像。那面铜锣就像一轮太阳擎在天上,闪闪发光。
二十年就是一代人。石槽冲王家的子孙成群了。夫子河边的傅家子孙也成群了。傅姓子孙据说在台湾当大官的很有几个,因为“江记”一支的有几个,服役于国军,解放前夕逃到了那边。两岸关系缓和后,经常有人回来省亲。
改革开放后,傅兴垸成了鄂豫皖三省交界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傅姓子孙有许多做生意做到了汉正街,在当地富得很有名声。傅兴垸村和石槽冲村的村干部,都是傅姓和王姓的子孙当。
两姓的祖人,盘根错节。傅姓和王姓达成默契,清明时节,不在同一天上山祭祖。
有人来采访,问起过去的事。双方都不说。
他们说,书上有,书上都写着哩。
于是就请,请你到垸里去喝酒。
2008年12月6日1:30完稿11日修改,27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