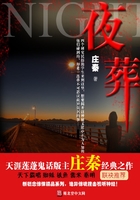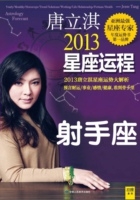傅兴垸垸城的门虽有兵丁守,但人心如浮头的鱼,惶惶不安。细雨中,守城门的兵丁见傅家老姑娘回来了,放下吊桥,洞开城门让她进。没人说一句话,沿路只见兵丁们默默的。傅大脚沿着垸巷青石铺的路朝桂花楼走,一路将手中的拐棍,拄得咚咚响。垸人见她,都避过眼睛不朝她望。傅大脚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垸中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傅大脚进大门,踏上桂花楼,拐棍拄得木板楼梯打颤。
傅大脚拄着拐棍喊,傅立松,你这个牲畜在哪里?你给我出来!傅立松的夫人流着眼泪出来了,不打招呼,不说话,领着傅大脚朝楼上走。傅大脚走到二楼上。傅大脚拄着拐棍问,畜牲在哪里?夫人将傅大脚领到一间紧闭的房间前。门前和窗前有人守着。夫人对傅大脚说,他在屋里。只听见紧闭的屋里传出狼样的叫。傅大脚透过窗户看见傅立松赤身露体用绳子绑着手脚,狂跳不止。
傅大脚用拐棍拄着地板骂,你这个畜牲!
屋内狂笑不已。
傅大脚骂,你这个天杀的!
屋内狂叫,天杀,地杀。
傅大脚骂,你想杀尽吗?
屋内狂叫,杀!杀!他杀,我杀!我杀,他杀!
傅大脚昏倒地上。夫人叫人灌水,傅大脚一口气转来了,泪流满面,说,天啦!这是人吗?这哪里还是人?
谁也拦不住。傅大脚拄着拐棍沿着垸街的石板路回去了,回到了大山里的石槽冲。
一路山路弯弯,细雨无声。
那雨如虫如蚁,无边无际,湿天湿地,湿透了傅大脚一身的瘦骨。
六十五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大别山里的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在红安河口黄柴畈召开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部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越平汉铁路,进行战略转移。
转移之时,红四方面军为了筹集资金,决定分头对红安麻城两县的乡绅庄园进行洗礼。时任团长的王幼刚奉命率领红军一个团进攻夫子河边的傅兴垸,将傅兴垸“江记”“裕记”“元记”三支的财产全部没收。
红四方面军决定准备放弃经营十年的鄂豫皖苏区,分成若干路,犹如破堤的洪水瞄准各自的目标泄出。王幼刚带着一个团出山连夜向夫子河边扑去,三更时分,像铁桶一样包围了傅兴垸。夜破了,火光熊熊,枪声骤起。一个团的兵力围着护城河进攻。傅兴垸虽有护垸河垸城防范和红枪会兵丁把守,但无济于事。时值深秋,沿垸城的护城河水浅得可怜,现出淤泥,红军战士用准备好的稻草,一人一捆,沿护垸河铺成若干条路,踏着稻草路,向垸城发起进攻,势如破竹。那时候傅立松疯了,绑在屋子里关着,红枪会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根本抵挡不住王幼刚一个团的攻击。只用一个时辰,傅兴垸的垸城就破了,王幼刚的一个团分数路攻进了傅兴垸。傅兴垸七条主街和十八条垸巷里被火把照亮了,“裕记”和“江记”乖乖向红军交出财产,交给红军登记,装挑。登记装挑的主要是黄金和银元。“裕记”和“江记”把纸币也拿出来了。但纸币红军不要,因为当时国民党发行的纸币连连贬值,几乎是费纸,要它干什么。纸币散落在地上,像树叶,任风吹,任脚踩。王幼刚带着没收人员将“裕记”“江记”没收的金银登记之后,最后围住了垸中的“元记”的桂花楼。
“元记”的桂花楼是垸城中的城中城,有高大的围墙围着,铁门紧闭。王幼刚带着红军战士举着火把攻到铁门前。王幼刚指挥红军战士抬起青石条撞铁门。八个红军战士抬起青石条向铁门猛撞时,由于用力过猛,一齐倒在地上。这才发现铁门根本没闩。高大的桂花树黑在夜里,庭院深深的桂花楼无灯无火,静得像一窟坟。
王幼刚的一个团向傅兴垸发起攻击时,火光熊熊,枪声大作,绑在桂花楼二楼屋子里的傅立松衣裳被撕得一条一条的露着肉,还在疯狂地咆啸,用头撞着墙,一个劲地喊,杀,杀,杀!妄图挣脱绳索,冲出屋来。但绑他的麻绳相当粗,无论他怎样地疯狂,无济于事。自从他在干河河滩活埋王幼勇被那个团长绑着送回之后,家人就没有松开他,他认不得人了,见人就吼就咬。只有夫人给他端吃端喝,他才安静。夫人端饭端水喂给他吃喂给他喝。他一天到晚亢奋着,瞪着眼睛不睡。他站着屙站着拉,夫人含着眼泪给他洗给他换衣裳,折磨得夫人心力交瘁。当红军攻进垸,枪声停止,没收“裕记”和“江记”的财产之后,傅立松突然清醒了。傅立松不狂不吼了,望着夫人。傅立松对流泪的夫人说,把绳子解开!我要换身衣裳。夫人吃了一惊,问,你说什么?傅立松说,把绳子解开,我要换身衣裳。夫人问,老爷,你醒了?傅立松说,我醒了。夫人上前给他解了绳子,拿来平常换洗的衣裳。他不要。他说,给我拿出门时的衣裳来。夫人拿来他出门穿的呢料中山装,问,是这身衣裳吗?他点头说,是的。夫人动手给他换。他不要夫人动手,他自己换。穿上呢料的中山装,换上配套的呢料裤子,他对着墙上的镜子照,将扣子从下到上,一直结到脖子上,结得整整齐齐。然后叫夫人将他的黑色毡帽拿来,他对着镜子戴正。墙上的镜子里他衣冠楚楚了。他对夫人说,我要洗脸。夫人拿来毛巾和水。他绞着毛巾,仔细地洗他脸,将他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叫夫人掇张太师椅到二楼的楼梯口。夫人掇来一张太师椅放在二楼的楼梯口。他出门,端端正正坐在二楼楼梯口的那张太师椅子上。坐在太师椅上的他对夫人说,给我光明。夫人进屋将点着的烛连同烛台掇出来。他对夫人说,将光明放在我的眼睛前。夫人将烛台放在木制的栏杆上,烛光亮亮的,照着傅立松的脸。傅立松望着发光的烛,流下了眼泪。
傅立松对夫人说,站在我的身边。夫人站到他的身边了。傅立松说,将它吹熄吧。夫人将烛吹熄了。桂花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王幼刚带着红军战士举着火把进到桂花楼的院子里。桂花楼在百年高大的桂花树浓荫下更加的黑,那黑无隙无缝,火把的光亮闪闪的,撕得黑丝丝作响。王幼刚冲着黑暗的桂花喊,有人没有?喊声被黑吃了,留下丝丝余声。王幼刚朝天放了一枪,大声喊,人都死了吗?栖在桂花楼上的那只猫头鹰,这时候才惊飞了,飞向黑暗的天空,翅膀扇起阵阵黑风。
这时候黑暗里就有了叫声。叫声传出来,谁说人都死了?还在!王幼刚冲着黑暗问,在哪里?那声音笑,你看不见我吗?我看见你了。王幼刚喊,听着!你被包围了。少玩花招!黑暗里传出笑,我不玩花招了。我的花招玩尽了。三外甥,我在这里,我将光明点亮,照你上来。傅立松叫夫人点亮蜡烛。蜡烛点亮了。光从天井上漏下来,现出二楼楼梯口太师椅上坐着的傅立松,还有他身边的夫人。
王幼刚带着红军战士举着火把上楼,坐在椅子上的傅立松没有站起来,两只手放在椅翅上,望着上楼的王幼刚笑。
王幼刚用手枪指着傅立松的脑门。
傅立松说,我知道是你来了。
王幼刚说,知道就好!
傅立松说,来结总帐吗?
王幼刚说,是的。
傅立松问,结完总帐就要走吗?
王幼刚说,你一生太聪明了。
傅立松叹了一口气说,你说错了。不是聪明,是明白。是该到结帐的时候了。十年啦,恩恩怨怨,怨有头,债有主,总该有个了结。不了结心就放不下。这样你是对的。你不能让我疯死。是要命还是要银子?
王幼刚说,命也要,银子也要。
傅立松说,你说得对。光要命是行不通的。人肉虽然是肉但不能吃,人血虽然是水做的,但不能喝。要银子是对的。银子是天下财富,不然漫漫征程,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王幼刚说,少费话!
傅立松说,一样一样的结吧。先把命拿去。然后拿银子。
王幼刚问,你怕死吗?
傅立松说,我什么都不怕,还怕什么死?等着你来。
王幼刚说,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不要你的命?
傅立松说,我等够了。还不快动手?傅立松朝王幼刚张开了嘴巴,露出牙齿,喉咙深处传哑声,你看看这里边软的还在,硬的还在。
傅立松扑上前一口咬住了王幼刚手中的枪管。
王幼刚愤怒了,吼,你松口。
傅立松咬着枪管,像狮子一样猛摇头。
枪响了,子弹从傅立松的头后飞出来,傅立松扑倒在地。
夫人惨叫一声,撞墙而死。
这时候天亮了。王幼刚不敢停留,领着他的一个团带着没收的金银,整队向红安天台山方向集结。天台山山高林密是红四方面军西越平汉铁路作战略转移的集结地。
傅立松的尸体仰面朝天就放在傅兴垸垸城的城楼上,肚子上挖了一个洞,洞里放了一根棉纱搓成的捻子,点燃了,吸着油滋滋响。
这是鄂东对付恶人的一种刑法,叫做点天灯。
六十六
红四方面军各部在天台山脚会合了,准备离开开辟十年的鄂豫皖根据地,西越平汉铁路,实出重围。浩荡的队伍里,王幼刚与两个妹妹王幼霭、王幼馨和傅素云母子见面了。为了不影响战略转移,就在这时候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命令各部轻装简从,将重武器就地销毁,将重伤员和儿童尽快就地安置。
那时候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十年,由于红白对立,水火不容,队伍里许多都是家人班子,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参加了红军。能拿枪打仗的编入战斗队伍,不能拿枪打仗的安排在医院和军工厂和被服厂。王幼勇在干河牺牲后,傅素云离开了苏区银行,组织安排她和两个孩子枪生、枪响到苏区被服厂工作。傅素云与妇女们在苏区被服厂给红军缝军服,枪响和枪生年纪小,给军服订扣子。傅素云接到指挥部孩子必须留下的命令时,枪响病得不轻,正在发烧,离不开娘的照应。傅素云向组织上反映,她不能离开队伍,她的孩子也不能离开队伍。组织上指示枪响病重不能离开娘,那就带着,但是枪生在转移之前,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就地安置。
八岁的枪生就是在转移之前离开娘的。
那是惨彻人间生离死别的场面。
大别山的冬天随着来了。寒霜凝地,雁阵在天。北风一阵阵吹来,寒得人打颤。南迁的雁阵,在风中一声声地叫,叫得人泪流满面。红四方面军负责安置地有关领导,将山里老百姓召来,召集在天台山脚一个小村山坡上的稻场上。山民们袖着手站在稻场的四周,红军的孩子们由父亲和娘领着站在稻场中间。敌军四面围来情况紧急,红四方面军的有关的领导人给山民作简短的动员,动员山民们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保存革命后代,领养红军的孩子,宣布每个孩子给五块大洋的领养费。
北风中四周的枪声像炒豆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