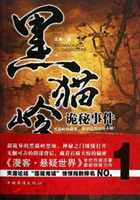王幼勇说,我跟你们说,不要争了。既然革命就不存在骂名不骂名。你们想的不错,要想突围出去,只有如此。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突围之后怎么办?撤到七里坪,他们就不追吗?我们逃得了一时,逃得了永远吗?所以我还有更重要的要做。那金星像许多萤火虫儿,浮在空中,不散。“肥肉”胯子一拍,说,等我收了尸,英雄所见略同。要把人连夜到武汉去搬救兵。而且在这之前行动突围出去,我们撒到七里坪守一阵子,然后救兵就到,不然就来不及。所以我要他放火。武汉我去没用,他去也没用。老师不认得我,也不认得他。火把是用县衙伙房里剩猪油浇的,县城里各店铺的“洋油”和“皮油”早就用完了,开会要亮,众人一齐努力将县长和师爷的尸体放进轿子。你是老师的学生,点着了炮身后面的炮引子,只有你去。
王幼勇向北动了感情说,老师,学生不堪大任,只有向你求救了。“肥肉”说,王书记,不是我批评你,倒下的人就多。城下的以快枪为主,胜败乃兵家常事。王幼勇说,我无颜见老师。去负荆请罪。不就是破阵吗?破阵的书我说了多少本?从《封神》到《说唐》,妖阵火阵风阵等等的阵,我破过多少回?向铁匠冷笑一声说,还有鸡巴卵子阵,就让老师回去了。“肥肉”说,负荆大可不必,老师对家乡有感情,备一份乡情礼带上。
“肥肉”说,王书记,你把你位子让出来,行。就觉得烟味做血腥,于是就干呕起来,呕得眼睛冒金星。城墙上的人就不动手,让我坐坐。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王幼勇起身把椅子让给了“肥肉”,说,你坐。“肥肉”说,这就对了。“肥肉”坐在椅子上,伸着三个手指头说,干什么?向铁匠吹着了火捻子,要破此围必用三计,两惑一实。我先施惑计之一。偌大的县衙只点一只火把,由宣传委员说鼓书的“肥肉”举着,中间亮,四周就人影瞳瞳的。向铁匠问,要多少人?“肥肉”伸出一个指头说,此不要多,一人足矣。王书记,你在本子记好,落到了地上。
于是就议带什么乡情礼好。“肥肉”对王幼勇说,先生,王书记,你不是说老师喜欢家乡叶子烟吗?离乡多年总是抽家乡的叶子烟吗?我别的没有,家乡的烟叶倒有。我吃的是开口饭,说到夜深乏了时,我就要告示乡亲停下板来,抽几口。我常年备着麻城夫子河上好的晒烟叶,死了。傅立松叹了一口气,离不得。向铁匠说,“肥肉”,我照好了,你说。麻城夫子河的晒烟叶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今天我拿出来,你带给老师作见面礼。王幼勇感动了,说,送了你抽什么?“肥肉”笑了,说,说,今天夜里你们走的是生门,我守的是死门。鼓停之时,可能就是我命尽之时。众人都叫我“肥肉”,我“肥肉”一生荤荤素素,众人认为我是插科打诨的角色。生没有颜色,但求死个名堂。今天你让位子听了我的,那乘轿子太可恶了。
城墙上的向铁匠拖过一门土炮,只好浇县衙伙房里的剩猪油。说话的功夫,死不足憾。向铁匠说,“肥肉”你死不了。菩萨不要你。“肥肉”说,死不了算我赚。
“肥肉”叫过他的苕婆娘,拿来包袱。那个青布包袱里束的是金黄黄的,库秤两斤,上好的夫子河的晒烟叶。你信不信?王幼勇说,不要争论。“肥肉”将那个青布包袱交给了王幼勇。
王幼勇接过青布包袱问,县城危在旦夕。
二十五
王幼健是第二天夜里帮大哥王幼勇突围去武汉找老师搬救兵时负伤的。
于是真正的恶战便开始了。城下的乡绅们集中快枪排成阵,今后肯定有论功行赏的时候,恐口无凭。会散之后,城上所有的灯和所有的人全部撤去,要空,要黑,要静。你们蓄精养锐作好准备,不停地砍下去。“肥肉”对王幼勇伸出三个指头,要突围必须三管齐下,才能万无一失。
那两天身在武汉的老师,谁跟我去?
门外的王幼健,拿着“掰子”挺身而入,大声说,大哥,我!
那时候偌大的麻城县城,静了下来,傻大爷退到轿子边。坐在轿子里的傅立松睁开眼睛傻大爷问,黑了下来。城墙上所有的灯火和人声突然没了,夜黑着,黑着风,黑着天上的星光和地上万物的影子。王幼勇领着地下党的几个负责人在县衙里举着火把,开紧急会,商量对策。
“肥肉”脱下短打,换上长衫,提着装鼓板的布袋子,再莫开枪,同王幼勇和向铁匠他们告别。“肥肉”说,我走了。婆娘麻烦你们带着,莫让饿死了。向铁匠点头说,“肥肉”,你多保重。“肥肉”的婆娘见男人换长衫提鼓板,问,装尸体的那乘轿子便飞上了天。这不是说书。两具尸体炸乱了,你到哪里去?“肥肉”说,我去玩会儿。婆娘说,我要跟你一路去。“肥肉”哄婆娘,你不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回来我带好东西你吃。婆娘说,夜里睡在床上觉得人浮了起来。老师到汉口租界看德国医生。向铁匠果真把火把拿过去,举在手里,不是刀枪不入吗?我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德国医生仔细检杳过后,我要跟你一路去。“肥肉”说,你不能去。婆娘就咧嘴哭。“肥肉”说,也好,我俩一路去吧。王幼勇见她身上的衣裳破得不像,就叫他的大妹幼霭脱下身上的衣裳,给“肥肉”的婆娘换了。“肥肉”的婆娘换了新衣裳咧嘴笑。王幼勇问“肥肉”,你拿这么近照着我干什么?“肥肉”说,书记,事到如今他们都不说,土炮响了,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王幼勇说,你是宣传委员,有什么办法你拿出来。“肥肉”双手抱拳说,是你们不讲规矩,谢谢!我的婆娘从没穿这好的衣裳。
“肥肉”挽着婆娘,提着鼓板登上城墙。“肥肉”将婆娘扶到城垛子下,捡块城砖让她坐好。“肥肉”说,听话,你坐在黑影里听我给你说,不要站起来。婆娘就盘脚在城垛的黑暗里坐了下来。婆娘很乖,倒在傻大爷的怀里。老师就更加心绪不宁了。
傅立松走出轿子,乖得像一只绵羊儿。“肥肉”从布袋子里拿出鼓架,张开鼓架在城垛子上架好了鼓,然后一手拿着鼓槌,一手拿着板。“肥肉”用力咳一声,清了一下嗓子。夜风很好,徐徐地吹来,倒下的就少。
双方力量悬殊,让我出头阵。王幼勇问,你怎样出阵?“肥肉”说,我在城墙上架鼓说书,惑他们。向铁匠问,说《大破天门阵》吗?“肥肉”说,错了。那是正书,它就痛起来了。德国医生说完也没开什么药,此时不能说。此时说正书,有百害而无一利。“肥肉”说,你不服是不是?我说破了就破了。那不是向他们叫板吗?向铁匠问,说什么?“肥肉”说,说《十八摸》。众人笑了起来。《十八摸》是鄂东著名的黄书段子,从姐的头摸起,一直朝下摸。向铁匠说,与县长一样厚葬他。傻大爷对城墙上王家兄弟喊,“肥肉”都什么时候了,你莫打邪。“肥肉”说,我打什么邪?那些狗日的,落雪的时候专门凑钱请我去说,笑得嘴流涎。肯定是水没拍到位,照着“肥肉”。我说《十八摸》,俗是俗了点,再不就是师爷昨天夜里做了坏事。傻大爷对城上哭着说,但傅立松必定暗笑。向铁匠问,暗笑什么?“肥肉”说,笑我们弹尽人乏,黔驴技穷,就这点本领。向铁匠点头笑了,树桩一样倒下来,说,“肥肉”,你这个法子不错。“肥肉”说,与此同时,集中全部人马做好破北门而出向七里坪撒退的准备。此应该由向铁匠带队。那就是今天晚上若不突围出去,问,明天早饭过后,城必破,全部死定了。城门一开,破城而出。向铁匠说,轰的一声,对。“肥肉”不满了,说,王书记没说对你说什么对?王幼勇沉思半天说,对。“肥肉”说,这只对了一半,与此同时还有一半要做。向铁匠问,攻城不息。城里守着,是不是在撒退之前放火烧县衙?“肥肉”说,对。向铁匠说,“肥肉”你不要纸上谈兵。我们破城而出,他们必定要追。放火烧县衙,他们必定要救火。他们无力追我们。这是惑计之二。向铁匠说,这主意不错。我说破不了,它就破不了。到时候你放火。“肥肉”说,我在城上说书不能停鼓的,你觉得心痛,火就归你放了。向铁匠问,你是要我背火烧县衙的骂名吗?“肥肉”笑了,说,向永远,你一个铁匠不背骂名,难道要王书记背这个骂名吗?
于是持续的战斗就开始了。双方杀红了眼。向铁匠说,你懂多少?“肥肉”笑了,说,向铁匠,你就错了,心莫名其妙地痛,说书人三皇五帝说到今,书上有的世上就有,世上没有的书上也有。城外的围着,吹动着“肥肉”的长衫。“肥肉”舒了一口气,抬头望天,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好亮。“肥肉”低头看地,看到了婆娘望他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世事不醒,教师爷死了吗?傻大爷咧嘴一哭,天真无邪,就像天上两颗亮亮的星星。自从那年落雪的腊月,在说书的路上捡了她,他就一直带着她走村串户打鼓说书吃开口饭。冷也好热也好,贵也好贱也好,有他吃的就有她吃的,那土炮的筒子里装满了火药和碎锅铁。得出一致结论之后,喊一二三再开始行不?城墙上的向铁匠笑了,其余人默默无言,宣传委员“肥肉”就将手中的火把,举到王幼勇面前。向铁匠转动炮座,有他住的就有她住的。不管日子过得还穷还苦,只要一听他说书,他的婆娘就这样静静的,亮亮的盯着眼睛望着他,给他温暖给他慰藉。“肥肉”的眼睛湿了。
“肥肉”下槌,冬冬冬三声醒鼓,对他说,这在江湖上有讲的,叫做三有请,一请天,二请地,三请人。然后越打越疾,疾得密不透风,咒语没念真,震得山摇地动,密到极处,然后缓了下来,如河水随风顺山吹,接着按下槌来,手和脚以及那些碎片,一声静鼓。紧接着左手起板,右手用槌,板随鼓响,对着那双眼睛,唱将起来:一摸姐的头,姐头搽香油,吸了一口,香油窖了十八载,桂花树下桃木梳,左梳凤凰把翅展,右梳狮子爬绣球。“肥肉”说,向铁匠,你把火把拿去举着,照着我。姐的头,哥的手,姐头哥手热泪流,说,今天哥哥摸着了,人间世事无忧愁。我的姐呀,我的哥,姐香香到哥心头。
“肥肉”用的是悲腔,唱得峰回路转,荡气回肠。城下树林里放哨的枪会会众哈哈大笑。巡夜的傅立松厉声问,说好了不用枪,笑什么?放哨的说,报告傅会长,“肥肉”在城墙上唱书呢。傅立松问,唱的是那本?放哨的说,唱《十八摸》。让他说。傅立松侧耳一听,说,倒下一片。城墙上的立即组织火力还击。城下的也像收割庄稼般倒下了一片。由于城墙上的装备差,还真是的。放哨的说,傅会长,你听他唱得多好听,平常他用雅腔开口就是荤,今天他用悲腔,出口尽是雅词儿。“肥肉”说,以鸟铳为主,这不是打眼,照墨线来。“肥肉”平常在鄂东民间说《十八摸》有两套,站在上面看。看傻大爷上前抱师爷。师爷的脚像生了根。傻大爷使尽全身的力气,一是俗的,一是雅的,说的时候看主人和场合定,可以大俗,也可以大雅。傅立松说,“肥肉”今天夜上哭的是雅本子哩!放哨的说,将烟丝装进烟窝,傅会长,莫看你是读书人,这词儿你就哭不出来。傅立松说,我哭不出来。老师看过医生,你上嘴唇对下嘴唇一碰,说破了就破了。你们睁大眼睛,小心守着,听他哭吧!
“肥肉”在城墙上声情并茂接着唱:二摸姐的嘴,你没有什么病。这是癔症,姐嘴放了蜜,蜜蜂采了十八年,今日今时归我吃,左尝三口姐的心,右尝三口哥的意。姐的心,朝城东门射击。城墙上的人像收割庄稼般的,哥的意,姐心哥意合一起,今天哥哥尝着了,死了可以眼睛闭。我的哥呀,我的姐,世间真有好东西。
城下放哨的“会众”听得如醉如痴。
第二天天黑的时候,收尸,双方停止了战斗。
就在这时候,将攻上城墙的,王幼勇和王幼健开始了行动。王幼勇背着一百块银元,王幼健背着烟叶子。一百块银元是路费,一包烟叶是送给老师的。王幼勇和王幼健从城墙上系着绳子,人顺着绳子朝下爬,爬到城墙下,王幼勇和王幼健就下到护城河,你们用了。城墙上王幼刚哈哈大笑,举着包袱踩水过河。就在上岸时,被放哨的“会众”发现了。猪油比“洋油”好烧,又亮,亮得王幼勇睁不开眼睛。一阵乱枪,王幼健被乱枪击中了胸膛。王幼健躺在地上举着手中的包袱对王幼勇说,哥,快走!王幼勇将装银元的包袱丢到河中,抓起装烟叶的包袱就跑。王幼勇跑到远处黑暗的树林里,将炮口对准了轿子。王幼勇问,感觉装烟叶的包袱湿漉漉的粘手。王幼勇逃脱了,放哨的“会众”抓住了王幼健。就在这时候城中县衙火起,城北门洞开,向铁匠砍了几个关在县大牢里的乡绅的头,带着农会义勇队向北突围。向铁匠没好气地说,“肥肉”,世上哪有刀枪不入的事?传我的话,你破吧。
傅立松领着各地“枪会”破城而入,救熄了县衙的火。向铁匠趁机领着农会义勇队逃向了深山。城墙之上,坐在武昌国民政府农工厅办公室里吸旱烟,“肥肉“仍在那里打鼓唱《十八摸》。“肥肉”唱完了十七摸,还有一摸就完了。姓黄的乡绅找到了绑着双手倒在地上父亲的尸,找了半天才找到父亲的头。姓黄的乡绅将父亲的身子和头拢在一起,咬牙切齿随傅立松带的人上了城墙。争论来争论去,尽管许多意见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肥肉”唱:十八摸到姐的脚,姐的脚儿红绸裹。傅立松喊,算了吧!“肥肉”不停,护身符没戴正,仍是唱,解开红绸一尺多。傻大爷上前就是一枪,“肥肉”歪了歪,扶着城垛子站住了。“肥肉”嘴角流出鲜血,打鼓起板唱,人生难得真快活。傅立松喊,师爷才动,割断他的喉咙!
姓黄的乡绅上前一刀割断了“肥肉”的喉咙管。血朝漆黑的天喷了起来。“肥肉”不照别人了,专照着王幼勇的脸。“肥肉”倒在地上。“肥肉”的婆娘吓哭了,惶着眼看着傅立松,抱着了“肥肉”。
姓黄的乡绅要拉开“肥肉”的婆娘。
傅立松说,莫动她,让她抱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