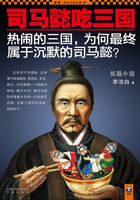参加办案的警官,提前介入的法官、检察官,一共十多人,加上两个武警战士,一个未决的犯罪嫌疑人,正好装了一囚车。坐在车头挨着小袁司机的钟子忱心里暗笑:那年为了要车子赶去处理紧急事情,管车子的邴望兴不仅硬不给派,自己摔了一大跤,三个老弟兄还差一点儿喂进了大卡车的轮子下。为了这件事,姓邴的老小子被轰出了市局汽车队。前年省厅拨给我们这辆囚车,自己坚决顶住尤经纶别有用心的瞎指挥,拒不交出去与其他的单位共用。本科有了这辆汽车,发生了像现在这类紧急的大事情可就起大作用了。
此时,刘传辉挤坐到钟子忱的旁边,轻声汇报自己和小周反复讯问翁卫朋放木箱的山洞及箱子周围的情况。翁卫朋说他自己没有下去,洞里边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但是,他说可以保证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手脚。那小子的态度还算诚恳,他说,我能不能死里求生,全都在此一举了。因而,老刘认为:“他既然要走活路,就决不会再欺骗政府了。如果害了政府干部,更是害他自己。”
刘传辉预审办案很有一套,一般说他的判断也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耳里听着老刘的汇报,钟子忱心想到,花奇人他们在那个山洞里边做没有做什么手脚并不太重要。他们没有做手脚,我们要进去,万一做了什么手脚,我们也要进去!穿上了这一身警服,关键的时刻就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当然,一定要把危险降到最小最小。下去的人,不能多。几个人下去,哪几个下去,都得好好地考虑考虑。
他最后还想到,不能把危险推给别的人。更不能让人家法、检的同志去冒这个险。
劲川市看守所的囚车没有亮警灯,没有鸣警笛,一路没有发出太大的响动。就着前大灯照着的公路快速、平稳、不事张扬地开出了繁华的闹市区。大约行进了半个小时左右,汽车就来到了两条山间公路交岔的丁字路口。
就着淡淡的月光,钟子忱瞪着深邃的双眼很快就判断出来,往东拐过去约两里路程,在公路北边的一处好大的山坳里,是二十多年前自己和尤经纶等人一起劳动过好几个月的市政法农场,也就是如今的市工读学校。想当年这里只是一条狭窄的、只能行驶小型拖拉机等农机具的乡间土路。现如今已经变成为可以对开两辆载重汽车的硬底子公路了。在东、南、北三个方向的丁字路口,路旁建有不少房子,大多是两层的小楼,间杂着少许一层的平房。路两边开有小餐馆、杂货店、理发铺等。宛如一个还算活泛的小村镇,掩去了昔日不见房屋、少见行人的荒凉景象。从东边拐向南边去的拐角是一处不算大的餐馆。在这全小“镇”皆黑唯它独亮的小餐馆里,灯影晃动,人声喧嚷。过了这个路口往南去,已是驶出了劲川市的领地,进入了临劲市城西区洗马公社的地头。这最大的店子刚好建在两市交界的地方,北边正对劲川市的土地,南边则全属于临劲市的“领土”。
囚车继续往南边开去,落进眼帘的全都是光秃秃的小山包。在朦胧的月光下,钟子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劳改农场改成的政法农场那荒芜而又凄凉的夜晚。
突然,翁卫朋喊道:“到了、到了。停车、停车!”
车子停在路边,熄了火。除司机小袁留下来看车外,其他的人都跟在武警押着的翁卫朋后边。往西走过约两里多的山间小道,登上了一个无名的小山包。
“就在这里!”翁卫朋说完,便很认真地看了看地形方位。他领着走到一处地方,在旁边的人看来与周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蹲下去又仔细地看了看,指着一道裂缝报告说,“报告,就是这儿了。”
钟子忱走上前一看,那道石头缝长不过2m,宽不过40cm。个子大的人是钻不进去的,瘦小个子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钻得进去。然而,却有好几个人争着要下,尤其是几个像自己似的“骨干型”干部,除了沉着冷静的刘传辉,一个个都脱掉了棉衣,穿着汗衫短裤,挺立在寒冬的夜风中。只待他老钟一声令下,就直往狭窄的洞口钻下去。一见到这么个架势,钟子忱那凹陷的双眼顿时有点儿发热、发涩。他连忙说:“弟兄们,同志们,赶快把衣服都穿上。这冬夜的山风胜过无形的伤人利刃,可不能大意啊。在进洞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呢,该谁进去还得商量一下呀。穿上,都把衣服穿上!”
几个脱了棉衣、长裤的年轻人,很有些不情不愿地把棉衣捡起来披在身上,下身还是穿着短裤子“乘着凉”。小伙子们是在准备着,到时候只待指挥员一声令下。
钟子忱对刘传辉和周长发说:“老刘、小周,你们先量一下这个洞有几多深吧。”
小周拿出一根30多米长的粗麻绳,在前头拴牢了一块五六斤重的石头。老刘把拴着石头的绳子塞进洞里直往下垂,麻绳很顺利地下去了10多米没有继续下坠了。他这时候想起来,翁卫朋交代的快到洞底有一个可以站人的磴子,就把绳子两边晃动了几下。绳子又继续往下滑去,不一会儿又不动了。再晃动,也没有觉得有下坠的力。
经测量,小周低声对钟科头说:“绳子已经放下去了14米多,和翁卫朋所交代的深度差不多。”
哪怕只存在万分之一的危险,钟子忱也决不能让外单位的同志去承担。因此,他当即作出决定说:“小周,我们两个下洞去!”
一听预审科长如此的偏心,好几个人都嚷了起来:“还有我,还有……”
尤其是方检察官,虎起“猴脸”,扯开嗓子提出抗议:“我抗议,你这个负责全盘工作的科长能下,为什么不让我们下?法官不下去,还有得一说。作为检察官,提取这么重要的物证能不到第一现场吗?”
钟子忱来了个“枪打出头鸟”:“其他人都可以下,就只你方检察官不能下!”
方华焦躁地问:“为什么?”
钟子忱举手环指大家说:“你看,除去翁卫朋和几个战士,在场的谁还是没有结婚的青年郎?”
方华闻言竟然不急反笑了:“嘻嘻。钟科长,你官僚了不是?我的儿子都两岁多了!”
钟子忱一愣,随即又摇了摇头:“你儿子两岁多了?那……那也不行!”
方华真的起了气,大声说:“你这是,强词夺理!”
趁着小方在与老钟纠缠争执,身高体胖的法官石平一声不响地脱光了长衣长裤,低头就往那个石头缝钻。可是,石头缝儿对威严唬人的法官一点面子也不给,硬是没让他这个“同姓本家”通过。他无可奈何地作罢,只好讪讪地穿起衣服,不声不响地站到一边去。
光顾争论不行呀,还得赶快行动。为此,固执的钟子忱,被迫对自己刚才所作的决定作了一点儿“微调”:“好吧,下洞去的人加一个,检察官方华同志。下去的顺序是,小周、我和小方。”
小周领到了打前阵的差使,一边往洞口里钻,一边对几个拉着麻绳的同志开起了玩笑:“同志们,再见啦。嘻嘻,我要是万一光荣了,请给我家里的那一位捎个信,把这个月的工资都代我交党费吧!”
钟子忱第二个下。他一手抓住粗绳子,一手拿着手电筒,慢慢地往下垂,仔细地照着四周的洞壁。他双脚踏到了那个石磴子,就摇了摇绳子,往上晃了晃电棒,仰头大喊:“小方同志,你现在可以下来了。手要抓紧绳子,脚要蹬牢石壁,一定要沉着冷静啊!”
〖JP+3〗待小方挨着他的身边垂进洞底后,老钟就全神贯注地紧盯着底下的战友。小周和小方揿亮各自的电棒,认真地一点一点、一方一方地照看着那只放置在突出一点的石头上边的木箱子。木箱上的白漆字,一个个清晰地收进了他的眼帘,没有发现一丝可疑的爆炸装置。方检察官昂首高声地叫道:“报告钟科长,木箱子上下和四周,没有任何可疑装置和导线。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钟子忱立即命令他们:“好,把箱子拴牢。”
底下两个人拴好了箱子,又抬起来试了试,小方再朝上回答,把这深而狭的垂直山洞震的嗡嗡响:“报告科长同志。木箱子已经拴好!”
钟子忱随即大声往洞口发布口令:“上边掌绳子的同志,请注意了。把稳住绳子,慢慢地往上提。起——”
周长发最后一个被吊到石洞的上面来,他一眼看到静静地躺在几公尺以外大石头上边的木箱子,就笑嘻嘻地走近前去。他先冲钟子忱和守在箱子旁边的刘传辉嘴巴一咧,算是打过了招呼,伸手就准备去揭箱子盖。刘传辉突然发出一声低喝:“慢——!不能鲁莽。”
钟子忱会意地一点头:“你们几个到旁边找地方隐蔽去。”
刘传辉、周长发、方华等人,当然明白钟子忱的意图,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小周和小方还伸出了手,要去揭那只木箱的盖子。老钟双眼一瞪:“干什么你们!人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我是头,大家就都得听从我的指挥。快,你们都给我撤到20多米远的那一块大石头的后边去!”
满满一箱子十二枚手榴弹,一百多发长、短枪子弹,还有一个冲锋枪弹匣,安静地躺在揭开盖子的手榴弹专用木箱里边。在场的人除去心情复杂的翁卫朋全都高兴得喜笑颜开。现场指挥员钟子忱也一样,他阴沉的脸上荡出一片难得一见的灿烂。
深夜11点半。预审科长钟子忱领着这一支短小精干的小分队,押着带路指认有功的犯罪嫌疑人翁卫朋,带着满满一箱子战利品胜利地打道回营了。凯旋而归的劲川市看守所囚车开了几分钟,到达了那个两市交界的丁字路口。满满一车子警官、法官、检察官,还有武警官兵全都没有吃晚饭,直到现在才觉得肚子饿了,实在是太饿了。
钟子忱当即决定,让司机小袁把车子直接停到那个一屋朝两市路口“最大”的餐馆门前。全车的人相跟着下得车来,鱼贯拥进那个正准备打烊的餐厅。中年胖经理连忙笑脸相迎:“各位辛苦了,请坐请坐,大家都快快请坐。”
钟子忱大声吩咐道:“老板,尽你店里之所有快点给我们做一桌丰盛的酒席来。手脚麻利点,越快越好!”
伙房里边的厨师手脚倒不迟钝,亲自跑堂的经理行动也还迅速。饥肠辘辘的人们,都像饿了十天半个月似的直嚷嚷:“老板,老板。快点,快点!”
不大一会儿工夫,经理就脚不停地先后端出了七八大盘热气腾腾的素菜、荤菜。每上一道菜,身着四种制服的官兵们就众箸齐下,风卷残云般地给消灭得点滴无存。论吃相,可真是不敢恭维。尤其是邱为群、石平等几位穿大号异型制服者更是显得馋不卒睹。这叫名为酒席,其实只有席没有酒,是以温开水作代。多数人连开水也不用,生怕耽搁了挟菜。毕竟“立竿见影”的,还得靠后者啊。
一天两餐“牢饭”早就已经进了肚子的翁卫朋,此时也没有让他饿着、馋着。每一道菜,那经理都按照方检察官的安排给他端去了一小碟,比起坐上了席的平均数只多不少。他此时的待遇,可是够相当高的“级别”了。他小子低着光头吃着吃着,竟然无声地掉起了眼泪。
检察官方华马上趋近前去,冲那小子低声问道:“怎么,又哭了?”
检察官这一问,翁卫朋竟然哭出了声:“我,呜……我真不是人,我真不是人。政府对我这样好,我还给政府打了埋伏,没,没有把问题全部交代出来。”
离得不太远的钟子忱,一听此言,连忙起身赶到翁卫朋所呆的墙角。既严肃又亲切地对他说:“说吧,你现在把问题都说出来,还算是你坦白交代的!”
方华又紧跟着补上一句:“你的交代,只要是够得上立功条件的也还算是你有立功表现。”
翁卫朋不敢放大声音,他是怕被外人听见给泄漏了出去会遭到同伙的报复。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学校,啊,是说我们的劳动学校,还藏得有子弹。”
囚车很快就开到了劳动学校的大门外边。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学员”被关进了市看守所,其余的一哄而作鸟兽散。所以,在这深更半夜时,在那高高的围墙内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晃动,听不到一点儿响声传出。身为这一校之长的邴望兴,竟然擅离职守。他垂头丧气、不声不响、偷偷摸摸地溜回到市公安大院他自己的家中,再也没有到这学校里来露一回面。那四个“老师”中倒只走了一个,还剩下外号“寡鸡蛋”的等三位。为生活考虑,他们自己组织了起来,轮流值班看守这庄园似的学校没有离去。夜半来的“造访者”们,很容易地叫开了大铁门。来开门的,正是那一个除翁卫朋之外,别人并不认识的“寡鸡蛋”。当然,也没有人去注意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有点儿怪异的神色。
老钟交代那开门人:“师傅,你就在这里,得等我们走了以后再关校门。”
囚车开进了学校,一直朝最里边开过去。路的尽头,是一排连几间的监室似的平房。翁卫朋跟着大家下车以后,指着最里边的那一间说:“报告,就在这间杂物仓库房顶的红瓦下边,藏着一个铁盒子。”
钟子忱伸手一一点向预审员小周、法官小石、检察官小方:“你们三个上去!”
三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就着汽车前大灯和十来支手电的光亮,手脚麻利地爬上了屋顶。爬在最前边的周长发停了下来,朝下边大声问道:“翁卫朋,是这里吗?”
翁卫朋赶快昂起头,大声回答:“啊。再往前边一点点,还在前边一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把屋脊下边第三口瓦揭开,就可以看见了。”
小周揭开了几块机制瓦,果真看到了一只一尺来长、半尺来宽的长方形小铁盒子。他把那只盒子捧下房顶来,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里边果然装满了子弹。经过清点,他脸露喜色地向钟子忱报告说:“钟科长,盒子里共有三百五十五发子弹。其中,手枪子弹三十发、步枪子弹三百二十五发!”
面对又一个还算可观的“战利品”,钟子忱的心里边并没有一点喜悦,有的倒是一阵阵地惊悚:啊——哟!这个翁卫朋看起来好老实,他还留了这么一手哇。假如,假如他们,在那个竖直的山洞里边……老钟不敢再想下去了。
是啊,如果那几个家伙万一在深洞里边做了什么手脚,安了什么机关,势必会造成一次重大的人员伤亡,进到那个深洞里边去的人还能幸免?即使他自己葬身洞底,也是万死难赎重罪的。原因很简单,这次是他违抗了局长舒成铭的意见,自己擅自决定行动的!还有,据翁卫朋先前的交代,他和花奇人、洪成孝等五个人一起炸掉了十六枚手榴弹,果真如此吗?果真彻底地清除了这个很大的隐患吗?手枪子弹还差四十一发,炸药还差整整一大包共4kg,又都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