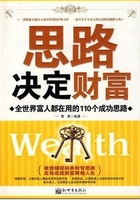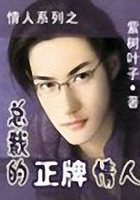兰色姆之前似乎没人把这名词用于文学理论,奥克斯汉得勒(Neal Oxhandler)认为受现象学影响的德国和法国文论家在三十年代开始使用此词于文学(“Ontological Criticism in America and France”,Modern Language Review,January,1960)。但是,看来兰色姆当时并不了解现象学的本体论研究。最近我们看到我国文论界有人开始使用此词,如《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纪川的《试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本体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开宗明义:“文艺的本源,文艺的社会功用以及文艺发展的动因等问题构成了阐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本体论。”这样的“本体论”的面似乎太广了一些。
兰色姆长年坚持鼓吹“本体论文学理论”,但他使用此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却不容易捉摸。我们仔细考察他使用此词的方式,可以发现他在两个意义之间游移。首先,他常将“本体的”与“实质的”(substantial)、“根本的”(fundamental)等词并用,在一段类似定义的文字中他说:“数学家的构造物……有可能存在,但不一定确实存在;有可能确实存在,但不一定有用处。这样,数学运算就变成一种思考推理的东西,变成了在用意方面非常一般化,非常基本化的东西,除了用‘本体’字样,就无法说明。”
瑞恰慈有一个提法或许接近兰色姆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这样,文学作品就是本体,它描写的那个世界却是“有可能存在,但不一定确实存在”,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源。瑞恰慈认为作品的价值在于引起读着的感情反应,浪漫主义文论家认为艺术即作者的自我表现,那么作品就是文学活动的终端产品,至少是中间环节,而不是本体。维姆萨特反驳他们说感情本身无法表达,我们只看到诗歌语言如何表达感情,这话可作兰色姆这句话的注脚:“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
兰色姆“本体论”的这个意义是从艾略特的“非个性”(impersonality)论演变而来的。“非个性”论所反对的是创作论上的表现论,而“本体论”主要是针对瑞恰慈的读者感情反应论,但两者指向同一方向。
艾略特在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中写了这句似乎故意夸张以惊世骇俗的名言:“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反对浪漫主义的表现论和滥情主义。对诗人来说,整个文化史的沉重压力比诗人自以为凌驾一切的“个性”重要得多。二是说个性和感情只是作品的语言媒介的品质:“我的意思是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那只是工具,不是个性”,“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实际上,艾略特并不认为诗人无个性,而是认为个性对创作无大用,每个诗人必须像莎士比亚那样努力去“促使其个人的私自的痛苦转化为丰富的、奇异的、具有共通性的、泯灭个性的东西”。同上,p10。诗人在创作中并不像一个成分进入反应,而只是一个催化剂。艺术家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泯灭自己的个性”的过程,而诗的文本就脱离了其“创作之源”,成为艺术本有的唯一的存在。
这第二层意思也就是兰色姆本体论的根由。这是新批评理论的一条主线,也是对延续一百多年的浪漫主义表现论的反冲。本世纪初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表现论美学和强调创作直觉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欧陆兴起,新批评派指责克罗齐美学是“浪漫主义的最高理论总结”,是“过了头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新批评派的势力是克罗齐表现论和超现实主义始终未能在英美站住脚的原因之一。超现实主义的鼓吹者,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也承认超现实主义是在再现浪漫主义原则。只有当新批评势力消亡后,六十年代在美国才出现“新超现实主义”诗派。
应当指出,“本体论”理论实际上也是唯美主义的艺术自足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作品既然无用不真,自在自足,它就只能就地踏步,自己解释自己。唯美主义者理论思辨之肤浅使他们无法清晰地阐明这个问题。他们经常舍不得浪漫主义表现论的“激情(passion)说”,例如华尔特·佩德(Walter Pater,1839—1894)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就认为“激情”是创作的基础,但经常又提出类似“非个性”的看法。例如济慈的“消极能力”说(negative capacity):“谈到诗人的性格……它不是它自己——它没有个性,它是一切,它又什么都不是。”“承认这一点,叫我难为情,然而这是事实:我说过的东西,都不能假定为从我真正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见解。”济慈的看法接近新批评。新批评派崇拜的柯尔律治倒是个表现派,柯尔律治断言:“什么是诗?这差不多等于问:什么是诗人?”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都意识到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论的短处,他们都表示了对拉马丁和缪塞等人的滥情主义(sentimentalisme)的反感。在写《包法利夫人》时,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愿把艺术看作激情的容器,像把夜壶。”在致乔治·桑的信中他写道:“艺术家不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人不算什么,作品才重要。”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巴那斯派的“不动情”论(i-mpassibilité);马拉美的“非个人化”(impersonnel)说;乔治·莫尔(Ceorge Moore)的“个性之外”说。一般说,唯美主义者强调他们是艺术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宁愿戴上斯芬克斯的面具,而不想露出“心灵的呼喊”(cri de coeur)。
因此“非个性”或“本体批评”都是有其长期发展经过的,并非艾略特或兰色姆的别出心裁的看法。二十世纪批评的非个性论,与十九世纪最大的不同是越来越把作品看作一种文化的存在,而不是把它当作作者一种精心设计的姿态。然而他们的源头都是从康德开始的艺术自足论。兰色姆正确地指出:“批评依靠本体分析正是康德的意思。”
形式主义理论充分展开后必然抛弃表现论。美学家克莱夫·倍尔(Clive Bell,1881-1964)论证说:“到画展找表现纯是徒劳,你只能找到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只有当形式令人满意,产生这种形式的思想状态才可能是艺术上令人满意的。”这样,作品就完全遮蔽了作品产生的过程,包括创作者的灵感、冲动、感情等等。
但一般形式主义的这种论述显然没有达到兰色姆的“文学本体”深度。某些结构主义者也试图从哲学上阐述以作品为本体的思想。福柯(Michel Foulcault)说:“‘我’被消灭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发现‘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十七世纪的观点,只有如下一个区别: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无主体的作品“代替神”成为主体,成为文学活动中本质性的存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论证路线与新批评派惊人的一致。
(第四节) 本体论作为一种平行理论
从兰色姆的本体论还可发现另一层意思,这与新批评所关心的“诗歌真理”论有关:“诗作为一种文体,其特异性是本体的”,因为,“它处理一种科学文体无法处理的存在状态,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诗歌意在复原那个我们通过知觉和回忆散乱地了解的(比科学所处理的世界)更紧凑更致密的本源世界(original world)。”因此“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正如一个兰色姆的评论者所指出的:“兰色姆是一个忠实于‘世界的肉体’之现实的批评家,他希望诗在艺术上展示这种现实。”
所以兰色姆的本体论有两个意义:既说诗自身是本体存在,又说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从一个意义滑进另一个意义。韦莱克对本体论的解释也把这二者并列:本体论即作品的“存在样式”(mode of existence),而这种样式即是“文学作品是自成一类的、有本体地位的、有认知力的客体”;布鲁克斯和沃伦也指出诗一方面自存自足,另一方面却又使我们“更意识到外界的生活”。布鲁克斯在另一文中更明确地说,虽然他只在作品的结构中寻找矛盾因素,但是“除非一首诗体现了我们通过经验所知的世界的矛盾,否则这首诗就不可能显得真实”。
如果我们把兰色姆的两层意义与瑞恰慈“拟陈述”的两层意思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正是针锋相对的:诗是本体,因此其价值不在于读者的心理反应(或作者想表达的感情);诗表达真理,因此它不是无客体的“拟陈述”。
但是,“本体论”的这两层意义如何调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本无所谓“文学本体”,这只是兰色姆比喻性地搬用哲学术语,所以不必太认真。但实际上兰色姆的矛盾体现了新批评派理论的根本立足点之复杂性。他实际上是一只脚踩在形式主义船上,另一只脚羞羞答答地向亚里士多德“模仿论”伸过去,这是一种我们常称为“平行主义”(parallelism)的折中主义理论立场。韦莱克就指出这两者要调和是大难事,因为两者中间有个“本体鸿沟”(ontological gap)。艾略特意识到这中间有问题:“语言在其健康状态中呈现(present)客体,而且与客体如此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一。”但是何谓“完美”?为什么完美才能与客体“合一”呢?
要弄清楚这问题,不得不略微触及哲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十九世纪唯美主义者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采取这种立场。波德莱尔强调“再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是没有好处的”;英国宣扬“为诗而诗”的布拉德雷(A.C.Bradley,1851—1935)说:“形式主义完全正确,他们反对把艺术品当作仅仅是某一事物的摹本或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