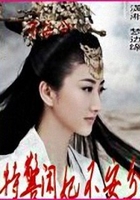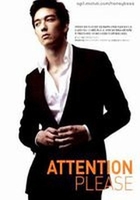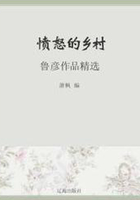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前言所提出的新批评在五十年代末突然失势的原因问题,单单学术上的兴代无法完全说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1957至1958年间正是美国文学和社会思潮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从五十年代初“黑山派”(Black Mountain Poets)开始的一股反抗学院派的“开放诗”(Open Verse)潜流在1956年旧金山朗诵会上破门而出,“垮掉的一代”标志了存在主义思潮进入美国,渐渐演成六十年代欧美的“左倾”社会思潮。
新批评派的得意弟子、美国当代最著名“学院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也受到垮掉的一代影响,断然抛开艾略特—兰色姆诗风,1958年他发表诗文集《写生》,开创了“自白诗”(Confessional Poetry)潮流。自白诗热衷于袒露内心感情和个人生活的隐私,完全反“非个性”论而行之。而自白诗之风横扫诗坛,使新批评派影响下的诗人纷纷倒戈,这与文论界背离新批评是同时发生的。
美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使新批评的保守主义不能适应,新一代诗风的多样化使新批评狭隘的理论不能适应。在这种局面中,新批评派失去了根基,结构主义的理论便应邀而来,取代新批评派而出现在美国文坛,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倒是第二位的原因。如果说新批评派适合于叶芝、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歌,那么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则适合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第三节) 新批评的特点
新批评派基本上是一个英美文学理论派别,二十世纪上半期与它在方法上相近的学派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俄国形式主义外,法国的“文本解释”(explication de text)批评很接近“细读法”,但那是法国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并没有一个形式主义理论体系作后盾;德国批评家沃尔夫岗·凯瑟(Wolfgang Kayser),瑞士批评家爱米尔·斯台格(Emil Steiger)等人,关注作品的个体批评,接近新批评派。但总的来说,新批评派并非一个西方世界共有的潮流。
新批评派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论,本书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一点。这里,我们不打算再将新批评的这些特点一重述,而只指出几个主要方面。
新批评派与其他形式主义之不同首先表现在他们试图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虽然他们是从一种混乱的折中主义哲学立场出发观察这个问题,因而不可避免落回形式主义共同的唯心主义中去,但由于其他形式主义大都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显出其难能可贵。
新批评派的第二个特点,而且也是新批评派理论中最突出的优点,是他们对文学作品结构的辩证理解。大部分新批评派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文学作品中矛盾因素的对立调和,尤其是理性与感性,具体性与一般性的同一。虽然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是肤浅的,很不自觉的,但在这一点上新批评派暂时解脱了形式主义的羁绊。
新批评派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在批评方法上持一种绝对的文本中心态度,从而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心理原因,把读者反应问题,文学社会效果问题,文学作品群体特征及文类演变等等全部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似乎没有一种形式主义在批评方法论上如此严峻。
新批评派的第四个特点是以语言特征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作品的全部结构特征——尤其是矛盾因素调和的各种方式,都首先在语言特征上表现出来,他们甚至以文学语言特征作为文学区别于科学的特异性;这虽是把唯美主义以来语言崇拜推到新的高度,但其论证本身有参考价值。
新批评派的第五个特点使他们过于僵硬的方法论得到某种程度的补救,那就是他们对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视,和他们在批评实践中的细腻灵活态度。因此新批评派虽与实用主义美学不一致,但不少论者认为新批评派终究还是充满了美国各种现代社会科学都免不了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当他们的理论或方法论难济其穷时,他们能在批评中暂时置自己的教义于不顾。
新批评作为一种形式主义,与其他形式主义在某些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作为一种现代形式主义文论流派,它与结构主义相似点更多一点。有一点需要说明:新批评派之产生在时间上与结构主义几乎完全重合,虽然新批评派得势比结构主义早些,但它们基本上是平行地,互相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然而,从一系列问题来看,新批评派可以被视为现代形式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首先,新批评派决定性地把形式主义从反理性主义朝理性主义方向推进,本文已对此详加论证。反理性主义是旧形式主义的灵魂,新批评派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摆脱反理性主义,探索理性与感性结合问题。俄国形式主义也是以“反对象征主义的主观主义美学原则”为己任,而结构主义则是五十年代末作为反理性的存在主义的对立面而兴起的。
列维斯特劳斯在五十年代初指斥当时的法国文论界依然在柏格森的影子中徘徊,他呼吁以索绪尔整饬的系统观念来取代柏格森的个人意识理论。但是新批评使美国文论比欧陆早二十年走出了“柏格森的影子。”实际上理性主义在欧陆文论中一直到结构主义兴盛起来才算站稳了脚跟。因此,理性主义是当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特征。
其次,新批评派是从早期形式主义极端态度中渐渐脱出身来的中间环节。唯美主义宣扬其教义是直言不讳的,说话狂热走极端而不加论证。
新批评派在理论上努力寻找折中立场,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突破形式主义束缚,但是在批评方法上他们甚至更加严守形式主义的狭窄阵地。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情况:例如退特的张力论表现出对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结合问题相当出色的见解,但他在反对从文学的社会效果批评作品问题上,态度与唯美主义者一样偏激;例如维姆萨特能试用辩证法处理诗歌真理等问题,却用两个谬见把新批评方法论紧锁在形式主义囚笼里。结构主义比新批评高明的地方正在于其方法论有更多的辩证因素,有比较开阔的视界,因而能从更多的角度观察研究文学这种最复杂的人类文化活动。
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日益复杂化完善化的中间环节。唯美主义几乎无理论基础,他们的文论往往是基于直觉之上;新批评派试图构筑一个哲学基础,但主要还是利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二十世纪初一些哲学派别的个别命题;而结构主义则几乎汲取了二十世纪所有主要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分析哲学、现象学与实用主义。唯美主义的批评不要方法论,他们主要搞印象式批评;新批评固执地自囚于客观主义纯批评圈子中,其研究工具也只是传统的语义学。兰色姆曾高度赞扬查尔斯·莫理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学,他在《新批评》一书中说,倘若符号学家莫理斯讨论文学,那么他的书应当把莫理斯列为“新批评家”之首。可见他们的立场之相近。而结构主义的方法繁复多样,作为其工具来源又同时作为其方法模式的索绪尔符号语义学比新批评派的语义学方法论视野宽得多。新批评派外围人物中,伯克的方法论是最多样化的,因而有论者认为新批评是结构主义的先驱。五十年代初,兰色姆带头向伯克的多学科方法论靠拢,曾激烈反对伯克的布拉克墨尔在五十年代初的“姿势论”中跟随伯克走出了新批评的圈子。可惜五十年代活跃的“第三代”新批评派没有继续这个趋势,反而致力于把“新批评”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