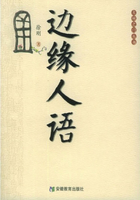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第一节) 新批评派改造反讽概念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最叫人头痛的概念之一,论者称它为有“臭名昭著的难以捉摸性质”(notorious ellusiveness),因为它“不仅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概念上还不断地在发展”。从古希腊一直到十六世纪,反讽只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次要的修辞格,从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反讽概念不断膨胀,一直到新批评派,反讽不仅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了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同时,又有一些英美批评家如和A·R·汤普森则努力反其道而行之,把反讽范围拉回十六世纪之前的传统看法上去。
我们不准备对反讽的历史变化问题作全面论述,但我们要了解新批评派心目中的反讽,就不得不略为回溯此概念的发展过程。在第五章中我们已谈及反讽的辩证哲学意义,本章中我们将着重谈作为一种语言技巧的反讽。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ōnia,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角色典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就是在扮演这种角色。所以,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相,意思暗指真相;吃反讽之苦的人一心以为真相即所言,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
新批评的反讽概念离此原意已发展得相当远。早在1921年艾略特在论玄学派诗人马伏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的论文中就提出玄学诗的特征是“理趣与反讽”(wit and irony)。次年,瑞恰慈提出了诗必须经得起“反讽式观照”,也就是说,“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燕卜荪在《含混七型》中把反讽概念使用于实际批评,他的七型中后两型实际上是反讽式复义,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新批评式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布鲁克斯。他在1942年发表的《悖论语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一文,首次详解这个概念,只是这时他称作“悖论”,而不称作“反讽”,我们下面将谈到两者的异同。而他的最著名论著《精铸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1947)全书主要是在用实例分析证明这个概念之重要。
布鲁克斯特地详细分析了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因为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华兹华斯一向被认为风格最质朴无华,语言简肃晓畅,重在自然之趣,传统意义上的悖论——一种狡黠的语言技巧,即似非而是之论——在华兹华斯这样的诗人作品中应当是看不到的。布鲁克斯指出,像《西敏寺桥上作》这首描写伦敦之黎明的诗,似乎临事直书,平淡乏味,却为人传诵。这首诗的魔力在哪儿呢?在于以肮脏拥挤喧闹著称的十九世纪初的伦敦,在晨光熹微之时,却有一种勃朗峰那样的大自然庄严肃穆的美:
太阳从没如此美地把一切沉浸在
最初的辉光中,无论幽谷、山岩、嶂峦。
一种“惊奇”(wonder)使诗人(和读者)心中充满敬畏,诗情违反常情,奇趣从中而出——既然华兹华斯的最简朴的诗都如此,其他有什么诗能逃出此例?
但布鲁克斯指出,最充分地发挥了“悖论—反讽”力量的是玄学派诗人。布鲁克斯用细读法详解了邓恩的名诗《圣谥》(Canonization)。这首诗是一个陷身“丧失理智”的恋爱狂热中的人对他“头脑清醒”的务实的朋友之劝告所作的答辩。但邓恩没有用浪漫主义激昂淋漓的语言。全诗在“外延”(逻辑)的展开上就够复杂的:正因为他们下决心抛开尘世,所以在对方身体里取得了自己的世界;即使世俗的人认为如此狂热的恋爱是不法的,他们却因为情愿为爱情而死,情愿简单地葬身于藏骨灰之“瓮”,而像凤凰一样永生,因此应当被谥为圣徒。这首典型的玄学派作品语象密集,展开速度极快:
我们不能以爱而生,就为爱而死
即使我们的行传不适合
墓园与灵车,它却适于写诗……
布鲁克斯指出:“邓恩的想象力充满了‘合一’的问题……这里的溶合不是逻辑上的,它违反了常识,它把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紧合在一起。”
布鲁克斯借用莎士比亚的著名哲理诗《凤凰与斑鸠》(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的诗句:“如果诗人必须忠于他的诗,他必须承认诗既非二,又非一。”但使新批评派叹息的是自莎士比亚与玄学派之后,“胆怯的诗人遇到一物双名时总是退避三舍,从德莱顿时代起,(英语)诗歌史可以取个副标题《半心半意的凤凰》。”
布鲁克斯的分析极为精辟,而且,我们从他的论证亦可看出,在实际分析时,他把反讽概念重新局部化。在这里,无论称之为反讽还是悖论,他谈的都只是诗歌的语言技巧之一。
但是布鲁克斯引出的结论却是普遍性的,他说:“悖论是诗歌不可不用的语言,而且是正合诗歌使用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语言清除悖论的所有痕迹;而诗人所表达的真理只有用悖论语言来处理。”他认为这是“诗的本质”。因此,在新批评看来,无诗不悖论,无悖论则非诗。
最后,布鲁克斯在1948年的论文《“反讽”与“反讽诗”》中,给“反讽”下了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反讽是“一种用修正(qualification)来确定态度的办法”。因此,反讽成了诗歌语言最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呢?布鲁克斯说,这首先是诗歌的“本体特征”所决定的。因为,“诗人把他的词在语境中赋以确切的含义时,不得不持续地些微地修改其含义。它记录下诗中不相容成分的张力关系,这些张力关系被合成一个整体。反讽承认强制因素。”另一方面,反讽又是文学语言这工具之不顺手所决定的:“诗人必须考虑的不仅是经验的复杂性,而且还有语言之难制性;它必须永远依靠言外之意和旁敲侧击(implication and indirectness)。”要把词新鲜地使用,这种张力关系始终存在。
我们知道,根据瑞恰慈的语境理论,诗中的词语必然受到语境压力,因此,正如弗赖所解释的,诗中“所说”,多多少少在某意义上是“非所指”。也就是说,诗中文词的意义总要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而布鲁克斯把反讽最广义地定义为“承受语境压力”的语言,因此,诗的语言就是反讽语言。
兰色姆虽然反对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但他也承认反讽“只要你去找,就很容易找到,可以说是普遍存在”。
有论者强调,反讽必须有谐谑讽刺意味,而偏偏新批评的“反讽”概念完全摆脱了任何这种喜剧成分。瑞恰慈说:“还有什么比悲剧更能明显地说明‘使对立和不协调的品质取得平衡或使它协调’的说法呢?怜悯(这是一种趋就的冲动)和恐惧(这是一种退避的冲动)在悲剧中取得协调。”
这种新批评式的反讽概念,被传统的文学理论家指责为“扩大化”和“弱化”。由于本文只讨论新批评派,所以我们不准备对这种术语之争评是断非。
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新批评的反讽理论并非完全出于他们别出心裁的杜撰,它经历了从德国浪漫主义者开始的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此做出主要贡献的是许莱格尔兄弟和索尔格(K.W.F.Solger)。F·许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指出莎士比亚悲剧中就有反讽。他甚至指出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A·W·许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则在莎士比亚剧本中找到“自我欺骗式的反讽”,靠这种反讽,莎士比亚把严肃的与幽默的,幻想的与平凡的因素相平衡。这实际上是瑞恰慈及新批评的矛盾调和论之滥觞。
英国十九世纪文学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在其名篇《论〈麦克白斯〉中的敲门声》中分析了莎士比亚此剧一个细节的特殊效果:麦克白斯夫妇杀了人以后突然听见敲门声。德·昆西说这敲门声“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人性的回潮冲击魔性”。而德·昆西在《自传》中更进一步分析道:“真理的所有有分量的方面……都是使人惊异的,都是悖论式的,我们不用费力气寻找悖论,相反忠于自己经验的人,会发现他用全部力气都难以把他所知的真理所包裹着的悖论压下去。”
存在主义的始祖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ёn Kierkegaard,1813—1855),把反讽看作一个哲学概念,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一段历程而提出。他在《反讽概念》一文中对存在主义式的反讽观提出一个著名的定义:“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
我们可以说新批评把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与作为哲学概念的反讽紧密结合起来,是汇总了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反讽概念的整个发展过程,而把它演化成更全面的诗的“本体性”原则。
(第二节) 反讽概念中的若干问题
新批评的反讽理论中首先一个触目的混乱是将悖论与反讽两个术语混用。在修辞学上,悖论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它也是一种古代人就在研究的修辞方式,因为悖论在《圣经》或我国的《老子》等古代哲学宗教文献中大量存在。在古代修辞学中,它与反讽的区别还是比较明确的:悖论在文字上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例如,我越想他,就越不想他,或“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反讽则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互相对立,悖论是“似非而是”,反讽是“口非心是”。
但是,反讽和悖论还是有相同之处的,那就是他们表现了一种矛盾的语义状态,而他们都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表现法。
反讽概念在现代被扩张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两者界限难以区分了。我们在上文中就可看到德·昆西与F·许莱格尔关于悖论的说明和许莱格尔兄弟对反讽的说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布鲁克斯在这两个术语上犹疑不定。在《精铸的瓮》中,他认为悖论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它包含两种形态:惊奇与反讽。惊奇的典型是华兹华斯《西敏寺桥上作》,反讽典型地表现于邓恩的《圣谥》。但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他却认为反讽是包含其他一切的术语:“反讽是我们表示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是表达语境中各种成分从语境受到的那种修正的最一般的术语。”这样,到底何者包括何者呢?
实际上,在布鲁克斯手里,这两者没有根本区别。他前后两文的混乱是术语上的混乱,而不是概念上的混乱。由于大多数文论家自古以来就认为悖论是反讽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新批评派使用反讽一词比悖论更多,所以我们这一章的章题就用“反讽”一词。我们在下面详细讨论时就可以发现:狭义的悖论的确只是反讽的一种,而广义的悖论与反讽是一回事。问题是语焉不详。
反讽之所以为新批评派所津津乐道,除了其张力性和有机组成外,在传统的文论中也都承认反讽有一种“非个性”性质。索尔格认为缺乏反讽精神的作者把他们的主观性与他所同情的人物或观点认同,莎士比亚把每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我们不可能怀疑其同情心,但莎士比亚却与他们的人物保持距离。这样,莎剧表示的就不是莎士比亚的主观性,而是“表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居高临下的“反讽精神”。用弗赖的说法就是“距离的客观态度”。因此,反讽与艾略特“反个性”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一种基本的创作原则。
(第三节) 反讽的各种类型
布鲁克斯没有像燕卜荪处理复义一样把反讽分出类型,要把问题说清楚,把各型反讽分开来讨论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