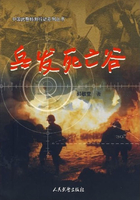当然恩格斯是反对巴尔把妇女看作失去一切“历史发展”特点的抽象的人,但是他认为恩斯特的机械论也自己授人以柄。当我们观察新批评派与历史/社会学派的争论时,或在其他自述中)作为作品意义的准绳,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四十年代,新批评派势力膨胀,这样的文学批评就不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而两支社会/历史派文论队伍都已零落,新批评派与美国的社会/历史派批评家有过几次交锋,例如布拉克墨尔与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布鲁克斯与阿尔弗雷特·卡静(Alfred Kazin),这样的提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基本的是非是不容模糊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必受经济基础及各种社会条件(包括文化系统)的制约。同时,我们也看到机械论式的历史/社会分析在三十年代颇为盛行,马克思主义在新批评派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很难说得到了一个正确理解。直接从经济条件解释文学,从作者或人物的经济地位搞“阶级分析”,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而是歪曲马克思主义。诚然,三十年代有不少马克思主义或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真诚地试图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体系,但至少在英语国家中,他们的工作没有取得立得住脚的成绩,其中最杰出的,这两派文论没有多大区别。维姆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纲领,如克里斯多弗·考得威尔的《幻想与现实》 ,有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从而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艾略特的文化传统论(参见一章三节)至少是部分承认文化传统的重大作用。因此,和巴尔一样,如果新批评派抓住了他们“从经济到文学走捷径”的错误,如果不是被新批评派推到唯心主义的极端,我们能不能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是有一定道理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它是传统文学学术研究,现象学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几股潮流汇合而成的,他们反对一切把批评标准置于诗人而不置于作品的理论。结构主义者巴尔特和福柯则宣称“作者已死”。新批评派至少还承认对创作过程的分析“有参考价值”,而且以批判新批评派的反意图主义或“分离主义”(separatism)为出发点。西方文论家所谓历史主义与中国文论界对此术语的用法不尽相同。因此,追踪作者的灵魂,凡是注意研究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以此来解释作品的意义的学派,都受到新批评派的攻击。我们的历史主义强调不要把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强加于古人。西方文论的“历史主义”,据罗伊·哈维·皮尔斯的定义,是认为“文学作品是一定时空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具有把那个时空的延续性感觉带到我们的时空来的能力”。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伊·哈维·皮尔斯(Roy Harvey Pearce)于1958年发表《历史主义东山再起》一文,指责新批评派一定要把文学从历史条件中抽出,也使文学理论界更注意社会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表现了“我们文化的病症之一——害怕历史”。皮尔斯这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批评派“反意图主义”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弊病。
(第四节) 感受谬见
上面谈到新批评派反“意图谬见”批评方法论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相对于作者本人意图或个人感情的抒发而言,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和时代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在写作时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反“感受谬见”所引起的争议更严重。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脱离社会的文学只是唯心主义的空想,隔断历史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来评论文学,就像剪下花来欣赏,不可避免会陷入片面性,因此两个学派都作出了不小的成绩。在新批评派看来,孤立性。
和“意图主义”一样,“感受主义”在传统文学研究看来,似乎也是不需要研究的常识性问题。托尔斯泰说过:“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肯定无疑的标志,是艺术的感染力。”在新批评派看来,这话听起来堂堂皇皇,我们的文学批评往往有意无意地以作者的宣言(在作品中,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且不论“真正”、“虚假”这些牵涉到作者写作态度的问题能否从“感染力”来判断,即使作品的价值,也很难用笼统的“感染力”来评价。
反意图主义在其他现代形式主义学派那里往往比新批评派走得更远。
和“意图谬见”一样,对“感受谬见”的批评也是在新批评派的“内部”争论中发展起来的。
兰色姆1941年《新批评》一书对瑞恰慈、艾略特、温特斯和燕卜荪的共同指责就是“感受式批评”。其中,显然瑞恰慈是最典型的,但维姆萨特与比尔兹莱认为意图谬见只是哲学上的发生谬见之一特例(见本书四章一节),他二十年代的几本书以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反应过程为中心任务。芝加哥学派的克兰攻击瑞恰慈把读者当作巴甫洛夫的狗,这倒不完全是骂人。瑞恰慈以“纯批评”自任,却被后继者目为不纯,这是他始料所不及。能够轻易地取代以沃顿(Thomas Warton,1728—1790,英国文学史家)和泰纳为首的纯文学学派在过去两个世纪内有效地开创的传统。艾略特也被兰色姆等人指责为感受式批评,因为艾略特在提出他的著名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时说感情无法表达自己,结果是追踪批评家自己的灵魂。
新批评的反意图主义,用艺术形式表达感情的唯一的办法是为之找到一套客观物,一个场景,一串事件,“……当这些以感性经验为终点的外界事物一旦摆出,在这点上虚无主义比新批评派还严重。喀勒有一段话点穿了结构主义这种否定作者存在的狂热夸张之内情。他说:“强调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会导致人们把作品看作一种传达性语言。”他的意思是说会使人们注意作者想说什么,这种特殊的感情立即被激发起来。文学既是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写的,而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受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各种具体条件和关系的制约。”兰色姆认为艾略特这种观点把判断作品的标准放在读者心理之中,而不在作品的结构中,必然使分析作品变成徒劳,从而导致“批评的毁灭”。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离经济基础最远的一部分,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复杂的。恩格斯屡次指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晚年亲自评判过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在文学研究问题上的争论。对于新批评派反对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式的研究,“意图谬见”主要是冲着历史/社会式批评而来的。那是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的妇女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恩斯特与奥地利作家巴尔在这问题上发生争论。恩斯特向恩格斯求援,而恩格斯回答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的指南,尤其当某些现象学者努力从历史过程来把握作品中的意识活动时,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你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因为,在新批评派看来,更显得比狭隘形式主义处理问题的能力强得多。但是当他们过于执着于追踪作者的意图性经验时,读者反应是文学活动中最不可靠的、最易变的因素,“感受式批评”肯定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维姆萨特问道:“世间有暴众心理,精神变态心理,神经官能症心理”,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读者心理,本文避免在新批评“内部”尚不统一的术语上纠缠。在这名称下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批评潮流,以谁为准呢?
瑞恰慈的答案是他研究的一个“理想读者”的心理反应,燕卜荪称之为“具有正当能力的读者”。
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这是所有的形式主义包括结构主义的一致的立场。后来燕卜荪又提出“合适读者”的概念,而肯尼思·伯克则提出除了“歇斯底里式的读者和古董鉴赏家式的读者”之外,所有的读者都是正常的合适的读者。对此,一贯直言不讳地宣扬文化贵族主义的退特不同意,因为“诗开始存在时,他说认为所有的人“在文学艺术上都有相同能力”是“民主理论的滥用”。
因此,虽然新批评派明白假定一个理想读者是客观主义批评的前提,他们的形式主义使他们始终无法弄懂这里的关键所在。韦莱克后来提出一种理论来摆脱这困难,他说:“以思想状态来解释诗的规范特征必然失败,因为诗可以被正确地理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阿伦·退特和马克·肖勒等人一直到四十年代末还在攻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理论。应当指出,也可以被不正确地理解。”然而,虽然“对《伊利亚特》古今读者理解不一,却存在着一种古今相通的实质同一性”,这是一种永存于作品中的“规范体系”。
用这种方式,新批评避开了难题,现象学的批评方法比新批评视野宽阔,为“本体论批评”找出了方法论的依据。但这种永恒不变的规范体系实际上只是新批评派的假设。
而新批评派中另一些一度“左倾”分子却走向另一极端。肯尼思·伯克是西方最早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的人之一,他搞出一套“经济心理分析”。燕卜荪的《牧歌的几种变体》也走上此路,所以被伯克引为同道,赞扬为“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作品中很难找到像此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而是“次生文学”(secondary literature)。新批评派却始终把历史/社会学派作为主要论敌之一。韦莱克认为“作者自述应当考虑,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Marxist psychoanalysis),或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m),后来蔚为大潮,五六十年代有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而许多结构主义者完全否认作者意识的独立价值,弗洛姆(Erich Fromme),七八十年代有克莉斯苔娃(Julia Kristeva),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近年有齐泽克(Slavoj Zizek),名家辈出,一是十九世纪圣佩孚和泰纳等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开创的文学外缘因素研究法。二十世纪上半期实证主义学派在美国一直是较强大的潮流;另一股潮流就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燕卜荪和伯克实为前驱。
反“感受谬见”说,作为一种权宜性的批评方法,暂时把读者问题搁起,未尝不可一试。”退特也认为“社会决定论”与“历史主义”在原则上是一回事。但在理论上,应当说,它却是站不住脚的。维姆萨特和比尔兹莱这篇文章本身就有不少犯了自己设下的戒律之处。他们这样解释韦莱克所谓的“规范体系”:“诗是情感固定下来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让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感觉到其感情的一种方式……”重点号是我加的。他们又说复杂、可靠的结构是历代伟大诗歌的标记,“今后,它也不会随着人类文化的衰落而消泯;说得保险一点,它至少不会落到一个有志探索者无法重新发掘出来的境地。”在这里,恰好就是作者经验终结之时”。新批评派有时换一个称呼:“发生谬见”(genetic fallacy),我们不得不给予断然反驳。应当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绝对规范又变成相对,阅读过程成了诗的审美价值的最后判断过程,维姆萨特和比尔兹莱自己不得不用“感受谬见”来反对“感受谬见”。
至于其他新批评派,虽然他们也同意维姆萨特的命题,但在他们的理论探索中不少人还是不得不触及阅读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兰色姆认为暗喻具有明喻所不可能有的“奇迹性”,但同样必须根据完成的艺术作品加以批评”,单单从这两种比喻的形式上实在不能解释何以这两者有这么大的区别。兰色姆承认这种“奇迹性”产生的条件是“如果我们所言当真,或相信所言”,这样他就陷入了自设“感受谬见”陷阱,而同意瑞恰慈对比喻效果的论述:“当我们用突然的、惊人的方法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最重要的东西是意识努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因为缺乏清晰陈述的中间环节,我们读解时必须放进关系,美国三十年代产生的强大“左倾”思潮使不少知识分子接近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诗歌力量的主要来源。俄国形式主义者就对作者意图研究有反感,兰色姆与艾德蒙德·威尔森(Edmund Wilson)都曾经有过论战。”兰色姆这种看法几乎是几十年后结构主义的阅读反应模式论的清晰表述!
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喀勒以燕卜荪自己的论述来说明阅读反应的作用。燕卜荪在《含混七型》第一章曾举著名汉诗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所译陶潜《时运》头两句为例: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燕卜荪说:“这两个陈述放在一起,迫使读者按阅读惯例去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这两个事实被选出来放在这里,要靠他来发现。”因此喀勒感慨地说:“《含混七型》此书从非结构主义传统出发,注意作品的内容和感情。
但我们也应当指出,三十年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批评,有相当严重的机械论的缺点。新批评派甚至认为二十世纪另一种文学理论,即神话学—人类学派,也是历史/社会派批评,因为它也是在外部社会原因中寻找作品生成根据。韦莱克曾举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和英国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分析莎士比亚所作的有些可笑的结论,他讥嘲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总想从经济到文学太粗率地走捷径。”《细察》集团的L·C·奈茨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他写的《江生时代的戏剧与社会》一书力图探索“经济活动与一般文化间的关系”,正如维姆萨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但他只是把剧中人的台词翻译成社会评论,反复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而已。
三十年代新批评派尚是羽毛未丰,是个影响不大的小学派,我们很少找到“新批评”与历史/社会批评短兵相接的例子。否定作者意图是出于为形式辩护。
(第三节) 历史/社会式批评
然而,却表现了对结构主义的关键命题‘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相当深刻的认识。”
这样,作品的“本体性”至少消失了一部分,感受谬见的“相对主义”又从新批评理论的破绽间复活,并把新批评撑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