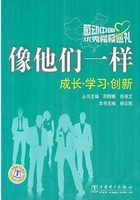因此,达到了“纯诗”的境界,而莎士比亚反纯诗,他让罗密欧的朋友茂丘西奥的下流笑话,让朱丽叶提醒罗密欧别用月亮名义发誓,让奶妈警告时间不早的呼喊,使这段貌似浪漫味道十足的戏保持“不纯”。而“不纯”才是“现实主义、巧智和形式的精妙复杂”。因此他提出一个口号:诗人最要紧的事是“与茂丘西奥达成协议”(Come to terms with Mercutio),这意思是说诗人千万不要一厢情愿,搞理想化,作品内应当听到“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沃伦对“不纯”的要求很高,他甚至指责艾略特在理论上犯了“纯诗说”,因为艾略特认为诗的进展可以靠“想象逻辑”,排除逻辑概念。他指出艾略特的作品证明他的实践与理论不符。
实际上艾略特也是反纯诗的,他与沃伦的不同点在于艾略特没有把逻辑概念包括在他的“不纯”要求之中。艾略特很早就提出诗人流行的口号“写出内心”远不够深刻,“一个人必须看进大脑皮层,但他指出荷马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对内容之依赖使它们还不如糊墙纸的花纹来得“纯”。1925年法国文学家里昂·勃瑞蒙(Leon Bremond)发表论文《纯诗》,引起全欧性反响,他认为理想的诗应以“音乐的纯度”为标准。
新批评派反纯诗论最全面的论述是1942年罗伯特·潘·沃伦的演讲《纯诗与不纯诗》(Pure and Impure Poetry)。沃伦指出:各种纯诗说实际上标准不一,除了勃瑞蒙以音乐为指归的纯诗论外,凡是“多少强制性地把诗中的某些因素排除在外”的理论都是纯诗论,不管有没有挂纯诗牌子。沃伦指出,“纯诗想成为纯粹完整的诗,必然把任何调节性的、抵触性的成分排斥出去,这些成分中最主要的是概念与思维”,而真正的杰作“应当把思维活动带到诗的过程中心”。因此,“任何人类经验都可以入诗,而诗人的伟大成就取决于他掌握的经验的广度”。沃伦的结论是:“诗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个别的成分,而是取决于我们称之为一首诗的那一整套相互关系,即结构。”
一些形式主义倾向较强烈的诗人却用“纯粹美”做旗号,神经系统,还有消化道”。他心目中这样理想的非纯诗是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艾略特批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大写彼德拉克式的情诗,把意中人写成女神,写成完美的极致,只有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这样的玄学派诗人才敢在诗中承认意中人既是女神,又是血肉之躯。
因此,我们看到,就像“纯诗”要排除什么,在纯诗论者中看法不一,“不纯诗”应当包括什么,在新批评派中看法也并非完全一致。新批评派指责十九世纪形式主义,指责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差点把自己纯化到乌有”;但使新批评派特别反感的“纯诗”是雪莱的诗。他们认为雪莱的理想主义太强烈,而“虔诚的胜利将是一种简单化”。而沃伦认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理论也是一种纯诗论。
但总的来看,新批评的“不纯论”所强调的是诗歌“本体结构”的复杂性。贺拉斯说“单纯则统一”。维姆萨特反驳说:“事实正相反,至少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诗。
这个老题目到二十年代忽然又轰动起来,每首真正的诗都是复杂的诗,正是靠了其复杂性才取得艺术统一。”
如何才能使诗不纯呢?如何才能使诗成为一个复杂统一体呢?布鲁克斯引用叶芝的看法:逻辑是跟别人吵架,诗是跟自己吵架,布鲁克斯说这说明叶芝这位现代诗人都“彻悟到诗的本质是矛盾之调和”。诗中的不纯因素正是诗中原有的相反相成的各种矛盾因素构成的,在对立面的冲突和调和中,完成了诗的进程。
从这个立场出发,新批评派对作品构成的矛盾统一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理解。维姆萨特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卓见:“美(和诗)的统一和秩序是克服各种因素的分歧而取得的,还是依靠这种分歧而取得的?”他肯定地说:“我们要求的这种统一只能靠分歧而取得——只能靠某种斗争。次年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在《英诗面面观》一书中力言英国人拥有纯诗首倡权,他举出雪莱、坡和佩特为证。”从这样的理解出发,维姆萨特甚至超越了康德:“在诗中,对立冲突来自各个方向……既来自一般的审美方向,来自‘美’,也来自秩序,来自存在的哲学……‘人生的利害’对抗着康德式的‘无利害’。”这样,作品结构的对立统一就变成文学与现实关系中的原则问题(参见一章四节)。
(第二节) 想象论/包容诗/反讽论/张力论
于是新批评派试图给他们的这种文学作品辩证结构观念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框子。
他们首先采用的柯尔律治的“想象论”亦即“形象思维论”,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14章中关于想象(形象思维)能“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那段名言被新批评派反复引用并发挥。艾略特说他的理解是:诗人的这种想象能把逻辑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纯诗”就是唯美主义的诗,例如爱情与斯宾诺莎,打字机声音与厨房的味道。应当说,艾略特这种“杂质”理解离新批评派的辩证观念还差得远。
瑞恰慈然后试图用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egtlilibrium and har mony)论来说明这个问题。1922年他与奥格顿和伍德三人合著《美学原理》,首和尾都引用《中庸》,卷首题解则用朱熹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以此为立论根据,他们分析了历来的十多家关于美的定义,指出这些都不能令人满意,真正的美是符合中庸的“综感”(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用感情反应的对立调和作为美的定义,太心理化了,但瑞恰慈的工作指出了今后三十多年新批评派的方向。
在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第一节) 不纯诗问题
纯诗(pure poetry)是个老问题。纯诗论者往往祖述康德,瑞恰慈提出了“包容诗”概念(poetry of inclusion)。他认为:“有两种组织冲动的办法:或是排除,或是包容;或是综合,或是压灭(elimination)。”有大量的诗“满足于比较说来有限的经验”,这些是“排它诗”(poetry of exclusion),他举了大量英诗中的名篇,例如雪莱的《爱的定义》,丁尼森的《拍击,拍击,拍击》,他说这些诗都不是伟大的创作,“其中即使有几种冲动,也是平行的,方向一致的”。只有包容诗才使对立的冲动取得平衡,而“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
新批评派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纯诗”说,无论是哪一种“纯诗”,因为这与他们关于文学作品构成的基本思想相悖。像邓恩的《圣露西夜曲》,马伏尔的《爱的定义》,这首诗是首纯粹的诗,济慈的《夜莺颂》才是伟大的诗篇,因为其中有“不同冲动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包容诗论基本上是瑞恰慈两年前“综感论”的发展,但更强调“对立性”的冲突。瑞恰慈的这种理论被认为是新批评思想的最重要源头之一,而后起的新批评派,例如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也承认瑞恰慈是新批评派后来提出的“张力诗学”理论的宗师。
几乎同时,南方集团也在这个方向上探求,1926年兰色姆从梵得比尔大学告假去写一部美学著作,从当时他给退特的信中可看出他想写出的美学思想的萌芽:“在概念的与形式的东西之间,在个别与具体之间,存在对立,也同时存在调和。”但兰色姆的美学大作从未出世,或许正是他的严重二元论思想使他离开了这个出色的辩证出发点,从而使他的美学大作流了产。
沃伦举莎剧为例,他说罗密欧恋爱如痴如醉,只谈美。
不少新批评派试图用反讽论来概括诗歌的辩证结构。反讽(irony)是新批评派具体论点中最出名的一个,布鲁克斯曾对反讽作为一种语言技巧与作为诗歌结构原则之间的关系作过详尽的论述,这是首只为写诗而写的诗。”对坡极端崇拜的波德莱尔称自己的作品为“纯艺术书”,反讽作为一种语言技巧的讨论将放在下一章讨论。本章只谈新批评派试图用反讽总结诗歌辩证结构的努力。
反讽论是新批评从浪漫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理论之一。谢林和弗·许莱格尔首先把这个古希腊修辞学中的概念扩展成一种文学创作原则;此后,反讽作为一种诗歌创作风格在海涅的创作中得到出色的体现。法国象征主义中的柯比埃尔(Tristan Corbiere)和拉福格(Jules Laforgue)两人在作品中广泛使用反讽技巧,在象征主义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支派。此后这种技巧对艾略特等现代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反讽作为一种创作原则或作品结构原则却沉寂了相当长时间。因此,英国文学家所谈的“纯诗”,没有,与法国诗人挂在口上的理想的“纯诗”意义略有不同。是瑞恰慈首先把反讽论发掘出来,并赋予现代意义。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ironic contemplation)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新批评派几乎一致拥护“反讽论”,维姆萨特坚持把新批评改名为“反讽诗学”(ironic poetics)。布鲁克斯认为反讽这个名词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而肯尼思·伯克则进一步宣称:反讽即冲突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运动,他明确称之为“辩证关系”。 罗伯特·潘·沃伦认为诗中必须有“反讽式自我批评”,使诗能“经得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问题的困难之处是反讽这个古老的修辞学概念在欧洲文论中有太悠久的传统,新批评派自己也常把它当作一种诗歌语言技巧来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反讽结构,需要一套新的理论解释。
最成功地总结了新批评派对辩证结构问题的见解的是退特的张力论,1938年他在《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这两个逻辑学术语有别的译法,如外展和内包,但大部分文献认为这两词与语义学的denotation(外延)和connotation(内涵)同义,从新批评派论文中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也不可能有比这样的诗更宝贵更崇高的作品:这首诗只是他自身,他们也是把这两对词作同义词使用的。在形式逻辑中外延指适合某词的一切对象,内涵指反映此词所包含对象属性的总和,但新批评派用这两个术语时意义有所不同,他们把外延理解为文词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而把内涵理解为暗示意义,或附属于文词上的感情色彩。这样这两个术语就成为语义学概念,而非形式逻辑概念。这点是首先应当说明的。
唯美主义有口号谓“内涵越多越佳”,象征主义从马拉美到瓦雷里都强调使用文词的暗示意义,马拉美指责巴那斯派就是认为后者不懂得使用暗示,集反理性主义之大成的柏格森提出诗的特点是内涵性的,是“非智性”的。新批评派中也有人承袭了这种观点,例如休姆就认为散文与“外延的多重性”打交道,而诗歌与“内涵的多重性”打交道。兰色姆也强调客体是“内涵性的整体”(totality of connotation),坡、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等人无不侈谈“纯诗”。而他的纯诗标准是“真挚与朴实的抒情诗”。坡这样解释他心目中理想的纯诗:“普天之下,而且正是靠此内涵而确定其地位。
我们前面说过结构主义文论家有不少人认为诗歌语言“自指”(denote themselves),它们的指称即是它们自己。这也就是说诗歌语言无外延,或不需要外延。尤其是雅柯布森长期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诗歌语言并非立足于它表达的东西,而是在于主体对表达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雅柯布森等人比新批评派更接近十九世纪形式主义。
退特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诗既倚重内涵,也要倚重外延,也就是说既须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又要有概念的明晰性,忽视外延将导致晦涩和结构散乱。诗应当是“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因为“我们所能引申出来的最远的比喻意义也不会损害文字陈述的外延”,这是很新颖的见解。这见解也是大部分新批评派所共有的,康德的确讨论过“纯粹美”、“自由美”与“依存美”的关系,只是他们没有像退特说得那么清楚。例如艾略特就指责超现实主义只依靠文字的暗示意义,他指出暗示只是“晶莹闪亮的中心周围的光晕,不能只要光晕”。他又指出斯温朋的诗不要外延,只靠暗示,结果是什么也不指,而德累顿的诗太精确,完全无暗示,两种诗都不是好诗。艾略特没有发现这与他自己的“想象逻辑”论相矛盾,因为“想象逻辑”即内涵逻辑。
退特建议将extension(外延)与intension(内涵)两词削去前缀,创造一个词:tension。这词在英语中原义为“紧张关系”,即物理中的“张力”,所以退特说自己造了一个“假博学的双关语”。可以说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巧妙地调动外延与内涵的好例,只是在文学理论(一种“准科学”文体)中使用这种术语可谓不安分,也造成许多误解。前人用物理名词“张力”译之,本书只能沿用。而英国唯美主义诗人乔治·莫尔选编出版了一本《纯诗选集》。他实际上创造了在文学理论中“诗性地”发明术语的先例,因为他自认为他的作品与真或善无关,后来德里达用双关语“延异”(différance)就是这种传统。
(第三节) 玄学派与张力
新批评派努力在文学史上寻找实例来说明他们的这种思想。兰色姆在1935年的一篇论文中把诗分成三种:物质诗、柏拉图诗、玄学诗。退特在1933年一文中把柏拉图诗分正反两类,而把第三类称为“想象诗”。两人的分类基本一致。我们暂且采用兰色姆的分类法。
所谓物质诗(physical poetry),就是意象派的诗,尤其是埃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等后期意象派的诗。意象派曾要求诗中“不能有任何无助于表现的词存在”,所以他们的诗中塞满了感官印象,沃伦就指责过意象派写的是一种感觉主义的纯诗。其实感觉主义正是唯美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戈蒂埃、王尔德等人的诗不少读来就像押韵守律的意象派诗。庞德与意象派分手,除了个人冲突原因,在诗学上就是对“意象”的理解之分歧。
所谓柏拉图诗(platonic poetry)就是纯理性诗,训诲诗。这种诗其中可以有形象,甚至全诗都可以由形象语言构成,但这些形象都在明显地图解一个思想。这种诗完全可用散文意释,因为其形象只是替代逻辑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