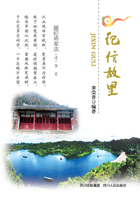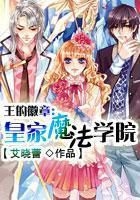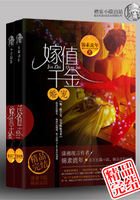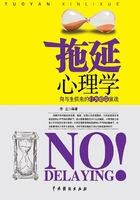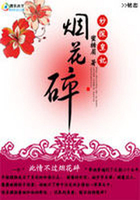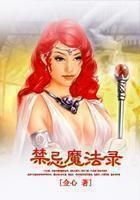群相制有集思广义的优点,但易造成遇事推诿,无人承担责任。唐代武则天时的宰相苏味道曾两次拜相。虽然他对朝中旧事了如指掌,但却无治国才能,并且从不得罪人。他曾对臣僚说,处事不必决断明白。倘若出现差错,就要遭到谴责,甚至获罪,那就很麻烦。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因此,时人就称之为“模棱宰相”。
五 二府制
“二府”是宋元时期的辅政体制。“二府”指“中书门下”(或称政事堂,简称中书)和“枢密院”(简称枢府)。《文献通考》载:“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二府”的长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共同执掌相权。“二府制”执掌相权发端于唐朝。
唐代设立政事堂,“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政事堂最初设在门下省。高宗永淳二年(683)七月,中书令裴炎秉政,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到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正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玺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从此,“中书门下”成为相权中心,宰相改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门下设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中书门下”不仅继续具有原来政事堂决策的功能和权力,而且由于五房办事机构的设立,“中书门下”还具有了行政权力。因此,政事堂改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成为最高的决策兼行政机关。这就发展形成了中书门下一省权力独重的局面。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决策与行政分离的三省制名存实亡了。在宋代,中书门下进一步发展,而三省逐渐变为闲散机构,其长官多授元老。
枢密院总理全国军务,是国家的最高军政机构。其长官称作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是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它是随使职差遣体系的出现而出现的。
枢密院分掌相权亦始于唐朝。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创设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可以说,这只是皇帝的侍从官,在君相之间起一个上传下达的媒介作用。后来大宦官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开始了相权向枢密的分割、转移。朱温诛灭宦官,更唐制,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心腹谋臣敬翔为崇政使,并选用士人。后唐以续绍李唐正统自居,恢复原名为枢密院,但沿用后梁“参用士人,而与宰相权任钧矣,故与宰相并书”。事实上,五代动乱之秋,君主多用心腹为枢密使,以致枢密院事权重于中书门下。如后唐之郭崇韬、安重诲,后晋之桑维翰,后汉之郭威,后周之王朴,均以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之职施行宰相职权,总揽朝政,而“当时宰相行文书而已”。“政事皆归枢密院”。“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专条,详述枢密院权重之例,反映出五代之枢密院不仅侵夺相权,甚至侵夺君权,所谓“枢密之权,等于人主”。
宋太祖代周,信用心腹谋臣赵普,“二府”权力轻重随赵普而变。赵普初为枢密使,“军国大计悉出于普”。赵氏旋为宰相,太祖视其“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宋太宗亦称:“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可见,此时“二府制”尚未定型。太祖开宝五年(972),赵普同枢密使李崇矩结为姻家。这触动了猜疑心重的宋太祖,乃下令中书、枢密分别奏事。这是二府对掌大政形成的关键一步。从此,“每朝奏事,(枢密)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
“二府”对掌大政的相权体制定型于宋太宗时期。太宗以早年知开封府时的幕僚担任枢密院要职,枢密院权力逐渐扩大,与中书的事权划分亦逐渐明确。雍熙三年(986),太宗企图收复燕云之地,倾力北伐。时宰相李昉为先帝旧臣,而枢密院长贰王显、张齐贤、王沔是太宗的心腹谋臣或太宗朝新科进士。“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中书不预闻。”事关军国大计,虽中书之首相亦不得而知。不少朝臣对太宗摈宰相于军国大计之外极为不满,纷纭奏陈,但太宗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二府”体制。相反,淳化元年(990)十二月,太宗因左正言直史馆谢泌的奏请,将“二府”体制确定下来:“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李太宗以诏令形式确定“两府”分掌相权为宋朝永制。《宋史》载: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其权力是“佐天子执兵政”,“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如“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仁宗以来,有中书宰相兼枢密使参决军旅机务,但没有从“二府”体制进行改革。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着力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依据《唐六典》,有损益地恢复三省六部制,相名与相权都有变化。宰相不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三省长官为相,又不设正长官(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而以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仆射为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实权主要掌握在右相手中。执政由四人组成,门下、中书二省各设侍郎一人,管理本省省务。尚书省由左、右丞管理省务。这四人称执政,行参知政事之权。当时有人提出废罢枢密院,权归兵部。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制维,何可废也。”唯将部分职权,“随事分隶六曹,专以本兵为职,而国信、民兵、牧马总领,仍旧隶焉”。正副长官仍为执政,改称知院事和同知院事。
南宋初期,因为军事斗争的特殊需要,突破了“二府”的相权体制。宰相初兼御营使,取缔御营使后又兼枢密使,合兵民之政于中书,相权开始膨胀。秦桧以宰相兼枢密使,专制朝政十七年。秦桧死后,宋高宗特颁诏令:“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领。”其后宰相是否兼领枢密使,全视军事形势而定,所谓“兵兴则兼,兵罢则免”。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南宋大举北伐,为适应战时需要,彻底突破了“二府”体制,“以军相兼枢密使为永制”,先后出现了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专制朝政。枢密院机构虽然始终存在,但已失与中书对掌相权之实。
六 一省制
元朝的中央最高国务机构就是中书省。中书省亦是元代正式的宰相机构。蒙古帝国时代就设有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任中书令,镇海、粘合重山为左右丞相,但此时中书省侍从和秘书性质很浓。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重建的中书省方能堪称相权机构。忽必烈创制之始就赋予中书省“总政务”的大权。《元史·王文统传》载:世祖“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官之政”,曾诏谕中书省,“大事奏闻,小事便宜行之”。后嗣之君沿袭此制,坚持以中书为国家权力中心。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武宗下诏规定:“设官分职,各有攸司。中书省辅弼朕躬,总理庶政。中外越分奏事者,即位之初,已常戒饬。今后近侍人员,内外大小衙门,钦依已降圣旨,除所掌事外,凡选注、钱粮、刑名、造作、军站、民匠、户口一切公事,并经中书省可否施行,毋得隔越奏事,违者究治。”这就明确了中书“总理庶政”的地位,肯定中书对“一切公事”有“可否施行”之权,禁止“隔越奏事”的侵权行为。可见,元朝的中书省囊括了唐代三省制时中书省出纳诏令之权与尚书省“总裁庶务”之权。中书内统六部,外临行省,所以《元史》中“中书政本”、“纲维百司”、“总裁庶政”、“百司之首”等提法屡见不鲜。
元朝实行“群相制”。中书省从中书令到宰执没有固定编额,少则数人,多则十数人,甚至数十人,如世祖时曾多至十七人,成宗即位时达二十一人,顺帝末年竟至三四十人。成宗大德七年(1303)定为八员,名号杂用前代官名(丞相、丞)和差遣名(平章、参政),置左右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二人,左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共计八人,史称“八府”。这是元代比较稳定的编制。“八府”之外有参议中书省事四员,相当于中书省的秘书长,“典左右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又有元老重臣或皇帝亲信加上“录军国重事”或“商议中书省事”头衔,参决中书大事。如此多人分掌相权,虽能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但必然导致相权分散和政治纷争。议政常有不同意见出现,这时就要由首相(通常为右丞相)负责定议。元宰相人数虽多,但相权并不平均分配,而是相对集中在丞相(尤其是首相)身上。
元朝宰辅制带有民族歧视。元朝无常朝之制,臣下与皇帝接触也较少。“百官入见,岁不过宴贺一二日,非大臣近侍鲜得望清光者”。即使是宰执,往往也是“奏事多则三人,少则一人,其余同僚皆不得预。有一人得旨而出,众人懵然不知者。有众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闻者”。能够入宫奏事的通常是几名出身于怯薛(即所谓“近侍”)的宰相,汉族宰执(他们一般只能担任左右丞、参政之职)多在被排斥之列。如何荣祖任参政时,“条中外百官规程,欲矫时弊”,右丞相桑哥却“抑为不通”。元末右丞相脱脱奏事时,因为“事关兵机”,即命汉族出身的左丞韩元善、参政韩镛“退避,勿与俱”。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据《元史·百官志》载,行省事权颇重,“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与都省建制基本相同,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品秩比都省低一等,而左右丞、参知政事则与都省全同。行省与都省为同级机构,往返文书俱用“咨”,以示平级。真正与都省平行的机构御史台、枢密院对都省却用“呈”以别上下。早在世祖时已有行省同都省抗衡。至元二十年(1283),有臣僚建议,行省不置丞相和平章,只设左右丞,以免内外均势。但有人以“非隆其名,不足镇压”为由,反对改变行省体制。元朝先后置行省十一个。十一个行省的长贰权位同中书“八府”。
唐宋元宰辅体制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翰林学士分割相权。中书省从魏文帝创建以来,“出纳诏令”是其稳固的职权。隋唐之中书省仍“掌军国之政令”。其中书舍人更是以起草诏制为专职。唐初“学士”开始侵夺宰相的草诏权。“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武则天用事时,召刘懿之等以本官待诏北门,专司草拟诏制,且“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翰林学士之称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为“代草王言”的学士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成为正式称谓,以草拟内制为职。唐朝皇帝制书有内外之别,内制(白麻)用于机密要务,外制(黄麻)用于平常事务。其分工是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到德宗之时,翰林学士陆贽当“泾原兵变”决策机务、代草制诏,遂有“内相”之称,其侵夺相权更加突出。宋代翰林学士之荣宠和权力都超出了唐朝。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明朝之内阁,清朝之军机处,与秦、汉、唐、宋宰相府相比,无论其机构、名号、职权、地位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内阁与军机处不失为辅政体制,一并论列于后。
七 内阁制
明朝初年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以中书省“总揽政事”,设置丞相执掌相权。开国功臣李善长、徐达出任首届左右丞相。当时中书长贰人员精少,丞相之权重于元朝。中书省内统六部,外辖行省。百官奏事,先中书而后闻,皇帝制诏必经中书而后下。于是,君权与相权矛盾加剧。朱元璋认为,“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允许天下臣民言事“得实封直达御前”,“勿关白中书省”,合并相权入君权的意图十分明显。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罪诛左丞相胡惟庸,正式废除中书省,在古代中国运行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朱元璋还留下了永不设相的祖训:“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丞相制度的废除使国家政治陷入混乱,也使明太祖自己陷入繁杂的政务之中。据吴晗先生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里,内外诸司奏章达1660份,涉事3391件。三千多件事皆由皇帝裁决,自然无法一一亲批,只得采取传旨处分,或者朝堂论定,各司奉旨意自行批写,执本回府施行。朱元璋也感到“人主不能独治”,必须招用贤才,分理“共治”。于是,他在不设丞相的大原则下进行试验:第一次是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创设四辅官,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号,选简老儒充任,职责是论道经邦,协赞政事。虽然为一品高官,但没有任何实权,加上老儒“淳朴无他长”,缺乏从政实际才能,到次年八月“遂废不复设”。第二次是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设立殿阁大学士。明太祖仿宋朝之制,“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秩皆五品”,但没有赋予实权,殿阁大学士“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于机务无与也”。史称,明太祖“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而且自洪武十八年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致仕后不再复设。但这给后世子孙以启示,内阁制自此发端。
内阁辅政体制形成于永乐时期。成祖夺位,拔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七学士多餐宿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此时之内阁学士与洪武不同,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礼赐赉与尚书等”,而且在东角门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可见,这时的内阁有参决机务之权。然而从相权的两大组成部分看,内阁所拥有的相权是不完全,缺少总率百僚之权。当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成祖对六部和内阁有过明确分工,即“六卿理政务,翰林职论思”。也就是说,这时的内阁侍从顾问性质很强,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当时的内阁同唐宋翰林学士院类同,故而多称“代言之司”。
明仁、宣以来,内阁权力增大,突出表现在内阁获得了“票拟”权。所谓“票拟”,就是内阁大学士在收到内外百官的奏章后,用小票代皇帝写上自己所拟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朱笔批出。内阁的拟旨叫做“秉笔”,出于首辅之手。无首辅时,可由次辅秉笔。从明熹宗天启(1621-1627)以后,拟旨则由阁臣分任。“票拟权”实际上是拟旨权。但皇帝对内阁票拟的意见有最后的取舍权,认为不合意时可以另行批答,还可以扣下不发,谓之“留中”,还可以不经票拟而传旨,谓之“中旨”。正统以后的明朝皇帝经常不由票拟左右,采取留中和中旨的做法,直接发布诏令。明朝重用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红”。皇帝以司礼监批红牵制内阁,而司礼监则借批红干预朝政。因而阁臣的票拟之权逐渐内移于宦官,甚至有时根本不由内阁。
八 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