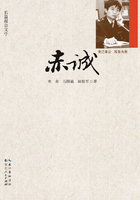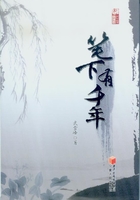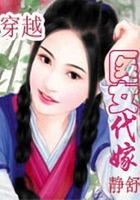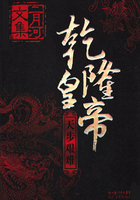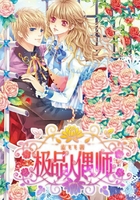1.文学的困境和梦想
关仁山
2007年8月,应深圳作家李兰妮大姐的邀请,到深圳市民大讲堂讲了一课。兰妮大姐给我定了个题目是“文学创作与人生立志”,我是作家,人生立志离不开文学,讲文学就离不开文学的现状。我真的不敢说是讲课,只是与大家共同探讨文学的话题,从而拉近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首先探讨的是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我感觉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到,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还有人说,专门发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刊物订数越来越萎缩,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刊物了。过去《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选一个“头题”就火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小说,可能在圈子里影响很大,可是在一般读者那里却失去了信誉。有的小说在市场上看好,可是圈子里并不买账。其实,这也是文学衰落的一种表象,这也就是虚构与想象的衰落。
在艺术形式里面,能看的东西观众最多。比如电视剧、电影、电脑网络、舞台话剧,等等;能听的东西就相对较少了,比如音乐、收音机、小说连播,等等;能读的东西就更少了,比如图书的阅读,等等,通俗读物还好一些,如果高雅的,能够思和想的东西,读者就少之又少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越发深刻的时候,小说已经走失了。我们说小说技术、小说元素、小说语言做得好不好时,殊不知怎么研究都不能感动读者,读者已经找到了新的狂欢载体。小说像京剧似的处在尴尬的悲剧中,却不忍自身的消隐。市场经济对传统阅读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破坏着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文化垃圾泛滥,进而抑制了优秀文学的创作和生存空间。其实呢,无论我们怎么渲染衰落,小说是不会消亡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时去听去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他们最要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文学的衰落,大环境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追问作家自身的问题。当代小说越写越轻飘,越写越粗糙,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躲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对叙事和细节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的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小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为大众写作。为哪些大众呢?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摆脱对历史的虚无和狭隘的功利原则,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小说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们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实。
传统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引领,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文学实现了传统往现代的转型,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私人化”等,文学的“个人发现”,成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载体,肯定世俗化的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摈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它顺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发展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更文学化、更艺术化、自由开放的姿态,产生了一批好作品。这是大进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雷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小日子。文学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文学回归了个人的独语,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一些要素,拒绝社会深度和宏大叙事,淡化了文学的使命、良知,疏离了民众和底层社会。把这一切都剥离之后,还剩下了什么?食与性?难怪有个编辑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人物环境多是酒吧、豪华别墅。读者厌倦了这样的模式。
一位评论家说,不要忘记,文学终究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作用,作为社会人很难绝对地逃离,绝对地逃离就一定会削弱文学的力度和感染力。
实际上,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来创作,向内也应向外。我们应该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灵质量,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也应该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而这就迫切需要重新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小说的基本元素,进行艰苦的自我磨炼,自我塑造,而去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功力。
我想,作家与读者的沟通还是靠作品。我生命的根基在乡村。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知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中国是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况味儿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我茫然。几年前,我为什么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这得益于老作家管桦老师的启发。1990年秋天,管桦老师到老家探访,我们的县委书记将我介绍给管桦老师。管桦老师听说我已发表了两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就叹了口气。他劝我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有艺术品位的作品。我听后为之一震,心想是该换副形象了。当时我27岁,做新人走新路绝对来得及。不久,我便认识了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柯杨。鲍柯杨在中国文联工作,读过好多书,也写小说。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著作。我读了,也就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言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我县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写完之后心里痛快,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0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呢?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序,每前进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作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干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进城热等,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在土地流转中求发展求生存,问题出现了,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忍,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好品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变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们应该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淳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土地结冻。我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事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地,也看到了冻土。那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进城打工人员。他们在9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着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那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了。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竟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他们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样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了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了江苏的华西村,看到经济发达的乡村。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我去过印度的乡村,也看到过台湾的乡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坐在身边的陆天明老兄问我,看到窗外美丽的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而且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沃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大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饱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隐入,还要头脑清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成长的过程。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是拥有梦想的人,是最快乐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乡村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2.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
梁晓声
仁山:
你好!
我用一天半的时间读完了你的《白纸门》。我首先向你祝贺!我认为你写了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同时也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