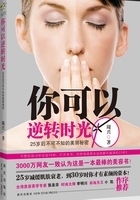方方,现在轮到你坐在窗前当静物了。你的周围,聚了一些手持画板的人,他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从各自的角度要仔细审视你,准备勾勒你了。这时你是气定神闲还是脸热心跳?这些人中,有的是绘画高手,他们深谙你的气质和秉性,因而画起来肯定得心应手。而我,只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初次拿起画笔的学生,若是把你画歪了,或者因为要认真打量你而走到你面前,意外淋到你脸上几滴油彩,你权且把它们当作幸福的鸟粪,千万不要恼。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1985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卷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她的消息,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1995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女作家们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有很多人因为有种种事情难以脱身,纷纷走了。最后到了五台山,只剩下叶文玲老师、方方和我了。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宿舍压死过一只老鼠。那间宿舍也常有老鼠跑过,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10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11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洪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价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却已然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儿,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便满脸幸福。我也很喜欢毛妹,她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却常出“惊人之语”。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情,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里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方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4.追寻认识方方的踪迹
何镇邦
第一次读方方的作品,记得是将近二十年前读她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大篷车”上》,那种泼辣的文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打那以后,在我的脑子中,就有一个从珞珈山下走出,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女作家方方的位置。真正为方方的作品所打动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读到她的作为新写实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风景》,这篇以现代主义某些技巧包装起来而其灵魂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汉口码头旁棚户区工人生活的作品,是篇典型的新写实的作品,我多次在文章中和讲课中提到它。而同样作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池莉,也是生活在武汉的一位女作家。我们通常把方方、池莉并列为武汉两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女作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1986年夏天张家界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池莉,从此比较关注她的作品,并为她的《烦恼人生》写过评论。而对于方方,却始终没有拜识她的机缘,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同时又同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的一些朋友共同筹办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因而经常到武汉去,却也没有机会见到方方。
为方方的作品深深打动而自觉写评论是在1990年春夏之间。那时,我从《上海文学》上读到她的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写的是她的祖父、伯祖父以及父亲的人生经历,其中更多的笔墨是写她父亲的,一位决心把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奉献给新中国而由于种种原因壮志未酬的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依我看,此篇的题目应易为《父亲在我心中》。使我感到惊喜和震动的是,我们不仅从小说中发现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方方,看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方方有别于《“大篷车”上》和《风景》的另一副笔墨,儒雅、从容、充满书卷气的笔墨,让我刮目相看。读了小说,趁着那股热劲我写了篇读后感式的评论,因为当时在江西的首届滕王阁笔会上正认识了一位《武汉晚报》副刊的编辑,于是把文章给了他,不久就发了出来,后来又收入我的一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文学的潮汐》。此文题为《且看方方的另一副笔墨——读方方的中篇新作〈祖父在父亲心中〉》。这可以说是我同方方在笔墨上的唯一的一次交往。我原以为方方会读到这篇短文,因为它就发表在方方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的一家晚报上。没有想到,方方却一直没有读到它,直到最近向她组这一辑有关她的“名家侧影”的稿子同她通电话的交谈中,才得知此事。我感到意外。除了答应她把文章复印件寄给她参阅外,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方方。她是有别于当下不少很注意自己的影响位置和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评论,不大注意创作之外的事,淡泊于功利的不随俗的作家。唯其如此,才让人更加喜欢她的作品和人品。像这样的事后来还发生了一些。诸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公安部宣传局每年举办一次“金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我和著名作家李国文、从维熙均应邀担任历届的评委。第一届评奖时,我力图把方方写警察“蹲守”的中篇小说《埋伏》补上,终因作者不是公安战线作家和作品发在地方刊物上(此作发在浙江作协主办的《江南》杂志上)而未果。后来,当我把这个事情和我遗憾的心情告诉方方时,她竟无动于衷,也使我很感意外,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方方。
第一次见到方方,也是在1990年。那年的深秋季节,我与方方、池莉同时应邀参加海峡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海峡笔会。到福州报到后,先游武夷山,又经南平南下厦门,再经石狮、泉州折回福州,历时十余天。时间虽说不短,但真正深入的交谈却不多。唯有登武夷山的天游峰至半山腰时,我与她及池莉的合照至今仍珍藏着。站在半山的台阶上,一边是方方,一边是池莉,感觉自然不错。当然,游罢水篇洞后一起沿鹰哨岩下小径走到慧苑特品茶买茶的经历也很有趣。这是我同方方交往的开始。
而有机会同方方进行比较深入交谈的是1996年夏天在庐山举办的百花洲笔会,我和方方均应邀与会。方方的好友我的学生迟子建也应邀与会,方方还带上了她天真活泼的女儿毛妹。我们在避暑胜地确实度过了难忘的愉快的一周。除了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和一起纵论文坛流变、切磋创作技艺之外,更多的是各种自由组合的无主题的海阔天空的聊天。那时候,迟子建诉沈阳出版社擅自篡改她的长篇小说封面,以低俗的封面损害她的人格的一场官司正到了关键时刻,因此聊天时,这场官司常成了聊天的话题。
每到此时,方方便慷慨激昂地发表见解,表现出一种侠义衷肠。笔会临近结束时,方方的女儿毛妹偶感风寒生起病来,把方方急得团团转,自此很少见方方的身影,她又把全部精力用在呵护爱女之上了。由此又可以看到一位母亲相当细腻的感情。正直侠义,还有作为女性的细腻温和,这大概也正是方方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
自从1996年夏日同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庐山举办的笔会之后,我同方方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说多也是相对以前而言,而且这种交流大多通过长途电话。不仅在电话里聊天问候,且有所托付。诸如她主持的《今日名流》杂志要在武昌一个商场的一隅办书店,托我同群众出版社打招呼,让该社出的书直接供他们出售。我也曾打电话托她查她的好友蒋子丹的电话等。直至不久前向她组“名家侧影”的稿件,闲聊中提到她曾发在《钟山》上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告诉她毕淑敏读后大加称赞并向我推荐过,没想到她却告诉我先不要急着读,她是边写边发的,杂志上先发的部分次序有些混乱,她劝我耐心等待,等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读不迟。方方的这种态度又一次让我感到诧异。照说,一部作品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别人想读想评,作家应该是很高兴的,巴不得人家快点读快点评,何况我二十年来还是个长篇小说的专业读者呢!而方方却劝我慢点读。这种态度着实让我感到意外,但回头一想,这才是真正的方方,也正是方方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