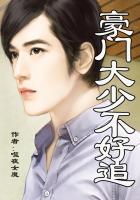1.我对世界所知甚少
刘震云
不仅仅是年龄关系。我还没有达到对自己发生强烈怀疑的阶段和境界——怀疑的指向往往还是外在世界。但我分明看到自己的过去和作品变得陌生了——像困兽一样躲在阴凉的角落瑟瑟发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相互的爱怜和同情油然产生。我们相互抚摩着知道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这个世界、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凌驾于内心之上的情绪的翻腾和游走及白天和夜晚的区别,以及你怎么控制你的梦特别是白日梦,当然还有永远不可触摸的万物生灵相对你的情感流淌方式。当我们想起我们曾经蜷缩在对世界的误会的自己的投影里沾沾自喜时,我们除了无地自容更想做的是失声大号。你比以前脆弱多了。想起温暖的朋友和往事,还有那些冰凉的现实,当你们想聚首一隅相互诉说时,也往往是一语未终,潸然泪下。甚至你对往事的真实过程发生了怀疑。你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你对许多简单的话语想作幽远和深情的注释。你周围的世界和情感像风雨中的泥片颓倒一样在飞速地解体和掉落——你试图挽留它们或是在梦中抓住它滑溜的尾巴但梦醒时分你发现留在原地的只有你自己——虽然你留下一把岁月的青丝那确是一把好头发。虽然你的亲人每天都在说汉语,但你对汉语像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所知甚少。你有些口讷和犹豫,你不知道将自己的脚步放在灶台的什么位置合适——所有的人和语言在你面前都变得陌生。你掉到荆棘棵子里浑身挣扎不动的时候你只好浑身是汗地挣扎着醒来,大梦初醒的时候往往太阳正当头,别人告诉你这就是正午。
我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幻想不久的将来我能成为专业作家,用写作挣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人在现实光彩的开始。
2.一朵乌云
迟子建
刘震云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师兄。那所学院位于京郊十里堡,只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楼。校园只有几棵孱弱的杨树和一片还算茂盛的藤萝架,常见震云和做律师的太太抱着美丽的女儿妞妞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徘徊。刘震云家所住的《农民日报》社离鲁迅文学院很近,他家没有花园,便把校园当成自家花园来闲逛。
刘震云来校园闲逛时多半是黄昏时分。白天在教室里却不常见他,他在《农民日报》社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只要他来教室,通常是提着一个大水杯,下课休息时就去同学的宿舍续水,有时也顺便蹭一支同学的烟来抽。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劳作了一天从田里归来。他的一口纯正的河南腔还带着那块土地的麦场被夕阳灼过的气息。常听他谈起外祖母,他对她非常敬佩和热爱。记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从河南老家奔丧回来,他在电话中很伤感地说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姥姥去世了。”那一瞬间他委屈得像个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领着他出去拾麦子,不负责任地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给抛到野地上了。
毕业之后见刘震云的机会便少了。倒是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还很恶心地在《甲方乙方》中过了一把电影瘾,饰演了一位失恋者。刘震云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来概括: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刘震云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但这一次却是把戏做过了头。当我这么说他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地辩白:“葛优说我没准能拿个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呢。”我想这是刘震云接受批评的一种表达方式。
刘震云苦心经营了八年的鸿篇巨制《故乡面和花朵》终于杀青了,我还没有看到这部长篇的全貌。他的毅力和才情令人叹服。我和毕淑敏有一次聊起刘震云,毕淑敏说:“刘震云可真了不起,能够写一部这么长的小说。”我想只有年富力强的男作家才会有这种魄力接受这种自我挑战。漫长的写作对作家身心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带给作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艺术感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刘震云是个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极易接触,所以他人缘不错。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淳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而这也仅仅是一种直觉。何镇邦老师勒令我写他时,我以为对他很了解,可一落笔才知道刘震云对我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要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他,恐怕只有王朔才会胜任。
记得有一年一帮朋友去黄山参加笔会,途经太平湖时,那些会游泳的人纷纷跃入水中。我们这些旱鸭子坐在湖边看绿水中的人姿态万千地浮游,大多数的人都把身子浸在水里潜游,只有一个人是一直漂在水面上的,就像一具浮尸。大家惊异地指点着那个人时,他渐渐地由湖中心向岸边游来,我们看到这个泳姿怪诞的人就是刘震云。坐在岸边的人就拼命起哄,让他不能上岸,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又朝湖中心游去,依然用他那自由而又有些骇人的泳姿,一个朋友骂他:“装死!”
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散落倾盆大雨。没有雨意的云彩只是晴朗的一种点缀,而乌云却能在天地间制造一种独有的气势和声音。
3.刘震云在单位里
沙丘
刘震云的《单位》写得好,而他自己在单位里又怎样呢?
超脱的“官人”
震云当官是1991年春天的事。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农民日报》社工作,担任编辑、记者。这一年报社领导更换,机构调整,让他来副刊部当部主任。他轻而易举地当了官,并不像他的小说《单位》《官场》《官人》中主人公们那样煞费心机。
在这之前,他不曾尝过当官的滋味儿。读书时连小组长也没当过,只在部队做过一段时间副班长。这回一下子从普通记者蹦到处级,他没想到这样顺。
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青年作家”,看不起他。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俗务”上花费工夫,有点得不偿失。
震云仍把主要精力用在写作上,但绝对乐于参与报社的重大报道,也愿意和“弟兄们”一起“热闹”,所以他不仅接受行政职务,最近还领了党支部书记的衔。
为什么要取得某些方面的成功,就必须抛弃另一些东西呢?人一生应当有的都应当有,这是强者的态度。作为作家的他把一切生活内容都当成体验,当然也不放弃当官的体验。震云是智者,他同样需要常人需要的东西但绝不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他巧妙地驾驭环境而不为它所累。
我曾经问他。当部主任影不影响写小说。他说:“没啥影响,王蒙开完会,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我也不必故作特忙,既然领导让干,那就干吧。”
震云也因为做官而变得更加谨慎:“如果我矫情,大家就不会买我的账”,他心里有数,“一些作家朋友同环境不和谐,说单位总找自己的毛病,其责任多半在自己。不要以为写了点东西就比别人高明,行业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如果想让别人尊重自己,自己首先要尊重别人。”
“我没有其他本事,只会写小说。”震云说。然而他做起官来却很在行,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有些事则故意糊涂。只要事情的大体走向对了,过程中出点问题没有什么;争大不争小,他很少同人发生争论,但是必须力争的事就不讲情面。记得他有两次发脾气,一次因为调人,他骂得很厉害,当着很多女士的面骂;还有一回为了编辑的稿子骂有关部门。
他在部门工作上,不求轰轰烈烈,而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求个安静,求个宽松,果然大家处得很和谐。要么不做,既做就要好;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出影响,同他写小说的路子一样。
几十位名作家撰文的《名家与农村》,呼唤新游记的《心系旅途》,宁缺毋滥的长篇连载《陈永贵沉浮中南海》和《浩然的夫妻生活》,编辑下农村体验生活每人一篇散文的《北京人在李堡》都是这个期间副刊部的拳头产品。
冷面热心
震云看上去有些冷,他性格内向,不喜言谈,很少同人交流,如果不找上门,他是不轻易涉及“文学”二字的。好像不屑同人交谈似的,至于文学界的活动,他总是悄然来去,谁也不知他在做些什么。
“每当我对周围环境烦躁不已时,我就像阿Q一样狠狠想:别以为我活在你们中间,我的心不在这里。”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这样的“创作谈”,更使人对他敬而远之。
距离是存在的,这是他同环境的关系。
“悄悄地做事更加重要,”他说。他喜欢海明威的一句话:“小说好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只露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全在海下。”“这种冰山往前移动是很有气势的。我不喜欢一块冰浮在海上,那样只能是块冰,会很快融化掉的。”
你只有长期相处,才能慢慢了解他。
冷静内涵,睿智机敏,性情温醇随和,重义气,也很富于人情味。念念不忘养育自己的外祖母,喜欢一个人陪她说话。八小时之外,大多时间泡在女儿身上。他的作品很多是由友情的触发而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扉页上就标明:“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震云并不擅唱歌,更很少登台,可有一回在歌厅却为一位女士献了歌。编辑孙丽娜心高而体弱,视力也不好,常为力不从心而叹息。住进康复中心,过节不能回家,大家便聚齐去探望她。邀她出来,点她爱吃的鱼,然后去找歌厅。那天震云带着孩子跑了很多路赶来。本来大伙只想听听别人唱,随着音乐跳跳舞,不料震云第一个上台操起话筒大声说:“我唱一首,献给孙小姐,祝她早日康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唱得小孙哭了,大家听了也很感动。
总是与人为善,总是成人之美,乐于帮忙。我对他最早的印象是他刚到报社不久,我购置了沙发正愁没人帮忙抬,他路过一看,就主动帮我抬上楼,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心里很感激,心想小伙子真朴实。周末版老郝发病住院,震云听说后,邀我同去探望。编辑冯雷的父亲去世了,我们商定去慰问,还派人送过一些钱去。临到向遗体告别,我说咱们隔了一层关系,不去也罢。震云说:“还是去的好。”
“快去,单位开始给装电话了!”有一天他提醒我,好早点把这事办了。他还告诉我穿老头鞋好,他自己有时跟着去开编前会,说穿着舒服,建议我也买一双。
文人相亲
他在同事当中爱称兄道弟。这回杂志约稿,我问从哪个角度写好,他说:“你就写咱们兄弟的相处吧!”记得他第一次赠我他的书,签上了“吾兄指教”。平时也总是“兄长”挂嘴边。国人讲究长幼之序,兄是一种尊称,男人社交上的客套,通常没有严格的年龄概念。但我感觉到他不是一般的称呼,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人、尊重人是他一贯的做人准则,我们合作三年没有发生过任何“过节儿”,同他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尽管性格上有共同之处,但处理事情的路数,一个是作家型的,一个是编辑型的。他是举重若轻,我是举轻若重。我极力调整,还是常常不知不觉陷入琐碎的事务之中。“你总是过于具体”,他自己超然,也希望我超然一些。
有一次我们谈起写作,不经意地聊,聊《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我说到自己的困惑,在报纸上写的东西同杂志上的不一样,没把握,不知这样写行不行。他说,刊物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没把握”往往正是出好东西的时候,他说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时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个什么东西。当时还有几句溢美的话。我似乎觉得自己有希望了。我同他探讨写作仅此一回,却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可见交流不在于多寡,也不在于形式。
1991年底我出差广东、海南,《心系旅途》专栏刚开不久,缺稿了,震云对我出差很高兴:“带上电传机,随时发稿子回来!”我怕丢,没带。南行一个月,回来陆续而成15篇。震云很高兴,请汪曾祺或何镇邦等名家写评论,一方面为了打响专栏同时也为我好,结果是何镇邦写的。
我有幸同他搭档,一块儿搞副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潜移默化地受他影响,明彻了许多生活的真谛,我开始从烦琐的生活困扰中跳出来,变得洒脱一些,自我一些了。平心而论,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那时开始的。
然而震云的写作却早得多,他起先是在二楼空荡的机动记者部,后来是在五楼副刊部的一个独间里一笔一笔写出了《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头人》等七部中篇和两部长篇,在单位里他第一个掷笔换了电脑,写出中篇《新闻》。
今年春天我奉命去另一个部门任职,要离开工作了好几年的副刊,有些留恋。震云很高兴,立刻设酒送我,我明白他的心思,是为我的一些事情着想。
写字的俗人
单位盖宿舍楼,需要搬迁。人们才发现一排平房后墙根冒出的一丛小榆树,长到胳膊粗了。看到它,我联想起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