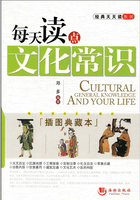星盘应用于航海的最早的、比较确切的记录出现在1481年,它应用于迪奥戈·德·阿赞布雅(Diogo dAzambuja,1432—1518年)率领的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的过程中。1487—1488年迪亚士船队的航行中也使用了星盘,这种星盘是船队的众多装备之一。星盘也同样是达·伽马船队的重要装备之一。达·伽马船队不仅配备了一些小型的,很有可能是金属的星盘,而且携带着一只大型的木质星盘(直径24英寸);达·伽马船队在南非沿海的圣赫勒拿湾(Saint Helena Bay)把它悬挂在一个支架上开展了观测纬度的工作。1492年,哥伦布船队在远航中也使用了与迪亚士和达·伽马船队所配备的星盘类型相似的星盘。1519年当麦哲伦开始他的环球航行时,他携带了六件金属星盘和一件木质星盘。15—17世纪的西方船舶普遍地配备着星盘来观测纬度。
可见,尽管航海用星盘的使用比较艰难,它们还是在西方颇具开创性的几次远航探险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说明采用它们来观测的纬度具有比较高的准确度,因此它们得到了西方诸位航海家的认可,从而成为重要的航海仪器,而且在15—17世纪的西方船舶上得到了普遍应用。而航海用星盘的准确度,显然来自精密的穆斯林星盘。故而,穆斯林星盘以其较高的准确度,间接地促进了西方纬度观测活动的开展和海外探索事业的进步。
测量太阳高度需要根据它的衰减情况进行相应的校正。大约从1485年起,葡萄牙海员开始把观测天体的主要精力转移到观测正午太阳高度上来,这使适合这项观测的星盘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同时,海员们还配备了太阳高度衰减表,它是从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占星家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些表册都经过了修正,用来显示人们所观测到的太阳高度在一天和一年中的变化情况。随着这些表册的使用,较为准确地测量纬度成为可能。
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太阳高度衰减表,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于1484年委托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来进行研究,并且编制专门的航海用天文指导手册。在这位国王当政时期,一位皈依了基督教的博学的犹太人亚伯拉罕·扎库特(Abraham Zacuto),携带着一部名为《天文年鉴》(Almanac Perpetuum)的希伯来语著作来到了葡萄牙。这部著作中含有太阳高度衰减表。他接受委托,向葡萄牙海员传授根据太阳高度的变化来测量纬度的方法。扎库特的朋友梅塞尔·何塞(Messer Jose)把这部著作翻译为拉丁语,这个拉丁语版本于1496年在葡萄牙的莱里亚(Leiria)出版。这就为葡萄牙远航探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需的工具和技术,同时培养出了适应航海需要的人才。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在航行中普遍配备着扎库特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编制的太阳高度衰减表。
哥伦布在1494年和1504年的两次航行中分别测量了月食,进而以此测定经度。这两次测量都是在下锚于加勒比海(Caribbean)中的某些岛屿附近时完成的。这是由于需要确定新发现的岛屿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而进行的观测。在这两次观测中,他都同时使用了扎库特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的天文表册。他在测定西经22°3′和西经38°时产生了部分错误。当然,天文表册不是他的观测出现错误的唯一原因。限于当时无法准确测量经度的客观条件,观测经度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西方观测经度的一次有益尝试。这次尝试获得了来自东方文化圈的扎库特天文表册的支持。
在麦哲伦的邀请下,海员安德烈斯·德·桑·马丁(Andres de San Martin)参加了首次环球航行。他致力于沿着船舶在海岸附近的不同的下锚点来观测经度。在观测过程中,他采用了月球距离法,以及扎库特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的天文表册。巴罗斯引用桑·马丁的文章说明,他采用上述方法,沿着南美洲的东海岸做过5次测量工作。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他所说的第一次和第四次观测结果的数据。前一次的观测结果误差非常大,后一种的误差却非常微小,我们恐怕无从知晓他是怎样减小误差的,也许只是一种巧合。无论如何,他取得了一项比较可观的经度观测结果。这几次勘测也是西方探索经度测量方法的有益尝试,同样获得了扎库特天文表册的支持。
可见,扎库特天文表册不仅帮助了西方人观测纬度的活动,而且帮助了他们测量经度的尝试,支持着西方对于经度测量方法的有益探索。
(二)西方对量天十字尺的使用
大约在1515年,西方海员开始在航海中使用量天十字尺。它很有可能来源于穆斯林船舶所使用的平板仪(Kamal),它是穆斯林海员在印度洋地区,通过测量天体高度而确定纬度的传统仪器。西方的量天十字尺的一个很有可能的起源是,达·伽马船队在航行中对于平板仪的观察。1498年4月,船队在东非海岸邀请到伊本·马季德引航时,这位穆斯林航海家观察到,葡萄牙船队所使用的那些航海仪器中没有一件能够比得上自己的平板仪。达·伽马船队的成员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以平板仪为基础,制作出量天十字尺。量天十字尺又称为直尺仪(Baculus),或者雅各布量天尺(Jacob staff)。同象限仪一样,量天十字尺也需要观测者直接凝视被观测物,因此也难以在黑暗的条件下使用,使用它的最佳时机是在黄昏时分观测恒星。然而,这件仪器的显著优势在于,在颠簸的航船上能够有效地保持平衡,从而保持较高的准确度。
16世纪末期,英国探险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发明了一种改进型的“背光十字尺”(back staff),它可以使观测者背对着太阳来对它进行观测,采用太阳的影子来观测它的高度(altitude)。这种类型的十字尺在英国的海军和商船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他们那里持续使用了一个多世纪。
穆斯林航海者提供的平板仪,成为西方的量天十字尺制作和改进的基础。在穆斯林的启发下,西方又获得了一件重要的航海仪器。于是,主要用来观测黄昏时分的恒星的量天十字尺,与主要用来观测正午太阳高度的星盘,在西方船舶上一起使用,扩展了观测时间和星体范围,提高了船舶的导航与定位能力。这种进步显然得益于平板仪所提供的较高水平的起点。
西方在远航探险活动中制作和使用象限仪、星盘和量天十字尺,以及附属的天文表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其基础仍然是东方地理学成果——阿拉伯人改善或使用的原型仪器。
在航海活动中,象限仪的使用时间不长,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它的使用说明了西方航海思想和地理观念的显著进步,利用象限仪测量船舶在南北方向上航行的较远的距离,必然要考虑到地面的曲率,与测量纬度只剩一步之遥了。尔后,星盘和量天十字尺相继投入航海实践,通过观测星体或正午太阳高度来确定纬度的办法终于成为现实。很显然,它是伴随着托勒密《地理学》思想中的经纬网观念在欧洲的复兴(15世纪初期)而发生的,同时也促进了经纬网观念的复兴。
采用星盘或量天十字尺观测纬度的方法在事实上默认了大地球体观,促进了这一正确的观念突破宗教束缚,重获社会认可的进程。而且,这种观测方法促使海员们更加紧密地把太阳、星体和地球联系在一起来观察,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显著地扩展了视野,扩充了地理知识。此外,海员们持有罗盘、星盘和量天十字尺,就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确定船舶的方位,保持航行方向,使航行的安全性大为增强,远航探险的进程大大加快。
另外,这种观测纬度的方法增强了西方学者对于陆地勘测的兴趣,许多富有进步意义的理论相继产生,一些实地勘测活动也相继出现,促进了陆地勘测事业的发展。海陆两处勘测纬度的活动的日益盛行,使许多地图和航海图上纷纷添加了疏密不同的纬线,甚至还有经线,有力地促进了制图学和地理学的发展。而这些成果,都是在穆斯林的原型仪器的基础上取得的;此外,在勘测纬度的活动中,译自希伯来语的扎库特的天文表册是必备的指南手册,也是东方地理学为西方提供的重要帮助。离开了这个基础,西方将难以迅速取得这些成果。
尤为重要的是,西方逐步地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比较准确地观测纬度,就为绘制带有纬线或纬度刻度的地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了地图的准确度,增强了实用性,促进了数理制图学的发展。
三、结 语
14—17世纪,在东方地理学提供的原型仪器的基础上,西方取得了罗盘术的快速发展,制作出航海用象限仪、星盘和量天十字尺。罗盘协助西方人更为准确地掌握航线上各个港口之间的方位关系;象限仪虽然在西方远航船舶上的应用时间不长,但是成为罗盘的有益补充,帮助西方人掌握了欧洲和非洲大西洋沿岸各主要港口在南北方向上的距离,为观测纬度做了有益的准备。借助星盘、量天十字尺和天文表册,西方实现了对于纬度的比较准确的观测。港口之间的方位关系,在南北方向上的距离,纬度的观测结果,都以比较确切的数据反映出来。14—17世纪,西方人对于欧洲周边海域日益熟悉,并且在海外探索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果,他们观测和搜集到的方位、距离和纬度数据也逐渐地丰富起来,所涉范围从欧洲附近扩展到全球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鲜明地体现在不断改进的珀托兰航海图上。
这些数据为西方数理制图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量化基础。同时,在东方地理学仪器的帮助下,西方逐步地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开展实地观测工作,获取和积累比较准确的数据,并且在此基础上绘制地图,就逐步地为西方制图学的发展建立起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西方制图学日益接近以精确数据为基础的近代制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