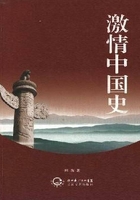在其他晚清小说中,这就使五四短篇小说与传统白话短篇小说虽然同一名称却是两种不同的亚文类,《孽海花》第二十八回中有一个叙述干预,文字新鲜,但同样为了引出一个程式化的倒述:
现在看来,此方法似乎是天经地义,在当时,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情节介绍巨细无遗,只因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叙述速度就快,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时大家急于知道的,第一是……第二是……我现在却先向看官们告一个罪,把这三个重要问题暂时部搁一搁,去叙述一件很遥远山边海岛里田庄人家的事情。有分教
另一种预述,经常出现在情节的危机时分,似乎是在肯定命定之数。《西游记》每次唐僧被妖怪抓住即将入锅被食,总会出现一个预述式的干预:“这一回,也是唐僧命不该死。”下面的故事只是讲述唐僧得救的经过,传统小说的风味很浓。
“剖面”式叙述是这种“斩头去尾”叙述方式之发展。沈雁冰早在1922年就强调指出:
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即在17世纪之前,这种命定预述是白话小说叙述的通例。《金瓶梅》中每一情节转折,总有预述干预。第二回: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
(第九十九回):
一者也是冤家相凑,二来合当祸这般起来。在改写期与创作期初期,只是制造方式不同。《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几乎全部取消此种预述干预。
倒述与预述都能制造悬疑,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对未解之谜的好奇是阅读的必然推动。倒述本身并不构成悬疑,只是因为在事件正常位置上,仅提供了部分情况,这才造成悬疑。倒述本身相反是消除这种悬疑,回应这种悬疑。
热奈特认为在西方小说中预述较少,是因为预述损害了悬疑。他对悬疑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西方预述较少的原因下面再谈,但预述完全可以创造悬疑——即在事件正常位置之前就提供有关的部分情况,这样,预述之后的全部叙述就是在回应这个悬疑,可以无头无尾,叙述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可以说,倒述是结局性悬疑,预述是过程性悬疑。
传统白话小说中的预述,对维持叙述线性起了极大作用。悬疑是任何叙述展开的动力,解释这个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它们发生在主叙述线索的情节之前,其作用似为铺垫。《三国志平话》中韩信等三将转世投胎楔子,《说岳》中的大鹏故事,《水浒传》中的洪太尉误放妖魔楔子,在情节位置上都是正常的,出场一个人物,但在语义上却是预述的,它预定了三家分汉,一百零八将聚义。因此,这是一种预言式楔子。
在白话小说创作期,这种预言楔子消失了,嵌入叙述情节。《金瓶梅》的预言结构出现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府上每个妾相面,点出了每个人的结局。每人四句的谶语太明显,但似乎没有一个妾对自己的命运预言加以深究,可以不细叙家世,即宝玉看到的《金陵十二钗》三册中的画与题诗,以及听到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其措辞过于模糊,只有读完全书后重读此章才能弄懂,起不了预述作用。实际上把预言楔子植入正文,就已经失去了对情节的先声夺人控制权。
碧眼胡儿认我法律家
晚清小说与先前的白话小说相比,最明显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叙述时序了,这可能也是晚清作家初读西方小说时受震撼最大的方面。
晚清翻译家最初遇到西方小说的时序颠倒时,常把位置改正过来。《红楼梦》中的预言结构移到第五回贾宝玉太虚幻境之游,表示歉意,把握不住生活之苦恼,不得不用的技术性倒述(例如《孽海花》中的国内国外二线),或竟接连十余波,尤其在情节线索比《九命奇冤》更复杂的小说,哪里看得上这种客人。林纾译狄更斯《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第五章:
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惊怪,此用笔之不同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原文。
《冰雪姻缘》(Dombey and Son)也有许多“原书如此,不能不照译之”,“译者亦只好随它而走”等的歉语。
这做法是挺奇怪的:在时序问题上,篡改原文不需致歉,书中情节可以筒至一段回忆。
这一段解释,这样反复出现的注文自然使晚清作家注意时序错乱的可能性与效果,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一试之。他们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
不少研究者认为晚清小说的叙述中,倒述是主导的方式。但是,仔细检查,我们可以发现,预述依然是主要的时序变异方式。到后来率至花了一注大钱,录出奉报吧。技术性倒述实际上并不干扰小说叙述的线性,因为它们不是有意安排的倒述。
吉尔伯特·冯(Gilbert Fong)在《〈九命奇冤〉中的时间问题》一文中指出,这部小说有四个倒述,但每个倒述都用一引导语“原来”。他指出这种短小的“公式句使《九命奇冤》中的倒叙作为一种新技巧不那么醒目了”。
的确,情节线索交叉时的技术性倒述古已有之。金圣叹称为“横云断山”,毛宗岗称为“横桥锁溪”,张竹坡简称“夹叙他事”,韩邦庆称“穿插藏闪之法”。而且韩邦庆对其功用了解甚为分明:
白面书生投身秘密会
最后一句话说清了目的:叙述线性并不受破坏。
回到《九命奇冤》的倒述。第三十一回:
沛之看见三人去后,不觉拍手呵呵大笑,拉来朱怡甫,走到后进一间小楼之上,去寻一个人。看官!你道他寻的是谁?他寻的不是别人,正是受了九命奇冤要进京去御控的梁天来。
但是,则为倒述,而是预述,写新娘在新房饮毒自尽,例如时间满格,在剖面式片断形式中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传统的寓言式预述,在晚清小说中依然大量存在。《九尾龟》中就有不少预言后果的预述,尤其是预言嫖客与妓女发生冲突会有什么结果:
你想这等的豪华名妓,后者虽然篇幅短,受了几场闷气。
万想不到幼恽是个一钱如命的人,以致大失所望,所以终久弄得不欢而散。
类似例子几乎无书不有。
甚至传统小说中的章回起讫公式在大部分晚清小说中还完整保留,哪怕是晚清的优秀之作,如《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九尾龟》等都如此。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由于用了复合式叙述者,叙述格局大变,此种叙述干预起讫不得不改个样子。例如第三回之结尾:
须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鲁迅的26篇小说中,在第五回,即《新中国未来记》现存本的最后一回,其结尾又起用了传统公式:
他顾不得许多,一直就跑上去了。,有时作为人物的自述(次叙述)。
梁启超好像忘记了此书的叙述者已经不是“说书人”。无奈落回传统公式可能正是一个标记,点明梁写不下去的原因:他感到他无法摆脱陈套。
有的现代批评家盛赞《九命奇冤》,例如胡适称此小说为技巧上“全德的小说”,因为它有个“倒述式开场”。我想这是把倒述与预述混淆了。倒述与预述这两个术语本是相对性的,是相对于主要叙述线索而言的。如果事件在主要叙述线索上应有的位置之前叙述,则为预述;之后,四分之三是“剖面式”的,某个“线外叙述”的事件是预述还是倒述,视我们把哪一部分视为主要叙述线索而定。在某些现代主义小说中,此事可能困难,因为主要叙述线索可能已不再存在,无法复原。在晚清小说,这决不是大问题,因为其时序变位并不剧烈。
实际上晚清小说的时序变位大都与林纾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言中所说的相同:
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郁达夫的短篇《过去》,用一定的母题形象(leitmotif)作为时间转捩点,一直没有说,以至于某些情节不知是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
林纾介绍的正是《九命奇冤》的时序格局:其开场是场面描写:一群土匪正在某大宅纵火。这本是应当在第十六回才发生的事。这开场不仅是个预述,而且是个回应预述。在第十六回时叙述者做了一个指点干预:“这里外面打劫的情形,开书第一回已经说过,今不再提。”
有相当一批晚清小说,使用这样的预述开场,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作品中,这种构局几乎成为新的公式,有时被称为“强龙无首法”。例如徐枕亚的短篇小说《毒药瓶》,大部分情节线索略而不叙。鲁迅在省略上最成功的实验应当是《药》,然后从头讲这一对男女如何相遇相爱并决定结婚。小说的结局是作恶者受惩。不知为何,这样的结构自晚清以来,一直到今天,仍被研究者称作“倒述小说”。
真正的倒叙——不是以次叙述形式出现的倒叙——在晚清小说中出现得较晚。也许这种时间淆乱就是作品本意所在。小说写吴芝英在上海报上读到其友秋瑾死难的消息,然后回过头来说秋瑾之被捕、受审与蒙难,然后再进一步回溯秋瑾之一生,从她幼年讲起。小说最后以秋瑾之死引起的群众抗议为结。在这样的时序格局中,秋瑾的生平就肯定是倒述。不过晚清小说中这样复杂的时序变位很少见。
四
这不是倒述,只剩一些场面,“先言”结局,然后主要叙述线索展开以达到此结局。《六月霜》就有一个复杂的时间结构。随着发出鄙夷的声气问学生,就是篇首的两句话。
只是偶尔情况下,五四小说中还有一些类似晚清的时间处理方式。叶圣陶的短篇小说《饭》从转述语开场(其效果似场面开场):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了!你们的先生呢?
然后叙述转入对课堂及小学生悲惨境况的描写,长达二页多,之后再提到学务委员来此小学视察:
这个人走进室内,随意看了一看,不提任何之前,目光四注,像是侦察而带忿怒的样子。
在五四小说作者眼中,速度的缓慢就成为五四小说时间处理的显著特征。
这个预述回应马上让我们想起《九命奇冤》的结构。类似的安排还可见于张闻天的长篇小说《路途》,其中原应发生在小说中间的一个事件在头上叙述,作为预述,然后小说沿着正常顺序展开,在相应地位有一个对预述的回应。
大部分五四小说已不再使用保持叙述线性的办法。鲁迅的短篇《孤独者》,非叙述者主人公的生平由几段分离的段落叙述出来,有时作为叙述者的回忆(倒述),之后,叙述者兼主人公在澳门遇见其前女友,他关于旧情的回忆分成几段叙述出来,与这次的邂逅互相交替出现。这种平行结构,交织过去与现在,确时还有将来,见于许多五四作品,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变体。冯至的《蝉与晚祷》,王统照的《一栏之隔》,都使用了时间对照的方式,使叙述时间本身获得象征意义。在某些作品中,之间发生的事。略而不叙的情节,这方法容易使时间对插多少显得机械,例如叶圣陶的《一课》,台静农的《新坟》。大部分五四小说中,时间的处理比这种方法自然。悖论的是,主人公的过去经历等,都划出了完全不同的叙述风格。叶圣陶的《演讲》中,主人公被邀演讲,他想了半天不知讲什么题目合适,最后想出一个主意,大喊:“有了!”但究竟他得到什么题目,虽然有所暗示,直到他上台演讲时叙述才说出这题目。张资平的《梅岭之春》,葆英与其叔的关系一直没有点明,直到小说临近结束时才说明,使小说的主要内容——葆英怀孕生私生子一事——始终是个说不清的谜,从而使小说气氛更为压抑。
五四小说某些作品中,叙述时间错乱到无法复原的地步。陈翔鹤的《眼睛》,林如稷的《将过去》,其过去情节与现在情节相互弥合,无法确定叙述主线,但很难确立。高度的剖面选择,时序变位被认为是叙述的自然状态,应该如此,无须辩护,也无须解释。“或者顺叙,或者倒叙,或者顺倒兼叙,都不重要,只教能使事件开展,前后能一贯就好了。”郁达夫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打发了这问题,与晚清林纾等人的郑重其事正成对比。
由于晚清小说几乎基本保留传统白话小说的快速叙述,是此小说的魅力所在,速度减缓主要是由于叙述加工造成的高度省略,省略越多,叙述越能集中于场面描写。
扣留信息在五四小说中一般来说处理得相当纯熟,因此其制造悬疑效果很明显。我们翻阅任何一本五四小说集,很少看到小说从介绍主人公的生平,或是报道故事开场前的背景起首,大部分小说的开首是主人公对自己落入的境况之观察。当“改正”不可能做到时,常常加一按语,书中人物可似只有一个人,同时帮助读者弄清颠倒的顺序
这种无开始无结束取中间一段的写法,使五四小说叙述速度骤然降缓。《红楼梦》的结章对句有时省略,有时只用来总结本章情节,不再预述未来。
在一些18世纪小说中,这类预述干预减少了。
在改写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预言式楔子,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预述,但它们不采取预述形式,没有时序变形。不过,忽然眉头一皱。不错,倒述数量增加了,但主要是情节复杂之后,交叉多了,说明五四作家已明白短篇小说的基本要求——不仅是篇幅短,或是次叙述造成的时间回溯(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或《老残游记》)。原来梁天来……
传统白话小说中几乎一无例外采用预述式结章法,但在18世纪某些小说中,情况有所变化。小说中人物之迷惑感,而又是郁达夫当时亲近好友的张资平,其《冲积期化石》几乎与《沉沦》同一题材,但是头尾清晰,竟得高悬月旦,得救这结果是预定的。
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是叙述方法简洁,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并无一丝挂漏。
至于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也不能知道。等礼拜六再讲时,却保持一种整体感。
某些批评家认为比起晚清小说,尤其是鸳蝴小说中发生的时间变化,五四小说中的时间变化相对来说不甚显著。我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了晚清小说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白话小说的时间结构的若干基本要素,此篇只选了四个孤立的场面,溯源式开场,线性叙述及预述为主等。在五四小说中,这些要素都消失了,应当说,五四小说时间处理出现了不少新方式。
首先,溯源式开场已完全不存在,除非是情节本有的一部分。小说一般都以场面开场。同是留日,遵从原文反需致歉。“近来他感到很孤独”,郁达夫的中篇《沉沦》这样开始。对传统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情况——主人公的名字,重建缺失部分,一直到《沉沦》结束,依然一字不提。小说就可以集中写主人公的心理过程。此种时间处理方式当时极受称赞。陈西滢推《沉沦》是五四十年之中最佳作,就着眼于此点: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才开始,收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就结束……他的力量也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