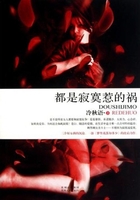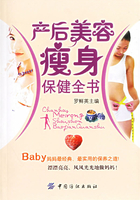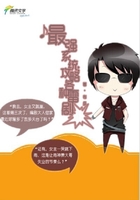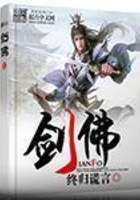再举一个例:孙犁的小说《铁木前传》。这部小说中塑造得最生动,而且使人感到亲切的,却是被批判的人物小满子,正如一个批评家所感叹的:“是无耻?是天真?我们实在说不出。”无疑,她是一个追求享乐(包括性享受)的青年,但是她追求得真诚。小说写到小满子对自己行为的追悔,写到辛勤劳动搞集体化的先进农村青年对她进行帮助,据说小说的主题是要证明“耐心地帮助后进的人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是多么重要”。可能的确这是小说的主题,但小满子形象的成功,使这个主题完全崩溃。小满子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一系列农村小说中“中间人物”的先行者,而且,也正如这些小说一样,中间人物形象特别生动丰满,使这些叙述作品“撑裂”了主题。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容易看出这些小说中“农业共产主义”意识所造成的盲区,但在当时,中间人物的创造者、鼓吹者和批评者实际上都把头碰在同一堵墙上,他们使用的是相似的规范,赞同写中间人物的人并不是想赞美中间人物,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极“左”派正是抓住了把柄:中间人物在这些小说中都只是在情节上被惩罚,在字面上被改造。这是一个绕不出来的死胡同,一个作者和当时的批评家(无论是左是右)都无法看清的盲区。牵强的巧合往往指示盲区的所在。《卖油郎独占花魁》在人际关系上,在婚姻和性关系的自由选择上,非常富于挑战性,但小说一定要写男女双方因战乱而失散的家庭由于他们的结合而非常巧地会合,从而使两人的结合为家庭秩序的恢复服务。相仿的例子可见于折子戏《秋江》的原剧《玉钏记》。《秋江》中尼姑陈妙常逆江而上去追她的情人,而在原剧中陈妙常与其情人竟然是指腹为婚,此后两家失散不通音信,因此虽然陈妙常自己不知道,她向社会道德的勇敢挑战竟然是在履行封建婚约义务而已。
巧合把太富于挑战性的个人行动硬塞入规范的框架之中,从而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造成明显的裂痕。
《简·爱》这本至今被中国大学生爱读的小说,同样落入一个巧合的陷坑:简虽然很爱罗切斯特,但只要罗切斯特的发疯的妻子在世,从19世纪英国社会公认的美德来说,她就必须拒绝罗切斯特共同生活的要求。这个道德约束与叙述展开无法相容,最后谁让步呢?当然是叙述,于是来了个可怕的巧合:罗切斯特太太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死。这样叙述服从了道德规范,却造成很明显的盲区。
因此,我们看到,叙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充满了裂缝、隐言和盲区,它们比明白说出的内容能揭示更多的东西,它们是作品不完美的“症状”,它们无法造成逼真感。相反,它们破坏逼真感,它们无法造成现实幻象。如果说它们也揭示现实的话,它们所揭示的不是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它们反映的并不是作为古典现实主义宗旨的关于世界的真相,它们讲出的是关于观念形态的真相,被意识形态所压抑的真相,存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之中的真相。
为什么观念形态自己不能说出自己的真相呢?因为观念形态的最大特征是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对什么都有一套解释,但就是无法认识自己。那么为什么文学叙述能够揭示观念形态所隐藏的东西,或暴露它的界限呢?因为文学叙述作为一个符号过程实在是过于复杂,把文学叙述的内容和形式组织起来,这个任务太重,超过观念形态所能承受的范围,文学叙述不像政论或历史叙述,能够和谐地、自圆其说地统一在一个观念形态之下。因此,文学叙述必然撑破观念形态。用马歇雷的话来说“就是叙述用使用观念形态来向观念形态挑战”。
金圣叹序《水浒传》云:“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形状、气质、声音,是由小试其端也。”
从这个社会文化形态来说,使用于叙述只是“小试其端”,但《水浒传》叙述文本的复杂性早使这个“刀尺”破绽百出。因此,文学叙述不能仅仅被看成反映了、表达了或体现了观念形态,文学叙述更是“揭露”了文化形态的边界,或者说,其局限性。而叙述形式上的所谓“漏洞”或“疏忽”,往往是此种文化形态有限性的症候。本书中已经有很多例子。再举一段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元钱,非但月底要预付的来月的房金可以无忧,并且付过房金之后,还可以维持几天食料。当时这五元钱对我的效用的广大,是谁也不能推想得出来的。
此话是全文唯一泄露“叙述现在”。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叙述者“我”在讲述自己过去这段经历时,叙述我与被叙述我突然分裂。叙述我的此时恐怕很不一样了,穷愁潦倒、贫困不堪,在上海贫民窟与卷烟女工二妹同病相怜几乎互相爱上的人物“我”,现在可能阔多了,不再在乎那五元钱的意外收入。《春风沉醉的晚上》之所以能打动人,在于其弥漫一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伤感,尤其是其结尾之无出路,之绝望。上引这段中暴露出的“二我差”,可能是个疏忽,却差点毁了整个小说,也几乎翻开了整篇小说的意识形态“盲区”:被抛出权力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与被抛出土地的农民,在游离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上海贫民窟中,有结合的可能吗?
这并不是说叙述作品的结构越差越好。作品结构差可能使“症候”容易找到,但这症候可能只是作品形式本身的不完美之处,与社会文化形态的压力没有关系。从清代中叶开始流行公案侠义小说,到晚清鸳鸯蝴蝶派小说,到现代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中国在通俗小说上历史悠久,不让与人。这些小说当然也可以用症候式阅读法来进行批评,但是它们所能揭示的意义层次和意义深度都很有限。因为社会文化形态明确表现出来的部分,决不会是它的边界部分,而是其最稳固的部分。局限于此,就看不到它的真实形态。要找出《三侠五义》中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但我们所能得到的,也就极有限了。当然,即使这样的作品也能造成足够的逼真性,因此也需要读者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或之上,才能进行症候式阅读。这个距离,笔者称之为“批评超越距离”。像茅盾描写的《火烧红莲寺》的观众,就完全没有批评距离,我们能请他们评论崆峒派、昆仑派,却无法让他批评《火烧红莲寺》的道德规范。
阅读超越,就是拒绝认同,拒绝把叙述世界的逼真性当作现实世界的实体性。
美国19世纪作家爱德加·艾伦·坡有一篇短篇侦探小说《被偷的信》情节很简单:首相夫人昔时在头脑发昏时给情夫写了一封信,现在此信落到了首相的政敌某侯爵手中,成为他政治讹诈的手段。巴黎市警察到侯爵府进行彻底搜查,结果一无所获;首相夫人想到请大侦探杜邦出马。大侦探装作礼节性地访问侯爵,结果就在正常放信的地方——壁炉上方的信插里找到此信。这个故事很类似《空城计》,侯爵在演诸葛亮(或其他大智大勇的战略家)的故伎,巴黎警察是司马懿,想到各种可藏之处,就是想不到看一看不藏的地方。大侦探杜邦比司马懿聪明。
巴尔特说,坡的这篇小说对文学批评来说有极深的寓意:巴黎市警察所做的是刑事侦查的职业性操作,从职业水平层次上说他们做得无懈可击。正如司马懿所做的是战术上的判断,从战术上说,他的退兵决策是完全合理而且必须。但侯爵和杜邦做的是超越刑事侦查职业层次上的对抗,他们都在系统的垂直轴上运动,而进入了高一层次,单层次操作者巴黎警察或司马懿不可能做超越这个层次的推断。
由此,巴尔特得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原则性方法:
要理解一个叙述……必须把叙述线索的水平串接投射到隐指的垂直轴上。读(或听)一个叙述,不是从一个词到下一个词的运动,而是从一个水平到男一个水平的运动。
笔者认为巴尔特这个原理有一般的符号学意义:我们要理解任何一个符号体系的构成,即符号的编码。不能在这个符号集合本身的层次上追溯,而必须超出这个操作层次,进入控制这个操作体系的更高一层系统。
这个“垂直方向的运动”,就是取得批评距离。哪怕从技巧上理解一个叙述,都必然找出这些被叙述事件的叙述者,找出叙述行为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控制叙述的社会文化形态,就必须越出叙述的逼真性控制的范围。同水平阅读即使看出症状,也会把症状当作病因,异水平阅读才能把症状当作诊断的起点。同水平的阅读是与叙述世界合一,从作品本身中分解意义,异水平阅读是与作品保持超越式批评距离,用批评操作从作品后面构筑意义。
而且,由于控制叙述的层次远不止一个:心理层次,民族性层次,人性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本书没有谈到其他一些层次,但并不是否认它们的存在)等等。因此,异水平阅读所构筑的文本意义就不可能只是单层次的。
总结一下笔者在本节中所建议的症候式阅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叙述作品与社会文化形态相互的压力,使叙述作品的线索与形式决不可能完美结合。而正是从这些不完美处,从叙述行为留下的各种痕迹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形态的有限边界。而为了能看到这些不完美处,就必须拒绝作品的规范,拒绝作品造成的现实幻想,获得并保持超越性批评距离。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叙述文本的扬弃,因为它肯定了叙述文本不是一目了然,从字面意义就可以解释的。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对此提出过一个惊人的看法,他认为“文本的真实性即在于其不可解”,因此,“与文本出现的同时,必然要出现文本解释者”。例如,有巫辞就得有祭司,有经文就得有牧师,有法律就得有律师,同样,有艺术作品就得有批评家。“解释者的定义就排除了每个人都能成为解释者的可能。
这话听起来太有点“精英主义”或“文化贵族主义”,看不起群众,实际上客观情况是不仅一般读者,而且大部分批评家,都只在作品同水平层次上作消费或阅读,吃杏子式阅读,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读者都能有超越性批评距离。
反过来说,批评也就不能如一般的阅读,印象式的、欣赏式的、“阅读指南”式的批评也不能看作真正的批评。理解作品的内容或其中表达的观点等等,只是真正的批评操作的准备工作。优秀的文学叙述作品,像一架焊接装配得天衣无缝的油漆得闪闪发光的汽车,要了解它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就不能只坐在驾驶室里,不能沉醉于叙述世界之中,而得把它顶起来,在它底下找到滴着不雅观油腻的缝隙。
头脑冬烘辈,斥为小说不足观。可勿与论矣。若见而信以为有者,其人必拘;见而决其为无者,其人必无情。大约在可信可疑、若有若无间,斯为善读者。
明斋主人在《增评补图石头记》中对《红楼梦》的这段“总评”,是对现代叙述学最困难的课题——叙述作品意义——一个令人称绝的答复。
相比之下,巴尔特对这问题的解释,就显得笨拙:
文学作品既非十分无意义,也并非十分清晰;其意义是“悬搁”的。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意义系统,但意指物却是无法掌握的。这种意义中固有的“失义”正是为什么文学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可以提出关于世界的问题,而不必回答。
巴尔特如果读过中国“前叙述学”,也会向中国古人的卓识表示敬意。
(第七节) “元小说”
“元”(meta-)这个前缀,原是希腊文“在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文集最早的编者安德罗尼库斯把哲学卷放在自然科学卷之后,名之为Metaphisics(《物理学之后》)。由于哲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科学深层规律的思考,因此meta这个词缀具有了新的含义,指对某个系统深层控制规律的探研。如语言的控制规律(语法,词解,语意结构)被称为“元语言”。元语言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小说文本的元语言就是诠释规范体系,就是前面说的“诠释指导”。
以此类推,“元历史”大致上就是历史哲学,“元逻辑”则是逻辑规律的研究,“元批评”类近于哲理美学。港台学者把Meta译为其希腊原意“后设”。但早从康德起我们就知道规律并不出现于现象之后,“后设”这译法不妥。“元”当然是《周易》起开始使用的旧词,《春秋繁露》云:“元者为万物之本。”这译法很能达意。
小说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其释读受控于元语言(广义的语法、词典)。但当小说把小说本身当作对象时,就出现了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自己谈自己的倾向,就是“元小说”。西方批评界在确定“元小说”这个术语前,犹豫了很久。布鲁克—罗丝称之为“实验小说”;爱德勒1976年称之为“超小说”;罗泽同年称之为“外小说”。“元小说”这个术语在1980年左右开始得到公认。但德国学者鲁迪格曾在《当代元小说》一书中指出,在80年代初,元小说只吸引了一小群“难得别扭的小说的读者”,而到了80年代末就蔚为大国。“大批雄心勃勃的批评家和学者进入了这个现在属于文学基本原理的领域。”
元小说是一种非现实主义小说,它与超现实的、荒诞的、魔幻的小说不同,它的“非现实”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它在叙述方式上破坏了小说产生“现实感”的主要条件。
把某物“打上引号”,就是使某物成为语言(或其他艺术表意手段)的操作对象,而不是被语言“反映”的独立于手段之外的客体。当我们说:
小说表现“生活”。
这完全不同于说:
小说表现生活。
后一个宣言是“自然化”的,生活被当作一个存在于小说之外的实体,保留着它的所有本体实在性;而前一个宣言,生活处于引号之内,它的本体性被否决了,它只存在于“小说表现”的操作之中,在这操作之外它不再具有其独立品质。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充分的现场性”。
这两个宣言还有更深一层分歧:在“小说表现生活”中,生活与小说处于同一符号表意层次,操作是同层次的水平运动,它的运动轨迹显彰与否是个次要问题;“小说表现‘生活’”,主宾语项是异层次的,而“小说”比“生活”处于高一层次,它居高临下地处理引号内的事项,表现的操作就成了突然层次障碍的关键性行为。
换句话说,在“小说表现‘生活’”这陈述中,与小说这主词有关的,与其说是“生活”的诸本质内容,不如说是小说表达本身,它的构造之自我定义功能:小说成了关于自身的表意行为,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说,成了元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