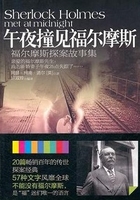笛卡尔说:“比起我的身体,我更能理解我的灵魂。”他的意思是说,对别人,我仅仅能了解身体,因为我无法接近别人的意识。即使是作对比,这句话未免太乐观。哪怕《格调》这样的通俗书,都在令人信服地说,我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还非常起码。哪怕在读懂了该书之后,我对我心的认识,恐怕还没有起步。不然我不会对自己的社会等级无所措手足。
4
19世纪以来,自我膨胀式浪漫主义者,层出不穷。提倡英雄崇拜的卡莱尔,建立“自我”体系对抗非我的费希特,把艺术视为解决主客观“最高同一”的F·施莱辛格,声称“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的叔本华,以及那位推崇“强力意志”的尼采,让人眼花缭乱。
德国人的自我膨胀,偏向于哲理。美国人则把自我膨胀作为应有的生活方式。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Self),楚图南译成《自己之歌》,稍微闪开一下,躲开“我”字。但是反复咏叹得很明确:“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哪怕有“你”,还是自己:“我相信你,我的灵魂。”
另一首同样有名的诗《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说得更清楚一些:“我歌唱的主题是渺小的,但也是最大的——那就是,个人自己——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为了新世界,我歌唱这个。”
自我膨胀是美国的需要,不一定是欧洲(“旧世界”)的需要,其他国家呢?惠特曼当时无法猜到中国人自我的崛起。
幸好,每当有一群自我浪漫主义者出现,必有更多的自我限制的悲观主义者应运而生,不然,现代思想史,就成了自大狂的辩护史,现代文学史就满是向这无限飞翔,而满世界无人不癫狂。
例如加缪在《反叛的人》中就认为在苏联式的集体主义,与美国式的“存在主义”之间,可以有一种“地中海-欧洲文化态度”:回向希腊文明倡导的平衡,人不一定非要跨过生命的局限。反叛是需要的,但是浮士德式的无限追求,会让人失去节制。
我同意英国当代哲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境况中的自我,必须依靠反思产生。”《中庸》里说的“不思而得”的圣人,在现代已经不可能。
自我膨胀,是为了涨破传统社会的硬壳,引出开放式的个人——社会关系,以适应市场需要。这壳固然是限制,却也是自我的保护壳。裸露的自我,固然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的自由,却增添了选择的焦虑:自行建立与社会的关系,远不是毫无精神代价。
自我限制派与膨胀派的对立,最出人意料的是弗洛伊德与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学说的冲突。一般都认为弗洛伊德应当对20世纪的自恋狂负主要责任。或许有道理。但是赖希的心理分析理论,崇尚自我远远更甚。
这位奥地利医生原信奉弗洛伊德,投于门下。1927年出版《性高潮的作用》,认为性高潮是某种宇宙能量(他称为“高潮素”Orgone)与自我的对接,是人生的至高需要。而各种社会压制,形成生殖器官的“黏膜甲壳”,自我一旦失去“高潮潜力”,生理上会引发高血压、溃疡、风湿等“压抑病”,社会上造成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主义。无法达到完全的性高潮,就不会有完整的自我。
弗洛伊德描述的自我,远比赖希说的复杂:完全立即地满足本能欲望,会同社会发生冲突,而且引出过大的负疚感。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以本能的遏制为基础的”。他认为这是必要的,是文明的代价。自然,现代文明向纵深发展,意味着负罪感增加。
赖希的书,1947年译成英语后,突然开始轰动。1954年,他的著作被禁,已经移居美国的赖希本人,也被关进疯人院。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任主席的心理分析学会,宣布开除赖希。
斗转星移,赖希1957年死于狱中后,他的各种著作大行其道,这位一度被视为伪科学家的妄人,现在成为圣者。
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基本上与赖希一脉相承,只是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上: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人的深度欲望。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自己政治上如何受摆布,但是无法说清自己在文化上、心理上如何被社会控制。要索回自我的“反抗能力”,只有回到本能欲望上去。
这种个人反抗哲学,在萨特那里集大成。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他自身: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此乐观勇敢的存在主义,离海德格尔那种强调存在的畏惧和焦虑的哲学,已经相去甚远。
5
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起跳,就扎进什么样的水里。“我”,远比我们胆敢设想的复杂得多。
当代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反而让人看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种族,阶级,性别之中,对此我们没有选择能力。我们身上先天决定的因素,远比我们想象的为多,生命像一颗已经丢出去的骰子:在基因那一团纠结的乱麻里,智商,相貌,身高,体重,瞳仁的颜色,以及许多疾病,都已经先于我的存在被决定,任我如何“选择”都无法改变。最近,调查同基因双生子,发现基因甚至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同样的半杯饮料,有幸福感基因的人,倾向于说“还有半杯呐”;而生来感到不幸的人,常说 “只剩半杯了”。自我的第一大奋斗目标,竟然先天已经决定!
关于性格的研究,似乎扩大到基因之外。据心理学家调查,母亲做得不好,会使子女一生遇到多达70项的“问题”。最近又有调查,发现剖腹产婴儿,长大后容易依赖他人,性情急躁。他们没有“阴道产儿”那种奋斗挣扎让自我出胎的“胎儿记忆”。在西方,近20年剖腹产增加三倍;在中国,恐怕30倍不止,无怪近年烦躁儿童大增。
6
自我的问题,如此复杂,就像自恋与羞耻,饕餮与厌食,大部分人在两极之间摇摆。据许多传记说,最漂亮的女人戴安娜王妃,生前就是每隔一个星期从暴食跌倒另一头——厌食。社会规范,给我的选择自由带上负罪感,于是我们想自我控制,健身,化妆,整容,当今各种控制自己肉身的秘方,成为大规模的产业,与其说是由于我们自恋,不如说是对自我感到焦虑。
而在当代中国,我们读到许多平易近人的自我中心教导:哲理散文家赠给我们的尤其多:
“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
除了事业爱情,“不要忘记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
对每个人,最宝贵的是自己,因为,“你死后,没人能代你再活一次。”
看来我们的哲学家是在把尼采“成为你自己”的训导,变着花样反复说。
这些箴言,如果是美国教育家写的,恐怕他得为这几句话作一番界定。如果是欧洲校长,恐怕他会挨社群主义者的抨击。在当今中国,听起来几乎是老生常谈。抱怨这些“哲理美文”清汤寡水,没有思想韧性的读者或许有之,对这些话是否站得住脚的怀疑,我尚未听到。
曾几何时,我们尚是以对国家责任感的道德立国之模范,不久以前,我们还是全世界最美好的集体主义乌托邦。难道真是中国人变化快?或许美国汉学家感慨得对:“中国人学美国学得真快”?
让我斗胆说一句:中国人学美国人太容易,中国人学做中国人才是难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即儒家家族伦理,本来就不牢固,缺少价值超越性,宗教式神圣化不够,加上缺少哲理的深虑反思,流于疏浅的工具理性层次。“文革”把这套改装过的旧价值,付诸狂热极端的全民强迫实践。在不可避免的大失败之后,从“文革”后期开始,就只能把这些价值弃之不顾。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早已经不像中国人,更像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
我倒是听到过一位做比较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虚拟实验:把一个世纪前的平均美国人,西欧人,波斯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以及中国人,与当今的平均美国人,西欧人,伊朗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以及中国人,一对对坐着,你就会发现,从外表到内心,中国人变化远为最大。
中国人变得如此快,当然是好事。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哲学家出来,为中国人急剧变形的自我作辩护,或代我们忧虑反思,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必质疑,这点最令我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