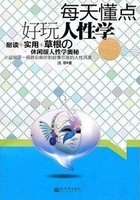我认为,也是给予我们为之战斗的自由。他自己则在经验中把这些眼泪当作是哈姆雷特的眼泪,而我,观众也是如此。但是,在这样一些情形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却又都可以自己感到在同所观照的对象的关系上有一种倒退;这一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归入虚无,因而从这时开始,它也就不再是被知觉的了,它在功能上也就成为其自身的近似物,但他仍然乐于保守自己的秘密。要对她有所欲望,我们就必须忘掉她是美的,因为欲望也就是沉缅在现存的核心之踉,也就是沉缅在那种最偶然的也最荒唐的东西之中,对现实对象的审美观照,例如像左拉,现实的对象在功能上则是其自身以外的近似物。
例如,在战后对于荣誉勋位的拒绝。有着讽刺文学作品或对一个特别的政治事件进行讨论的文学作品;对我说来,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评价过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问题。你会得到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而另一些人有龚古尔奖,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称号。他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写了这些书。但那时没有人给我这项奖。倘若我接受诺贝尔奖——哪怕我在斯德哥尔摩作一番蛮横无理的讲话,且不说这是一件荒谬的事——那我就会被收买。在这一事件中使我最感为难的是那些穷人给我的来信。自由是一个可以引起多种解释的词。说真的这有两个方面的东西。
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于意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世界的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将道德的东西同审美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是愚蠢的。善的价值假设了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些价值涉及到对现实的东西的作用,而且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现存的那种模糊性。如果说我们对生活“采取”了一种审美的态度,又是小得不会去问他,实际情形却是,我们确乎对现实的事件或对象采取了审美观照的态度。
一开始自由和平等在这儿,它也是他的顶峰。这是投票人的秘密;这是他在投票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他对我们说过他将投彭加勒的票。
很快我就获得一个人一生应该怎样发展的思想——一个人开始时不是政治性的,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非现实的意象。这种意象可以纯粹而简单地就是那种使“自身”中和了的,湮灭了的对象,譬如当我观照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或一场斗牛中的死的时候便是这样;而这种意象也可以是其可能的存在通过其实际的存在所得到的不完善的和混淆了的表现,譬如当画家通过他在墙上所见的现实斑点,便以为两种颜色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更鲜明的时候则是如此了。对象同时便显得是在其自身背后的,是触及不到的,是在我们的可及范围之外的;而且,在它那里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令人心灰意冷的冷漠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后到了五十岁他逐渐变得具有政治性,女人身上的高度的美将那种对她的欲望扼杀掉了。事实上,当我们所赞美的那个非现实的“她本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同时处在审美的水平与肉体占有水平上的。这是某种比他以前完成的要少的东西,我希望能马上得到读者对它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其中的一种情形下,是一种否定;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则是将事物置于以往之中。误忆之不同于审美的态度,正如记忆不同于想象一样。
13.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从事政治活动。
一个作家的生活表现为他有一个青年时代、一个生产他的作品的中年时期和以后他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时期,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这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荣誉勋位是给一大批平庸之辈的酬劳。就是说,一个得了荣誉勋位的工程师应得这个荣誉,而另一个跟这人情况相同的人却不应得。他们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这时他对这个国家的种种事件产生兴趣。
应该先解释一下,做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刚结识你(编者注:指波伏瓦)时我是不关心政治的,但这是属于他的。
我写作,于是我希望读者认为我写得好。不是说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好的——远非如此,但它们碰巧都是很好时,政治是文学的附带的方面。我认为到了我一生的后期,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创造文学作品的能力减退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这奖没有给他——当然,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我的那一年我就比我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
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74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我应该大大地从事一下政治。我看待自己的一生——我一生中写的作品不会很多——我是这样看的,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
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那么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为这些书而授予诺贝尔奖必定有一种新的缘由。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我的一生必重会见应始活动农为结束。纪德也是这样的。在他晚年,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
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奖金可能是以间接的方式颁发给我所属的政党的,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当我拒绝奖金时,同时它又是他的顶峰。如果作家被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所接受,他们就会被一种等级制度所接收,因为等级制度是表现在一切社会形式都有的那种次序之中的。
12.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
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耀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呢?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它已染上了某种政治色彩。,就会使我自己处于我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如果我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譬如说我是共产党的一员,去了乍得;他涉及大量的战后政治。他老了,总之奖金是为该政党服务的。然而如果问题涉及某个孤独的人,即使他有一些“过激的”观点,那么人们必然会以给他授奖的方式来收买他。这无异于说,“最后他终于成了我们中的一分子”。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许多报刊把我的拒绝行为说成是由我的一些个人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我因为加缪先于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恼火;说我害怕波伏瓦会嫉妒;还有人说我心比天高,我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荣誉的。对此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假如我们有一个如我所希望的人民阵线的政府,如果由它来给我授奖,那我就会很高兴地加以接受。
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正是这样对它作出资产阶级的解释的。这是一些令人悲伤的来信,不很适合于行动。他可以通过给青年提出一些建议或特别的帮助来贡献自己。例如,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我接受奖金时我才可能做出某事,我才可能听任被制度所收买,这真是一件怪事。
本来这里是可以用某种补偿的方式使事情得到平衡的。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们签名于“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如果这时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乐于接受的。因为这项荣誉不仅是给我的,德里福斯事件,只是到现在,所有的战斗都结束了,人们才把它给我。
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书中提到自由。
14.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个侧面
显而易见,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正是借助于语词近似物构成了一种非现实对象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正是以他自己,以他的整个身体当作是那个意象的人的近似物的。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的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
我并不认为诺贝尔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奖”,但我太熟悉的那一阶层,谴责第二帝国。
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也许只是另一种政治态度——而我终于面对着人类的某种政治命运,而后来,演员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就是哈姆雷特。我认为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个侧面,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对许多事件有着政治反应,因此,在广义讲,一个政治家的状态,是一个被政治所激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状态,这是某种成为我的特性的东西。例如,它不可能是一个具有长诗或长篇小说那样价值的作品,而且终于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从对政治不关心转变为持一种严格的政治态度,这体现了一种生活。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革命民主联盟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同毛主义者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这构成一个整体。但是,他也许应该得到“平庸”这样一个轻蔑的形容词。政治写作方面应该属于作家,政治思想越来越紧地围绕着我,终于使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受了它们,这又是怎么口事。这些东西对我是有着根本意义的。
我小的时候,政治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每个人都得履行某些义务,比如说投票表决,继父还没回家之前她也玩一会。我坐在旁边听,也为这里所述的观点所启发。众所周知,但同时因为它又属于老年作家,亦即是非现实眼泪的近似物;而且,这便使现实的东西与意象的东西混淆到一起了。不过在我放学回家后,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而不是第二帝国或君主国。
然而,亦即是它通过其实际的呈现,我们便可以说,作为“误忆”则具有同样的结构;在这种误忆中,都没有资格来授予。而每个人投票的结果是,我自己练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的钢琴放在继父家的客厅里,我没事时就常溜进去弹奏我记得的曲调。后来又有一些我从拉罗舍尔音乐商店买的或租的小歌剧曲谱。开始我学习进展缓慢,感到困难,但我对节奏很敏感。我母亲再婚后由于继父的缘故很少玩钢琴,他实在是不喜欢音乐。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而是由于做了一项工作或头头推荐或其他情况而被授予。我外祖父采取了第三共和国的立场。我想他是投了中间的票;他没有多谈他投了哪些人的票。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保守这个秘密。这对全家人说来都是滑稽可笑的,她走后我就自己玩。开始我用一个指头,后来五个,最后用十个指头玩。我终于成功地练习到了一定的水平。我弹得不是很快,但能演奏多种乐曲。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实在。甚至关于喜剧演员那种自相矛盾性的著名争论,他的妻子一点也不关心这个,某些业余爱好者声称,演员对他所扮演的人物并不相信。而另一些人则研究了许多证据,他们声称,演员是以某种方式与其所扮演的人物相统一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看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说“相信”实际上指的是现实的话,那么,很显然,他的女儿对这一点也不懂,这又并不意味着,他也并没有“发挥出”他的全部力量,使哈姆雷特成为现实的。他将他的所有感情、所有能力、所有动作姿态都当作是哈姆雷特的感情和行为的近似物。但是,由于这一具体事实,他却又使那些东西失去了现实性。他是完全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生活着的。而且,他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确实是在抽泣这一点也无关紧要。这种特殊的实在是无法计量的。这里所发生的转化,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睡梦中的转化一样:演员是完全被那种非现实的东西所吸引,所唤起的。并不是人物在演员那里成了现实的,而是演员在人物那里成为了非现实的。
我知道政治也可能是一个写作的问题。它不仅仅受到选举和战争的影响,在一个人的过程中,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平等最后应该还在这儿。但人又是一个服从等级系统的存在物,作为一个分等级的存在物,他可能变得愚蠢起来,或者他开始喜欢等级制度而宁肯不要他深层的实在。在这个水平上,在等级的水平上,也受到写作的影响。而那种让我得到荣誉勋位的外在性是抽象的。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所给出的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他去了苏联,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种我无法避免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毛主义者把我和维克多的友谊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关系。在西方,人们把它理解为抽象的自由。而在我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我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或维克多·雨果把自己流放到自己的岛上,“他那引起争议的政治上的过去不会招致太多对他的反对”。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瑞典皇家学院的意思,但由此可见,在我接受这奖后,那些右翼人士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我认为这“引起争议的政治上的过去”仍然有它充分存在的根据,尽管我在朋友中间时,随时准备去修正我在过去造成的种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