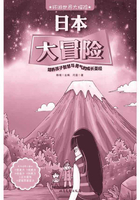绥州已经偏靠西北,人说话的声音很响亮,吃的东西也与中原不大相同。我们在驿站歇下来,驿站的人十分热情殷勤,把最好的院子洒扫了收拾了给我们住。吃的东西也极有绥州的特色。白面里夹了豆面和小米面摊的煎饼柔韧筋道,煎饼里卷着油炸芝麻椒盐馓子,外软里酥,口感极好。用巧姐的话说,好吃是好吃,就是太累牙了,吃半个卷起来的煎饼卷馓子,累的两腮酸的没力气。一边福嫂子在笑:“这个东西是好吃,就是练牙口。巧姑娘别吃这个了,喝点羊肉汤吧。”
巧姐点头,然后又想起来问:“福大娘,这个东西带着做干粮,在路上吃,可方便么?”
福嫂子说:“自然能,不过得包的密实些,否则,煎饼一搁变的极硬咬不动,馓子却吸了潮气绵软失了味道光剩油气,两样都不好吃了。上次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图省事,用煎饼把馓子卷好了带着,结果等到要吃的时候,哎呀呀……那可是难下口呢。”
巧姐点了点头,福嫂子问:“巧姑娘可是喜欢?那我去准备着,带一些路上吃。”
“不是的。”巧姐摆摆手,笑眯眯的说:“就是觉得这出门啊,比困在家里是好玩的多了,在家里可看不到,听不到,见识不到这么多新鲜有意思的事儿。”
我微微一笑,虽然也觉得味道不错,可是那个煎饼嚼起来是费力。
“夫人要是吃不惯,咱们就先别吃这个了。这驿站也备有大米菜蔬,咱们也有厨子,这就去蒸锅白饭弄些小菜来。”
“不用了,”我笑:“弄来了也没力气再吃了,别说巧儿,就是我这两腮也觉得累的不行。喝点汤算了。”
那羊肉汤有两种,一边上面红亮亮的一层辣椒油,另一边是清汤羊肉只点了醋,桌上摆的调羊肝拌羊肚儿白切羊肉,看架式这里的主要肉食就是羊肉了。还有一只焖的烂烂的鸡,我舀了一勺鸡汤喝了,又夹了些白菜吃。巧姐一时好奇,把那红艳艳的汤喝了一口,辣的只一愣,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哎呀,巧姑娘,这是,这是烫着还是辣着了?哎呀呀,这汤真不该端过来……”福嫂子急的要命,我说:“倒些温水,加点蜂蜜给她含两口,就好了。这是又热又辣,谁叫你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呢。”
巧姐只流泪,说不出话来,平儿急忙掏帕子给她擦眼抹泪,红眼睛红鼻子红嘴头,看起来真是滑稽可爱。
福嫂子动作极快,已经把蜂蜜水端来了,巧姐喝了一口含着,眼里还噙着泪花,鼻翼一抽一抽的,象只小兔子一样。
“楼下沈爷他们吃了么?”
“已经用过饭了,我们这边上了桌他们那边也就开饭,听动静比我们吃的可快,已经都收拾过了呢。”
“那是,他们吃饭是快些。”福嫂子看平儿和巧姐吃完坐到一边,还俯下身来,有意无意似的说:“原来我就说,用咱们的厨子做饭食,夫人和姑娘也能吃的惯。偏还是爷吩咐的,说总是难得出门一趟,既来了这个地方,就尝尝当地的特色吃食,也不算是白来了一遭。”
这一路上我和沈恬没有多少说话的功夫,不过,他的体贴倒是总是不经意间表现出来。
比如我们的行走路线,六子不经意提起过,他们常来常往其实并不走现在这条路,而是走一条更近,但是要艰苦的多的路线,那一路可够吃苦的,常常要露宿野外。现在带着我们一行,走的尽是大路,歇脚要么在驿站,要么在大客栈里,虽然路途颠簸难免风霜,但是说真的,我们这一路走的还算是很舒服的了。
“嗯,沈爷是好意,”我慢慢的说:“将来要是和人说起来过绥州,总不至于连绥州什么东西出名也说不上来。”
“这说的也是。”福嫂子让人撤下饭桌,又说:“一路风尘仆仆,套间儿里让人备了热水,夫人和姑娘洗一洗,早些休息吧。”
我点个头,目送她出去。
话说,泡澡真是享受啊……
平儿帮着我把头发也洗了,巧姐也痛痛快快的洗了个够。热水足够,平儿照顾完我们俩自己也洗了一下,我还帮她用皂角搓洗头发,这皂角膏里面应该是兑了茉莉花香料,闻着让人觉得舒畅清新。我的头发用布包在头顶,有时候真觉得这么长的头发太累赘了,不过此时可没有女子轻易剪发的,这个念头想也不能想。
平儿浸在热水里,湿透的秀发更显的乌黑似云。
“凤姐,沈爷待人是真的不错的……”
我笑笑,舀水替她冲头:“你也不用这样说,我知道你心存疑虑,这几天晚上都翻来覆去的难睡着觉。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挺靠得住的。”
平儿的心情是一定复杂的。这时候可不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没感情了,大家可以一拍两散各自去寻找另一段缘分。我还顶着贾府媳妇的身份却跟另一个男人跑了,这些所作所为简直可以用‘**’,‘伤风败俗’来定义了。平儿是这个时代的女人,她心里一定有更多的惶恐和压力。
还有,巧姐现在是小,她大了,保不齐怎么想我呢。毕竟——巧姐是姓贾的。
看着家族运势不妙出门避祸是一回事,避着避着和别的男人勾搭上了……
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办法自圆其说,只好尽量不去想不去提。
等我们都洗完,蘸了头油将头发慢慢梳顺等着干,屋里是一股洗完澡之后的带着潮意和香味儿气息。巧姐洗的脸红扑扑的直喊热,要开窗子透透气。平儿劝她,这里的院子可不是我们以前住的院子,一个外人没有。这里是驿站,怎么说也人来人往的,就算这院子我们包下来了,也不能太过随意放肆,把巧姐劝下来,拿木梳再给她细细的梳头。平儿梳头很有一手,不轻不重,被梳的人只深感舒畅放松,几乎会在梳头的时候睡着。
巧姐就被这么哄睡了,平儿也陪着她先上了床。她们两个睡套间里,我睡靠东墙下的那张,床已经铺好,我坐在床边,心里面觉得好象被塞的很满,可又不知道又都塞的什么东西。再仔细去想时,又觉得很空。
外面月亮起来了,映在窗纸上。
我听着外面脚步声响,然后沈恬的声音,很轻,挺柔的在问:“夫人睡了吗?”
“刚才沐浴过,现在想是已经睡下了。”
我趿着鞋下了床,靠近门边走了几步,低声说:“我还没睡,有什么事么?”
对沈恬,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奇怪的。
一方面,我觉得他实在神秘。他的背景我到现在还猜不出来。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似乎完全了解他,我能看懂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时候,仿佛整个心神都倾注在人的身上,令人不能不被打动。
那样的目光,就是铁石也会被融化的吧?
“没什么……”他顿了一下,我听到福嫂子走开了,他才低声说:“就是想寻你说说话。”
我唔了一声,靠门站着,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这个人真是……
我和他到底谁是穿来的呀,他这副作风,倒象现代人谈恋爱的那种做派。谈恋爱谈恋爱,不谈怎么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