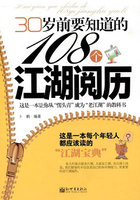熙景三十年夏,皇帝病危,朝中动荡,太子与瑞王两股势力分掌朝廷,斗争愈来愈激烈。五月底,国舅门生京兆尹周良被弹劾,最终因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而锒铛入狱,此事牵连甚广,无疑是对太子势力的一个巨大的打击。六月中,昭国率大军侵犯边境,朝廷命辅国大将军为帅,领兵十万出击,虽说辅国大将军无明确地表示支持瑞王,但此事到底在无形中削弱了瑞王的势力。
瑞王韬光养晦数年,去年博得皇帝信任,得以掌管左右两路禁军,手下多是武官,却苦于出师无名,而太子虽有储君之名,名正言顺,近年来亦竭力了建立一支人数不少的亲兵,可惜底下多是文臣,并无良将,一旦兵变,并无胜算。
唯一的变数可算是沈青彦,他独领一支青衣骑,不受他人管制,直接听命于皇帝。青衣骑虽然只有五千人,却是由皇帝一手创立的,随其打下了半壁江山,如今的青衣骑虽换入了不少年少之士,可战力仍非一般军队可比。前几年沈青彦考取了武状元之功名,皇帝称其年少有为,又深谙兵法,便这支军队拨与他带领。虽说沈青彦是瑞王的好友,可亦有传闻说其钟情于太子妃,情字当前,谁也无法保证他不会调转枪头对付自己的好友。
沈青彦显然比过去更忙碌了,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彻夜不归,秦瑶虽从不过问,但心到底是苦闷的,觉得他近来待她冷淡了许多。虽已是夏日,可夜半醒来,枕边微凉,又岂能不慨叹?可怜闺中寂寞人,不想她亦会沦落至此。
屋中烛火早已熄灭,窗外月光皎洁,屋中人却无心思睡,披着单衣立在窗前仰望着。
却听屋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沈青彦脚步轻轻地走了进来,看到秦瑶,眼中露出了几分惊讶。
“夜已深,娘子为何还不睡?”他走近她,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脂粉味。
秦瑶疑惑地蹙起了眉头:“相公才是,如何深夜才回?”
“不过是朝中的应酬罢了。”沈青彦含糊其词。
“是么?”秦瑶尤不相信,“不知相公近来都在做些什么?可有为难之处?”
沈青彦的神色有片刻凝滞,却搂住她的肩膀将她扶至床边,笑道:“娘子莫要多虑,好好歇息吧,待忙过了这一阵,为夫带你到南方游玩可好?”
“相公此话可要算数才好。”秦瑶亦笑道,尽管眼底的虑色并无消减半分。
事实上,秦瑶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沈青彦身处朝廷,总有身不由己之时,有许多结果并不是二人抗拒便能改变的。
七月初,瑞王送了一名美姬至府上,其姿色与才气都不在秦湘之下,沈青彦碍于局势,只得将她留在府中。
秦瑶自然不乐意,可也无可奈何。自动寻上门的琴鸢姑娘他们可以用银子打发,可瑞王送来的女人却不是用随口编造的借口便能推却的,尤其是在这动荡的季节里。据闻太子与瑞王两派都欲拉拢沈青彦,而瑞王送来这名美姬未必是想用她拴住沈青彦的心,却是要他表明自己的立场。
沈青彦看着秦瑶的眼神满是愧疚:“抱歉,娘子,但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待的。”
秦瑶唇角勾起一抹苦涩:“好,我等着,可是,在这位姑娘出府之前,你还是不要来找我了吧。”
那位美姬被安排在府中的一处偏院住下,偶尔会随沈青彦出席一些宴会,虽然与秦瑶碰面的机会不大,但秦瑶还是无法消除心中的芥蒂,她承认,她并不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她无法容忍自己的丈夫拥有自己以外的任何女人。
沈青彦果然谨守诺言,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她面前,可她并不见得会欢喜,偶尔低头苦笑,亦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坚持着什么。他送的白玉还如往日般通透,他说过定不会负她,他恐怕也是迫于无奈,她或许该像别家的妻子那般体谅他……可是,他沈青彦不是别人,她秦瑶也不是别家的妻子,他从不曾向她解释,她亦坚守着不愿放低自己的底线……
沈青彦收下瑞王送的美姬一事自然也传到了太子派系的人耳中,因关系重大,他们很快便有了动作,出乎所料的是,此番竟还扯上了秦瑶。
最先找上秦瑶是秦丞相,他领着幼子秦欢登门造访,选的却是沈青彦外出之时。秦瑶看着客厅中逗弄着秦欢的父亲,心中颇不是滋味。事隔多年之后,他再次在她面前演出这慈父的角色,却不是为了她,而当中恐怕还牵系着许多利益与谋算。
“女儿拜见父亲。”她上前施礼道。
秦丞相放下膝上的幼子,笑道:“都是自家人,何必拘礼?”
“是,父亲。”秦瑶道,挽裙于旁侧坐下。秦欢还是个五六岁的幼儿,眼神仍懵懂,看到秦瑶几番想亲近却又腼腆地躲在父亲身后。
奴仆为秦瑶奉上茶后便退了出去,客厅内突然安静下来,杯中茶烟袅袅,就像是二人漂浮不定的思绪。
“不知父亲今日前来所为何事?”秦瑶问道,她已多年不与父亲亲近,此刻相聚一堂,一时之间亦不知该说些什么。
“瑶儿不必拘谨,为父不过是来探望自己的女儿罢了。说来惭愧,自你出嫁以后,为父都似乎还不曾关心过你,也不知你在沈家过得好不好。我本以为沈府该是一个好归宿,怎料近来竟听说沈将军新近收了一名美姬……唉,倒是委屈你了。”秦丞相太息,语重心长。
秦瑶看着他鬓侧的白发,忽觉他比自己印象中的父亲老了许多,可那双颇为浑浊的老眸中却依然浮显着野心。她又不明白了,这般辛苦劳碌究竟是为何?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当真如此重要吗?
“父亲多虑了,大户人家三妻四妾乃寻常事,当初娘亲不是亦与魏夫人一同伺候父亲了么?况夫君待女儿极好,父亲大可不比挂心。”秦瑶道,语气中多少带着些讽刺之意,尤其是提及她娘亲之时。
秦丞相纵横官场多年,自然能听出其中深意,神情有些僵硬:“既然如此,为父便可安心了,可……”他顿了顿,看似有些犹豫,“瑶儿,你往后也得劝劝你的夫君,自家人还是帮着自家人比较好,外人终究是信不过的。”
“是么?”秦瑶有丝不以为然,他口中的自家人恐怕未必会把她当做自家人,“父亲的意思可是要女儿劝夫君帮助太子殿下?”
“瑶儿若能明白便再好不过。”
“可惜女儿向来不过问夫君在朝中之事,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妨,有心便可。只是……他日若你姐夫与姐姐落败……为父亦不敢多求,只求你能让秦家留下一点血脉……”他将秦欢拉到自己面前。
秦瑶看了一眼面容稚嫩的幼弟,虽说孩子无罪,可她还是忍不住暗笑,想来这才是她父亲的主要目的——为了保存自己。
“若力所能及,女儿自当尽力。”
“那么为父便代欢儿谢过瑶儿了。唉……倒是难为你了。”他再次叹息,看似万分无奈。
“罢了,时候不早,为父便先行告辞了,你在沈府虽是当家主母,可万事还是得小心谨慎些,这儿终归不比自己家。”他起身道。
“女儿恭送父亲。”秦瑶亦站了起来。
秦丞相看了她一眼,又长叹了一声,便拉着秦欢迈了出去。
“父亲。”秦瑶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唤住了他,“他日若女儿落难了,父亲也会如今日一般为了女儿去向姐姐求情么?”
秦丞相一顿,许久没有言语,秦瑶看他的反应,心中便已有了答案:“父亲,父亲似乎许多年不曾到娘的坟前上香了吧?”
秦丞相回过了头,疑惑地凝视着她,仿佛从来不认识自己的女儿:“瑶儿,你可是在怨父亲?”
“是。”秦瑶抬头微笑,直言不讳。
秦丞相的脸色变得铁青,鼻下的胡子吹动,像在压抑着什么,秦欢不解自己的父亲为何停下脚步,仰起头晃了晃父亲的手。
秦丞相似猛然回过神,略为窘迫地别开了视线:“也罢,这些年我确实愧对你娘,但无论如何,她也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
“却不是最爱的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不是么?”秦瑶依然微笑,淡然地提醒他。
世人都道女人贪婪,可秦瑶却觉得自己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真心人罢了。沈青彦不愿重蹈他爹的覆辙,她又何曾愿意踏上她娘亲的旧路?
送走秦丞相后,秦瑶便到院子里的小亭中闲坐,天色渐暗,而沈青彦未回,直到用过了晚膳之后才听丫头说他回来了,喝得酩酊大醉,被小厮搀扶着去了书房。
绿意担忧地看着自家的小姐道:“小姐,您别多想,姑爷或许只是被朝中的同僚绊住了。”
“或许是的,放心吧,我不曾多想。”她浅笑道,却再一次摸出了那块白玉,捏在手心再一次告诉自己要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