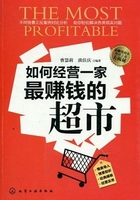做尽了那些下人做的事,可到头来她却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是!我自讨苦吃!我活该!天底下温柔善良,像水一般的姑娘多的是,可偏偏我就稀罕她这么个绝情的主!”
殿小二风风火火地闯入了月老庙,把正在数银子的杜潮守抓起来便大吼了一顿,若不是他的手实在肿得厉害,只怕连庙中的桌子也难逃被分尸的命运。
杜潮守被吼得一愣一愣的,他小心翼翼地退开了两步:“头儿,您稍安勿躁,您对秦掌柜的心意咱清楚得很,可是,您在这儿抱怨又有什么用?您就是把整座庙给拆了,秦掌柜还是不知道啊。”
“她哪是不知道?她分明是知道了,却视而不见!女人啊,就是不能宠,给她一根鸡毛,她便当令箭。”
“可是,您舍得不宠她么?您若是不给她鸡毛,只怕,明日就被她赶出客栈了。”
殿小二挥舞在半空的手僵了僵,虽想说些什么反驳,却又觉得杜潮守这小子说得有理,只得负气地坐到了一旁。
杜潮守仔细地观察着他的神色,不敢轻越雷池。月老庙附近多三姑六婆,端茶送饭,是非八卦可谓滔滔不绝,哪户人家门前的狗死了都可以叫她们议论上半日,更何况婚姻此等大事,是以秦瑶要成亲此事他亦略有耳闻,自然也听过那八个彪悍的“不嫁”。也难为了他的头儿,向来脾气便不大好,竟也忍了这么久。
时已夜深,月光柔和,初夏的风凉凉的,吹得江面上的月影一起一伏地荡漾着。街上的灯火大多数已经灭了,月老庙中的灯光却仍在闪烁,周围安静得很,听得见蚊子嗡嗡的叫声,就连二人细微的呼吸声也能听得到,月老像前的帷幔轻轻拂动着,仿佛月老就站在哪里,正无声地笑着他们。
杜潮守觉得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口:“头儿,秦掌柜的‘八不嫁’——说实话,咱佩服得五体投地,沾上那些人确实会麻烦不断呢。而且看她将官家朝廷之人放在第一位,想来是铁了心不随你啊。”
殿小二瞪了他一眼,他顿了一顿,迅速地端起他的茶咽了一口,又抓起一旁的扇子道:“不过头儿,在下倒觉得您这招以退为进用得极妙,只是用错了对象,若换了别个寻常的女子,只怕早就心软从了你了,但秦掌柜……头儿,您也知道,能让您看上的女子又岂能寻常呢?唉,这些由爱而生的恨啊,向来都比别的仇恨难办些,且不论结果如何,仅仅过程便已叫人纠结万分。”
杜潮守摇着扇子,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殿小二只是闷吭了一声,不作表态。
杜潮守却是纳闷了,他的头儿精于战术,在战场上英明果断,叱咤风云,怎么如今就变得这般优柔寡断了呢?想当初,头儿在京城里也是一名翩翩的佳公子,身边也不缺红颜知己,虽不至于掷果盈车,但也不知迷了多少女子的心思,听说还有过那么一段风流韵事,可眼下,怎么连一个秦掌柜也哄不住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他看看庙外风凉水冷月凄迷的景色,不禁慨叹万分,漫漫长夜,他便只能在这与头儿大眼瞪小眼了么?他还惦记着自己桌底下那些没数完的银子……
“那个,头……头儿,此事急不来,秦掌柜不是还没有嫁么?再说,哪怕是明天要上花轿了,我们不是还能从中作梗么。我看,您还是先回去吧。”
“不回去!”殿小二一甩头,为她铺床叠被,看似气还没消。
杜潮守扁扁嘴,使劲地摇了几下扇子,又道:“头儿,要不……小的最近赚了些银子,请你到附近的浴堂去泡一泡如何?就当是去去晦气。”
殿小二又把头拧回来,板着脸点了一下。杜潮守叹了一口气,弯腰抱起他心爱的钱瓮,极不情愿地步入了内堂,出来之时掂了掂腰间的钱袋,心疼得两眼泪汪汪。想当初,他贪这月老庙里的油水足,便主动向林校尉请缨,留在柳江城照应头儿,却不料,所谓的照应还包括了钱银上的照应。唉……
洗雨楼是柳江城中的一家老浴堂,前不久刚换了东家,新东家似乎是个有钱的主,大张旗鼓地修整了一翻,把浴堂装饰地美轮美奂,比隔壁街上的青楼还华丽,听说还请了许多年轻貌美的少年少女做浴侍,只怕也不是个纯净之地。
杜潮守捂着自己的钱袋慢吞吞都地跟在殿小二身后,额上的冷汗擦了一把又一把,所幸殿小二如今一副心思都摆在秦瑶身上,若不然,万一他看上了哪个楼子里的花魁,那才是真的要命。虽说殿小二不是没钱还他,可是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啊?万一他赖账……
“杜潮守!你在磨唧什么呢!”那厢殿小二已经走到了洗雨楼门前,不悦地回头看着他。
“是,来了。”杜潮守小跑着上前。
却见殿小二抱起胸,眉头皱了起来:“这就是你所谓的浴堂?”
杜潮守点点头,却又目露喜色,试探着问了一句:“头儿,您若是不喜欢,我们可以……”
殿小二嗤笑:“烟花之地!好!她这般待我,我也犯不着为她守身如玉,走!”说罢便大步流星地迈了进去。杜潮守看着他的背影脑袋耷拉了下去,一脸哀痛。
洗雨楼内灯火通明,雕栏红柱之间,轻纱飘然,越过厅堂,再走过一条短廊,便来到了洗浴之地,但见一扇扇碧纱厨间隔着一池池温水,烟雾迷蒙之间偶见细藕白莲,就着沥沥水声,编出一室旖旎,更显万种风情。
或许是夜太深的缘故,楼中的客人并不多,但殿小二岂愿下与人共浴之水?便不顾杜潮守的哀伤,硬是点了一个雅间。泡在温暖的水中,他紧绷已久的面容总算松动了些,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受了伤的右手不能碰水,只能在池边架着。
杜潮守心疼他的银子,死活也不肯下水,只闷闷地坐在一旁。
门吱嘎地一声开了,“枉我推心置腹,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走了进来,螓首微垂含羞答答地道:“爷儿,您的酒来了。”
她的声音轻轻柔柔的,拨人心弦,然而屋内的二人却都无动于衷,杜潮守依旧低着头闷闷不乐,殿小二蹙起了眉头,想起了秦瑶那些冷嘲热讽,又想到若秦瑶也这般待他——他不由地打了一个激灵,速速地让她放下酒便摆手示意她出去。
那姑娘的面容一滞,怏怏地走了出去。
片刻后,门再次开了,进来了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他低着头道:“爷儿,可要奴家为您捏捏肩膀。
殿小二把着酒杯正想浅酌,看到他这低眉顺目的模样,突然想起了秦瑶说的那句“把你卖到馆子去当小倌也可以么”,刚消减下去的怒火又开始燎蹿。“滚!”他一甩手,把杯子扔了出去。杯子啪地撞在了墙上,摔了个粉碎。那少年一惊,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殿小二的怒气却仍不能平伏,他本想来这里寻个宽心,不料心还不曾宽,怒火倒越来越盛了。
他揉了揉肩膀,忽觉近来身心都异常疲惫,只想好好地睡一觉,然而老天爷却似乎故意要跟他作对般,连泡个澡也不让他安生。
雅间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须臾之后,门又一次开了,一个发丝凌乱,衣衫不整的女子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
“爷儿,爷儿,救救奴家,他们……要逼奴家……”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说话断断续续。
殿小二一声不吭,但脸上早已乌云密布。
杜潮守似乎也从他的哀伤中惊醒过来了,看着殿小二的脸色战战兢兢地走到那女子身旁:“头儿,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土豪恶霸,逼良为娼之事寻常得很,偶尔遇上一两桩也……”
“当个土豪恶霸也不错,我要是土豪恶霸,第一时间便把那个狠心的掌柜给强抢回去!”哪用地着像现在这般只能靠自暴自弃来泄愤?殿小二凝视着那只肿得不像样的手,冷笑着,仿佛进入了冰火二重天的境界。
“这……”杜潮守看看那个仍在哭泣的女子,又看看殿小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殿小二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摆摆手:“行了行了,你带她出去吧。”
杜潮守得令,如获大赦般迅速地抱着那女子飞了出去。
周围终于安静了下来,殿小二倚着池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着自己的肿手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劈柴之时不觉得痛,如今却觉痛得锥心了。
他闭上眼休憩,而此时,雅间外却有一双眼睛,正透过窗眼窥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