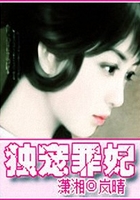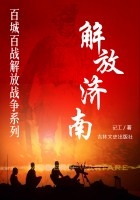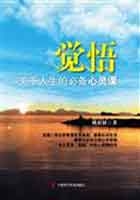南北朝时代,中国佛教学者关心成佛主体问题的同时,相应地心性问题也被提到佛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并且形成了佛性论、阿赖耶识说和真心本觉说三大心性论思潮。
佛性学说的探索与分歧
印度佛教的《大般涅盘经》是一部阐述佛性思想的主要经典,但在该经传入中国以前,东晋后期一些信奉般若学的重要佛教学者已经自发地产生了佛性思想。慧远的涅盘常住观念就和印度佛性常住思想相似。[注释:参见《释慧远传》,《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卷,360页上。]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叡在所作《喻疑》中说,他曾在长安亲自听过鸠摩罗什的答辩,鸠摩罗什也肯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是没有见到经文的根据,未能畅述。[注释:《喻疑》云:“什么时虽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而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或时有言:‘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业,众生有真性,虽未见其经证,明评量意,便为不乘。而亦曾问:‘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答言:‘《法华》开佛知见,一切亦可皆有为佛性。若有佛性,复何为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华》所明,明其唯有佛乘,无二无三,不明一切众生皆当作佛。皆当作佛,我未见之,亦不抑言无也。’若得闻此正言,真是会其心府,故知闻之必深信受。”(《出三藏集记》,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他着重阐发了涅盘佛性说,开创了佛教一代新风。随着《大般涅般经》的译出和竺道生的倡导,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众多的涅盘师说。这些师说都以“佛性”理论为重心,对于成佛的原因和根据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佛笥理论空前繁荣的局面。对佛性的探讨主要围绕这样三个问题:(1)什么是佛性义?即佛性的意义是什么?(2)众生是否都具有佛性?(3)佛性是本来具有,还是后天始有?以下将探讨的情况略加叙述。
一、佛性的意义
隋代吉藏在《大乘玄论》卷3中称,隋前论及佛性的有十一家,又吉藏的同门慧均在《大乘四论玄义》卷7则称论佛性有根本说三家、枝末说十家,合为十三家。[注释:详见《续藏经》第1辑第74套第1册,46~47页。]此外还有三家说、六师说等。这些说法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今以吉藏归纳的说法为主[注释:吉藏所说,见《大正藏》第45卷,35页中、下。],分别给予评介。
(1)以众生为正因佛性。“正因”指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相当于主因。因据《大般涅盘经》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说众生是正因佛性。吉藏所说的佛性都是指正因佛性。相对于正因的是缘因,缘因即次要原因,外在条件、助因。《涅盘经》认为,众里的布施、持戒等种种修持都是缘因。
(2)以六法为佛性。六法是指色、受、想、行、识五阴(实)及由其构成的假名之人(假)。实际上六法就是指众生中的人。以六法为佛性也就是以人为佛性。
(3)以心(识)为佛性。《涅盘经》认为,“心识”是“异乎木石无情之物”,凡有心(识)的,必能得无上菩提。所以说心(识)即佛性。众生和无情识的木石不同,是有心(识)的,众生的精神实体及其作用是成佛的主因。
(4)以冥传不朽为佛性。“冥传不朽”指“识神”而言。识神就是众生不灭的精神、灵魂。识神是轮回的主体,是不灭的。这种不灭的识神也就是成佛的正因,就是佛性。
(5)以避苦求乐为佛性。这是由心(识)为佛性的思想而来。心有避苦求乐的本性和作用。心在轮回流转中不断产生厌恶痛苦,乐求涅盘的作用,这种追求就是佛性。
(6)以真神为佛性。真神是指识神的本体而言,真神即成佛的基础。
(7)以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为佛性。自性清净心同如来藏。此说认为众生欲求出世解脱,证得涅盘,必须依靠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所以自性清净心便是佛性。
(8)以当果为佛性。当,当来,当有。当果即当有佛果的意思。这是从众生将来可以成佛的角度讲佛性。
(9)以得佛之理为佛性。这是认为一切众生本有得佛之理,是为佛性。
(10)以真如为佛性。真如亦即真如佛理,是众生具有的本性清净的理体。
(11)以第一义空为佛性。第一义是相对于世俗常识而言,是指最殊胜的义理。第一义空是以事物的实相,乃至终极的涅盘为空。此为北地摩诃衍师的主张。
吉藏还把上述十一家分为三类:一、二两家是以众生或人为佛性。第三家至第七家是以心识为佛性。第八至第十一家是以理为佛性。这三类佛性说的立论、视角显然不同,第一类说法除与无情识的木石加以区别外,是直接以成佛的主体为佛性,失之空泛;但以众生或人为佛性的观点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传统文化立场,对后来佛教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说法是分别从主观(心)和客观(理,即外境方面)立论,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在探究佛性问题上的分歧和困惑。佛性究竟是指众生,还是指心体,或是指理,这三种说法实有很大差异。这些不同的说法也给后来中国佛教宗派的分野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类说法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佛教学者的创造性及其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密切关联。这可分别以竺道生和梁武帝萧衍的佛性义为代表。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率先阐扬佛性论者。他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魏晋玄学的体用观念影响下,把佛教般若实相本体论和涅盘佛性心性论结合起来,强调实相本体就是佛身,众生体证返归实相就是佛;而实相本体也存在于众生的心性(本性)之中,此即佛性,是众生冥符实相、成就佛果的内在根据。道生所讲佛性的主要涵义有三:一是善情性、本性。他说:“善性者,理妙为善,反本为性也。”[注释:《大般涅盘经解》卷51,《大正藏》第37卷,531页下。]意思是说,理妙返本就是善性。这种善性又不同于通常所讲的善,而是一种所谓了知照见(神秘直觉)一切事物实相的智慧。这种善性也是本性,是本来具有的。二是理。“理”即所谓符合事物实相的真理,亦即常住不灭的法性本体。道生说:“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注释:《大般涅盘经》卷54,《大正藏〉第37卷,547页下。]佛因也即佛性。三是法,自然。道生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注释:同上书,549页上、中。]法,事物。体悟一切事物的真实本相,冥合无生无灭的自然状态,就是佛,所以,所以法是佛性,自然是佛性。所谓成佛,就是要达到自我与万物等同忘却,万有与空无齐一无别的境界。竺道生说:“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求之也。”[注释:《注维摩诘经》卷7,《大正藏》第38卷,392页上。]“以体法为佛,不可离法有佛也。”[注释:《注维摩诘经》卷8,《大正藏》第38卷,398页上。]认为真理湛然不变,众生若悟见真理,人心真性也就自然流畅,如此在生死中当下就可以觉悟成佛,所以涅盘生死不二,两者并无二致,佛无净土,众生是佛,从而客观上把涅盘定位为众生的主观理想精神境界,破除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由上可见,竺道生所谓的佛性是以“主”“客”相结合的角度界说的,佛性既是宇宙万物的实相本体,又是众生悟证实相本体的善性、慧解。在中国思想史上,竺道生的佛性论既否定了以般若学的“空”怀疑涅盘学的“有”的观点,也否定了把佛性常住与灵魂不灭相混同的观点。尤为重要的是,竺道生的佛性论既和般若实相本体相结合,又吸取中国固有哲学的本体观念,把心性论和本体论相结合而纳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框架之中,为从心性论向佛性论打开思想通道;又将佛教心性论、佛性论植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之中,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吉藏所列的十一家佛性论中,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是第六家,即由染武帝主唱的真神佛性说。梁武帝撰有《立神明成佛义记》(见《弘明集》卷9)等文,集中阐发此说。所谓真神,也称神明,是众生异于木石的本性,也就是精神。梁武帝运用玄学的体用观念来阐释精神,认为精神具有性和用两个方面,神的作用是有兴有废的,神的本性是恒常不灭的。这个不灭的神的本性,就是佛性,就是成佛的主因和主体。十分明显,梁武帝所讲的佛性,实际上就是不灭的灵魂。可以说,梁武帝是用中国固有的灵魂观念,去阐明佛教的成佛学说, 把中国的神不灭论观念纳入于成佛学说的思维框架之中,并与大乘佛教的佛性论相融合,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印度早期佛教的面目。梁武帝所讲的神,既是众生报应轮回的主体,又是超越轮回成佛的主体,也就是用不灭的神把众生来世的两种不同趋势、归向给统一的主体性说明。应当说,这是中国佛教的众生主体转化说提供了较鲜明而周密的理论解说,因而一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支柱。
二、佛性的有无
佛性是众生普遍具有,还是仅部分众生具有,这在佛教史上被归纳为性有还是性无的问题,亦即佛性的普遍性问题。在佛教内部,它引起的争论是长期的。竺道生时,法显(?—约422)译出6卷本《大般泥洹经》。经中认为“一阐提”即是不具信心、断了善根、没有佛性的人,不能成佛。这种观点成为当时佛教界的共识。竺道生根据中国人得意忘象忘言的思想方法,批评了当时的佛教教条主义者,并且不拘文句,孤明先发,大胆提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的观点。竺道生的说法独见忤众,当即遭到僧众的诘难,并受到逐出所住寺庙的处分。及至后来,昙无谶译出大本40卷《大般涅盘经》,果然称“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竺道生的主张又受到僧众的普遍赞扬。
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即一切众生无一例外地具有佛性的观点,是他的佛性理论的彻底性的表现。他根据对般若实相学和涅盘佛性学的深入研究,独创性地提出了“佛性我”的观念,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种实在自体。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善于运用中国固有文化观念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据日本沙门宗法师撰《一乘佛性慧日抄》引《名僧传》云:
生(竺道生)曰:“禀气二仪者,皆是涅盘正因。三界受生,盖惟惑果。阐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度未尽耳。”[注释:《大正藏》第70卷,173页下。]
“二仪”,阴阳,“禀气二仪者”,指众生。“此经”,指6卷《大般泥洹经》。竺道生吸取中国的禀气论来支持佛性论和“一阐提”人也有佛性的观点,公开批评《大般泥洹经》理论的不彻底性,反映了中印异质思想文化的摩擦和交汇。在竺道生看来,凡是含生之类,即“禀气二仪”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具有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据。“一阐提者,不具信根,虽断善犹有佛性事。”[注释:《名僧传抄》附《名僧传说处》,《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7套第1册,15页。]认为即使是断了善根善行的人,也还存在成佛的深层根据,也能修持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注释:《妙法莲华经疏》,《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23套第4册,408页。]
竺道生基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厚素养和对印度佛教文化的独到理解,提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即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的观点在中国佛教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关系到人的本性是否同一,也关系到恶人能否转化成佛的问题。对此,竺道生都予以肯定的说明,强调人人都有同一的佛性,恶人同样可以成佛。这种观点不仅符合佛教的发展需要和根本利益,也符合世俗社会不同人群的心理需要和宗教愿望。正是竺道生的佛性论,极大地推动了外来的佛教在中国走上以心性论为重心的新途径,并在尔后的佛教心性论发展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一直成为影响最大的佛教主流的基本观点。
三、佛性的本有始有
自大本《大般涅盘经》流传以来,佛教界普遍认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此后,又出现了佛性本有、始有之争。本有是说众生本来就有佛性,始有是说众生经过修持当有佛性,也称“当果”,意谓因有当果。这一关于佛性形成的争论涉及了佛性的释名定义、先后时限以及由此产生的修持方法、途径步骤等一系列问题,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争论持续数百年,迄至唐代仍无定说。玄奘西行印度求法的主要动机之一,也就是为了寻求这一疑难问题的答案。
佛性本有始有的对立,也和竺道生的《佛性当有论》直接相关。有的学者引申此论,立因有当果之说。此说主张由因推定将来有可能成佛的当果佛性。至于佛性是本有,还是始有,并没有直接论及。后人又据当果佛性说立佛性始有义,并把竺道生的主张归结为始有说。竺道生的《佛性当有论》已佚失,此处“当有”两字究竟作合解释也难以考辨。根据竺道生把佛性等同于善性、理、理、法、自然等范畴,认为佛性常存不灭,以及强调“一阐提”人虽断善根仍有佛性思想来看,应当说,竺道生是佛性本有论者。再联系竺道生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当有”似乎是针对那种认为一部分人不具有佛性的观点,而强调一切众生都当有佛性,都必能成佛,并非是就成就佛果的时间而言始有。
南北朝时期持本有说或始有说的佛教代表人物,史载不一。这里我们只着重论述两说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区别。本有说的重要立论有三:一是生死中本有真神之性,二是众生本有成佛之理,三是众生具有的本性。此三者都具有实体、本体的意义,其特征是天然的,非造作的,常住不断的。佛典常以贫女宝藏和雪山香药等比喻,说贫女家有黄金宝藏,雪山里有香药,只是是否被发掘或发现,来说明众生本来具有佛性。
始有说的重要立论是当果说,是从成就佛果的角度说佛性。具体地说,一是众生本来杂染不净,具有清净佛性是后来的事,此为始所具有。二是与上一点密切相关,认为众生毕竟还不是佛,还没有成就佛果,只是就未来必得佛果说有佛性,众生的佛性是始有的。持始有论者常以“卖草值,不索驹值”(卖雌马不索将来可能下驹的价钱)和麻非是油等比喻来说明因不同于果,佛性是如有。可以这样说,本有始有两说对于佛性范畴内涵的界说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两者对于佛性的立论角度。本有论侧重从众生成佛的角度立论,强调众生悉具正因佛性。而始有论侧重从众生成佛的正果角度立论,强调众生只有达到成佛果位时才有佛性。本有始有两说的对立也对众生本体、本性的看法不同有关。凡以净识为众生本体的多持本有说,凡以染净合识为本体的,则多持始有说。本有论与实有论的对立,不仅表现出对佛性与众生关系的不同看法,而且也引发出修持实践方式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