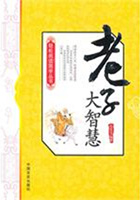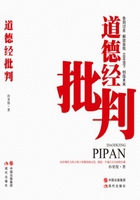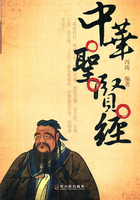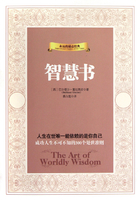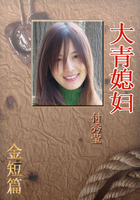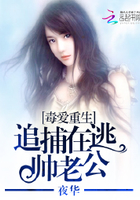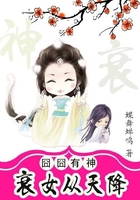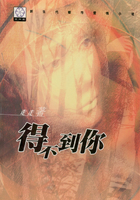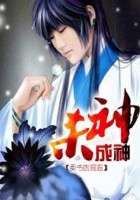佛教心性论是着重论述人心的本质,心性的作用、意义以及心与性的关系的学说。从根本上
说,就是探讨人存在的根本原理——人是什么,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是怎样的理论。换句话说,这种探讨人的本来状态和应有状态的理论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完善和显现人的生命本性,开发和实现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可归结为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即人性论——人的心性论。
佛教教义最关切的问题是寻找人类受苦的根源以及解脱痛苦的方法和途径,而对解脱生死痛苦问题的探讨,又始终是与主体的精神世界(知、情、意)的本性即心性问题相关联的,一直是与升华人的本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境界相关联的。由此,佛教对心性的意义,不仅仅只从它与烦恼的关系上去立论,而且更从具备所谓成佛的因素方面去阐发。一般地说,佛教心性论具有心理自然、道德修养、宗教情感、宗教实践和众生乃至万物本原等多个层面的涵义,涉及了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主体论、价值论、实践论、境界论和本体论等广泛领域,是佛教学说,尤其是佛教主体价值论的根本内容。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佛教心性论实质上是一种人在主客观世界互动中追求自觉和自由的学说。这种学说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等因素制约下具有鲜明的特色,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人在宇宙中的自觉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对主观世界的开拓和完善,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和觉悟等方面的思维成果,蕴含着人类的深邃智慧,值得我们开发、借鉴。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的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编以十四章,约为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对中国佛教的心性论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全编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自南北朝以来历代佛教重要派别的心性论,以及佛教与儒家、道家在心性论思想上的互动互补。全编论述的中心是南北朝以来历代佛教重要派别的心性思想,共设十章,同时也重视佛与儒、道心性思想互动的探讨。关于本编的中心内容,即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心性论,其重点是论述禅宗的心性论,尤其是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的心性论和慧能以后的荷泽禅、石头禅与洪州禅三系的心性思想,之所以如此,是由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所决定的。同时,本编也重视对天台宗和华严宗的心性思想的论述,尽力揭示两宗的丰富而有特色的心性论内涵。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印度佛教心性思想的继承、调适和发展,在论述中国佛教心性论前,有必要简要地追溯一下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本编开篇即设“印度佛教心性论思想概述”专章,论述了印度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如来藏系与瑜伽行派的心性思想,着重简介心识、心性、菩提心、如来藏、佛性和种性等概念的意蕴,以及整个心性思想的历史演变,并指出:
印度佛教心性思想的主流是心性清净说,此说自小乘佛教倡导以来,后经大乘佛教,更发展为如来藏说和佛性说,始终是印度佛教心性论的主导思想。
笔者认为,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心性论思想,一个重要的途径即是找出心性论体系的范畴,论述其内涵与实质,并揭示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又因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内涵十分丰富,本书采用的又是以历史为线索,依次论述佛教各重要流派心性论的方式,为此,我们先从总体上论述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体系,而设“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专章。此章在界定心与性的关系之后,着重从心与性两方面分别作内在与外在的展开。在心的方面,着重论述真心与妄心、心与意识、心与神、心与物、心与理、心与佛的思想关联。在性的方面,着重论述心性与法性,凡性与佛性,性净与性觉,性善与性恶,性有与性无,性本有与性始有,性的体、相、用,性与情,性与理的思想关联。本章还指出中国佛教心性论范畴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结构功能系统,并尽力总结这一范畴体系的特性以及不同范畴之间关系的类型。
关于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内容,本编分三个部分来论述:一是南北朝时代的心性论,二是天台、华严、三论、唯识和密诸宗的心性论,三是禅宗的心性论。南北朝时代,随着中国佛教学者对成佛主体问题的日益关切,心性问题也相应地被提到佛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并形成了佛性论、阿赖耶识说和真心本觉说三大心性论思潮。在佛性论方面,主要是探讨佛性的意义,众生是否都有佛性,佛性是先天而有还是后天始有三个问题。与佛性问题探讨相关,关于阿赖耶识是真识还是妄识的问题,也成为地论师和摄论师争论的焦点。最后,本书认为《大乘起信论》从禅观的角度总结了有关心性异说,提出了众生成佛根源的真心本觉说,和径直以发明、显现真心本觉为修持成佛的途径,影响极为深广。
天台宗人沿着万法与真理不分离、万法与心性不分离的理路,把法性、真理与佛性三者等同起来,提出了“三法无差”、“三因佛性”、“性具善恶”、“中道佛性”以及“无情有性”等一系列心性论命题,构成了广博丰富的心性论思想体系。本编设专章论述了天台宗的心性论思想,在比较全面地论述相关心性问题时,又着重从多方面论述该宗的性具善恶说。笔者认为,从心性论的视角而言,“性恶”、“性毒”之说,是天台宗的极具特色也是颇具理论意义的心性思想。
本编设专章介绍华严宗以佛性为众生本来具有的自我本性的心性论,着重分析和论述此宗心性论的主要思想“自性—佛性”说的基本特点:清净性和圆明性。清净性指佛性是至纯至善的,无染无恶的;圆明性指佛性的本性遍照一切,无不光明。此说构成为华严宗有别于其他宗派心性论的重要思想特色。
本编以一章的篇幅,简要叙述三论宗、唯识宗和密宗的心性论的主要论点。先是介绍三论宗人在总结和批判以往学者的种种佛性论观点的基础上,所阐扬的中道佛性论;次是简述法相唯识宗的三类阐提说和佛性说;再是简述密宗的“本不生即心实际”说。
如上述所指出的,本编的重点是论述禅宗的心性论,为此我们以慧能为界碑,设两章分别追述慧能前禅宗的心性思想和慧能的心性思想,随后设四章着重论述慧能以后衍化出来的禅宗重要流派的心性思想。在追述慧能前禅师的心性思想之前,我们又特设一节来说明心性论是禅宗的理论要旨。文中从禅宗以参究的方法来彻见心性本原的主旨、禅师们的大量禅法著作都以见性成佛为目的,以及禅宗思想实质是从人的心性方面探求生命自觉、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进而凸现出心性论是禅修方法的理论基础。由此还认为,不了解禅宗的心性论,就无法了解禅师的禅法,也就无从了解禅宗本身。随后依次简述菩提达摩、慧可和僧璨的真性与自觉说,道信和弘忍的念佛心与本真心思想,牛头法融的无心与妄情说,以及神秀的染净二心说,从而为论述慧能的心性论提供重要的思想背景。
对于慧能的心性论,笔者着重通过对《坛经》的心与性的两个基本概念以及相关命题来研析。文中分别对心、自心、本心与自本心,对性、自性、本性与自本性相互关系作了比较详密的分析,并指出《坛经》是主张心与性同一、自心与自性同一、本心与本性同一的。最后论述了《坛经》怎样把自心、自性与佛性的关系打通,进而又与佛的关系打通,并在自心是佛的基础上,提出本性顿悟成佛的学说。
荷泽宗的心性论主要是灵知说,本编设专章加以论述。文中着重揭示荷泽宗灵知说的三层涵义:空寂之知——空寂之心的觉知作用;自然之知——不藉功用、自然而有的智慧;无住之知——无所依托的自由活动的心灵。灵知也称为众生的本原清净心,灵知说是对人类的心性本体的深入探究。此外,还论述了荷泽宗人的这样说法:灵知就是佛智,而佛智作为众生的本性,就是佛性。并指出,宗密以心性说为基准,全面地分析了禅宗三大流派的心性思想,极富有总结性的意义。
本编设专章对石头宗系统的心性思想,尤其是其核心心性思想和重要的心性命题作一集中论述。此宗的中心思想是以“灵源”即心源为众生和万物的根源,认为灵源是皎洁圆满的,是不同于日常行为动作,排除一切妄念偏见的;又以此灵源去统一理与事,本与末的关系,进而把握宇宙与人生的真实,见道而觉悟。文中还分析了石头宗宣扬的“无心合道”说,此说主张排除分别心,无心于物,不执著物,强调只有无心才能契合道;有的禅师还反对禅门中的非心非佛、非理非事的说法,表现出与洪州宗门风的某些不同。
本编设两章论述洪州宗以及由其衍化而出的临济宗的心性思想。洪州宗心性论的主要命题是“平常心是道”,所谓平常心即众生本来具有的不矫揉造作、不作分别的本心,也即众生的日常现实心。在此宗人看来,如此的平常心就是佛道。这是强调众生的日常行事都是真心的体现和表露,见闻觉知虽不是真心,但真心又不离见闻觉知,众生必须从见闻觉知体悟本心,其他途径是没有的。由此也表现出了此宗重视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以及更为主体化、生活化和行为化的思想特征。洪州宗人很重视心与佛的关系,提出了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说,此两说表面看来对立,实则是以表诠和遮诠的不同方式来说明不同的开导方法和禅修境界,其思想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此宗也是一面宣扬“心即是佛”说,反对向外追求;一面又大力宣传“无心是道”说,并把二者统一起来,强调“无心”是灭尽一切分别情识,对凡圣不作分别取舍,由此真心本体显露,也就进入悟境。此外,文中还指出,洪州宗人对有情与无情、有性与无性的意义也作出了新的诠释,从而使以往关于有情与无情、有无佛性的意义有了新的发展。
关于临济宗的心性论,我们着重论述的是临济宗人在平常心是道和无心是道等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否定外在于生命、外在于心的超越理想,大力肯定现实的人和人心的无限价值,强调禅的真正旨趣内在于众生的生命之中,必须向内自省,开发“活泼泼地”创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表现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文中指出,临济宗高扬一念心清净就是佛,并强调众生要有高度的自信心,坚信自身就是佛。还分析了临济宗提出的“无事是贵人”的命题,临济宗认为,“无事”也即没有人间造作的事是人的真正本质,“无事人”就是贵人,就是佛。临济宗杨岐派传人大慧宗杲提出的菩提心即忠义心的说法,如果结合南宋时代抗金派与投降派斗争的背景来看,此说的时代气息是尤为浓厚的。
本编重视论述佛教与儒家、道家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关系,故设两章论述之。在“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动”专章中,认为儒、佛的思想主旨决定了心性论必然成为两者成就理想人格的思想基础,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差异又为双方的互动提供了可能,而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局限又决定了两者各自思想发展的需要,并且强调指出,儒、佛在互相碰撞、冲突、贯通、融会的过程中,在心性思想上寻觅到了主要契合点。本章在简述儒家的心性思想的历史演变后,着重论述儒、佛心性论互动的四个基本方面:儒、佛的学术思想重心分别向性命之学或佛性论推进的轨迹;促进佛教突出自心的地位、作用和儒家确立心性本体论;广泛地调整、补充、丰富两者心性论的思想内涵,且都增添了新的内容;彼此互相吸取、融摄对方的心性修养方式方法。由此儒、佛心性论在历史上一度共同成为人文思想的基石,并在伦理道德和人格培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道、佛心性思想互动”专章里,我们着重从道家的道、自然、无为而无不为、静观、得意忘言思想对佛教的影响角度,强调道家为佛教尤其是为禅宗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借鉴;又从佛教的轮回果报、万法皆空、心生万法、明心见性思想对道教的影响角度,强调佛教对道教在转变对人的形体、生命、人生理想的看法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之转向心性修养。
本编还设“余论”两篇,其一是“心性论:中印佛教思想的重要同异点”,着重归纳、论述中印佛教在心性论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强调弘扬如来藏思想和佛性说是两者的最大共同点,而提倡“平常心是道”、“本觉”说和返本归源修持方式是在心性论上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大差异点。其二是从儒、佛、道三教在心性思想上的整体互动的角度,提出了“心性论:儒、道、佛三教哲学的主要契合点”的论说,并对形成这种契合的文化根据与历史根据作了纵向横向结合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