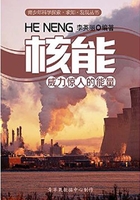抱着那人蹭了许久的鼻涕眼泪,直到肚子“咕噜”一声,饥饿逐渐上升代替了伤心的存在感时,我才慢慢松开了他。我抽噎两下,又随手抓来他的蓝布袖子胡乱擦着脸。
“轻点,万勿擦坏了。”他阻住我的手,自袖内取出方白软的帕子,捧住我的脸一点一点轻拭着。
我一听更觉气闷,赌气地瞪过去恨恨道:“坏就坏呗,反正都见不得人了。”
“好好的样貌哪里见不得人了?”他抿着嘴笑看我,捏了捏我的腮:“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回去做饭了。”
“你你你,怎么又是你!”我回过神来来颤着手指他,又凑上去左右看个仔细:“这里你也能寻来,说!容竹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奇怪了,为何我狼狈不堪时总是遇到他?这也忒巧了些吧我狐疑地瞅着他,是个凡人没错啊,一个凡人对于我这一穷二白的落魄户有什么图谋的?
他弯着眉眼看了看我,又转头看了看四周,坦然而又疑惑道:“将才你心神不宁出了村子,一路跌跌撞撞到了这荒郊野外。紧接着便晕在了地上,我这才扶起了你。这里怎么不能来了?”
“啊?”我茫然地随他的视线看去,果真是一处野林清溪边上。啾啾鸟鸣,皑皑霜雪,潺潺冷溪冲击着圆滑的石头发出清灵的声响。暮风缭绕着悠扬的牧笛音兜转着钻进黑压压的林子里,掀起一脉脉碎碎的细音。
远方山脚下的隐约可见一缕轻淡炊烟袅袅直上,似乎都能触到灶火间里的喧闹和温暖。
一想到这,腹间的空荡荡感更甚了,我琢磨着难道经过那千年龙息的一番摧残,我这副万把年来的老骨头也经不起饿了?
正当我在为八荒界门的飘忽性愣神的功夫,容竹已自地上起了身,将粘在袍上的枯草扫去,弯下身将手伸来:“来,我们回家。”
容竹的手干净细白,就是极瘦,青筋凸出,骨节分明。他见我直愣愣地不答话也不动作,又好脾气地重复道:“阿罗,我们回家。”
我刚刚波平泪止的眼眶又一热,生生的疼。我压下那窝心的酸楚,将手搭了上去,顺便嘟哝道:“我要吃鸡吃鸭。”
他携着我缓步朝村落走去,脚下绵厚的积雪咯吱咯吱作着响:“小生乃一介穷白书生,靠教书和出卖书画度日。阿罗要吃鸡鸭,恐得等小生攒够了银子。”
“你真坦白。”我抽着嘴角道。
“贫何耻,富何荣?不过身外之物,生死之后比黄土还足。”他微微笑道一派潇然。
“书生你真是颇有慧根,颇有慧根!”我诚心赞道,一阵冷风吹过我缩了缩脖子,扇了扇鼻尖奇怪道:“说来你有没有闻到股血腥气儿啊?”
他步子一顿,从容解下身上棉斗篷披到我肩上,将我团团裹住,又将领子掩得紧了紧,他低着眉笃定道:“没有。”转而又补充道:“大约是阿罗饿极已生了幻念。”
“……”我哦了一声,继续踩着雪蹒跚着向前去。也不知是为何,这心口处自打我魂归后就作着一线的痛,本想运起仙力探一探,谁料一动仙力那痛就使了劲往里钻,似要生生在我心脏处钻了个洞来。我余了一背的涔涔冷汗,暂且不与多想。
忍着痛缩头缩脑走了没几步,身后的林子里“嘎吱”一声响,我猛地止住了步子:“这实实在在的声音难道也是我饿出的幻觉?”
容竹笼在袖里的手伸了出来,轻握起我的手忧虑地看着我:“恐怕也是。”他的掌心干燥而暖和,似是有股暖意自他覆在我手背上的手心里传出,一直流入到心里,无端地便祛了几分寒意。
要么是我饿晕了头,要么就是这书生失心疯了。但紧接着林间又传来沙沙磨蹭的声音,如同有什么顺着雪面蜿蜒爬行,时不时还有骨肢折裂的脆响。隐遁在腰间的纯均剑逐渐生热,发出如振翼般嗡嗡的剑鸣。
容竹淡然瞟了一眼阴暗、枯叶飘零的森林,将盯着那的我往他身边拉拉,压低着嗓音道:“听村里人言,这附近林子里近来多有走兽出来觅食。这荒冬腊月的,想来那走兽也被饿得极为凶恶,这天色已晚,你我还是快些离开为好。”他柔着嗓音哄道:“阿罗,乖”
我脸黑了黑,论年岁我不知比这凡间书呆子长了多少辈了,怎么他对我也像对个小孩子一样。又警惕地往那林子里瞧了瞧,却再未听它弄出什么响动来。而今我有伤在身,若是凡间猛兽倒还好,假使碰上了魔族就怕力不从心了。
略一衡量,我觉得还是快些离开为好。你瞧,猛兽伤人那只能说那人年寿尽了,该魂归地府了;又若为魔族的话,那自有镇守一方的人间卫道士来收掇他们。至于我这个不学无术,闲散的编外神仙还是先料理好自己为上
阿爹说过,武罗我将自己看管好,就是造福苍生,我自当遵他老人家教训。我说阿爹,你又云游到何方去了,你亲亲女儿被你遗忘地好生干净!
此地万万不能再待下去,否则容竹没失心疯,神叨叨的我就要被他认为是失心疯了,太有损我的形象了。
就在我随他离去时,我恍惚又发了幻觉,听到长长地一声舒气儿声。
“哎哟,这就是容先生家的媳妇儿吧。瞧这水灵灵的样貌!”一进村,我和容竹就被一群三姑六婆七大爷给层层围观了。
我甚是茫然地被一位大婶亲热地拉扯住左右丈量了一番,吐出一句差点震出我魂魄的话来:“小媳妇儿这身子骨看来是因常年病着瘦弱了些,可不好生养啊。婶儿那里还有只下蛋的母鸡,明儿送过来,可得好好补一补。”
我面无表情地将容竹定定看着,眼里的刀锋是刷刷直飞。他正弯腰应对着不知哪里蹿出来的几个孩童,听闻此话回过头来,眼里的笑意十分狡黠。
“去去去,大伙都散了吧。”一个大爷衔着烟杆,吐出口白眼圈,叉腰道:“没看容夫人才醒转过来,别耽搁人家小两口热络感情。”
心尖不再痛了,我的脑袋开始作痛了。
我不动声色,往容竹那儿挪了几步,狠狠踩了下去又碾了碾。叫你无中生有,叫你胆大包天,叫你毁我清誉!
他吃痛放开了正欲扑腾到他身上的一个小女娃,神色不变地挨近我,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发:“阿罗莫吃醋。”
我脑袋和心尖一起抽啊抽的痛了。
等围观群众作鸟兽散去,我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一人直大步走上前。他在我身后喊了声,我没搭理,他又喊了声,我回过头去嚷嚷道:“烦不烦!再啰嗦,我就阉了你!”
他用力咳了几声,脸上泛起了抹白,歇了歇气他缓缓道:“你认识回家的路吗?”
我确然不认识,本来我想一气之下就此离开。可是看着他嘴角边如和风般的笑意,和他说的那个词,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不出狠话来。回家,在这冰天雪地里多么温馨的两个字。我原本有婆家和娘家,而今那婆家里再没有了我的位置,娘家我暂时是也回不去了,天地之大,我头一次体悟到了孤独二字。
就算他有所图,我现下最值钱的就是这条命了,以他的本事想图也是图不来的。既然他主动送上屋子来给我避这腊冬的凄风冷雪,以供我歇脚,我何不收纳呢?我是个明事理而体贴的人,万不能伤了书生他那颗乐于助人的心呐。
容竹的小院在这村落的东头一棵老柳树下。墙垣低矮,枯细的褐色柳枝半搭半垂在上面,掩着门扉。
我和容竹刚一走近,手还没搭上门,“轰”地一声,伴着一股焦味,一个白绒绒的团子自天而降,直直冲着我落下,我下意识伸手接住。
“小兔崽子!今儿我不把你剥皮烤了!”气急败坏的沈红衣黑着如锅底的脸踹开门,手里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三寸来长的银针咬牙切齿道。
尾巴卷在我胳膊上,在我怀里磨来蹭去的小狐狸斜睨了他一眼,又狠狠瞪了瞪身边的容竹。哼了一声,继续极为亲昵地蹭着。
我握起他三条尾巴,将那白团子倒提了起来观察了番,失声道:“留欢?”
小狐狸黑亮黑亮的眼睛神采奕奕地看着我,软软叫了一声:“汪”
我手一抖,“噗”它四仰八叉地掉到了雪地里,白绒绒地一团扑在雪里几乎融为了一体。
我呐呐对着怒发冲冠的沈红衣和好奇的书生道:“这个,这个,他是我的人”
哦,不,他是我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