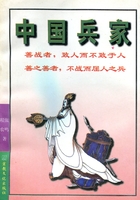没想到,旁人非但管不来,竟也羡慕不来——当然是羡慕那厮!
上海人说“烫得平,兜得转”——以他这样的质素和品行,竟也能娶到菲菲这等温温柔柔、秀外慧中的女子,还这么死心踏地地跟着他,真得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
“喂,到底怎么样?你去不去?”MAY问我。
“去哪里吃饭?她家吗?”
“是吧,听说她老公下厨,手艺还一流呢!”
说完这话,我听到MAY从鼻缝里哼了一声出来,“怎么样?去不去?”
我打了个哈欠。“不想去。”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
“我去不去本来就无所谓。不过你可是她的老乡兼昔日同窗。她新婚燕尔,首度邀请你去她家中做客,你却拒绝——似乎不太好吧?”
“那你都不去了,我一个人待在那儿干什么?菲菲已经是有正主的人了,跟我们又不是一国的,至于那个猪头——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那么……”我沉吟了一下,“我就当给你面子,陪你去好了!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有。也别多说话。反正吃完饭就走,行吗?”
“好吧……”MAY似乎也是不情不愿的,“我就搞不懂那个菲菲!原来家乡有一个家境那么好,人品那么好的男孩子等着娶她,死活就是不要!好像跑到上海来了,就非得嫁个上海人似的,有什么意思?——挑来挑去,还不是挑了一头外地过来的猪!”
“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我笑,“那头外地过来的猪可是有上海市身份证的,好坏也算个知青子女。而且现在把房子一买,怎么也算是在上海生根落户了。比起我们这些漂来荡去的人,可强多了!”
“可我认为找老公和扎根是两码事。扎根可以靠自己。找老公就一定得找优秀的、人品好的,否则怎么靠?靠不牢!”
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心里升了上来。冰凉的,弥漫的,无声的。像雾气,又仿佛是一股蜿蜒向上的风。
“也许是因为靠自己扎根太累、太痛了,所以有些人放弃了。”我轻轻吐出一口气,“成家立室也是扎根的一部分。只是这个步骤进行的早晚和对象的问题。如果靠自己解决不了面前的课题,那就找个上海人出来嫁了。那么个人的扎根问题就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上海家庭的生活水平问题。而这个问题因为有了多一个人分担,比起所谓扎根问题来,自然就显得容易多了。”
“唉!嫁个上海人!×!”
5
在菲菲家中以亲切友好的和平气氛吃完晚餐,我们并没有实现立刻就走的誓言——吃饱了就溜是白眼儿狼的做法——我们还没有那么不讲道义。至少,不能对菲菲不讲道义。
我们选择留了下来。
陪菲菲吃吃水果、聊聊天。参观了他们两室一厅的新居。
据说房子的首付是双方父母一家一半掏的。至于供房嘛,当然就是男人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女人而言,家庭生活最实惠的地方就是转嫁危机——婚前虽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意味着得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一旦结了婚,自然就成了男人赚钱养家,女人嘛——负责管钱就好!
新房装修得尚算清爽。
平民家庭的装修,没资本标新立异。反正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看着不奇怪就好了。
唯一让我和MAY有些妒嫉的是那张粉白色的公主床!
圆顶的粉白色碎花纱帐从房顶上悬挂下来,像梦的衣角包裹住整张床。
床单和被套、枕套也都是粉白色,镶着同色系的蕾丝花边。床的骨架是镀成金色的钢架。床罩层层叠叠的花边直垂到地上去,遮住了它的脚——一切都是那样曼妙而完美,恍如一个梦境!
一个只属于公主的,粉色的梦。
MAY情不自禁地吹了声口哨,“我都要开始嫉妒你了!要是我能每天睡在这样一张床上,一定天天美梦做得都不愿醒过来!”
“你不需要,”我斜眼瞄她,“你现在也一样天天睡得不想醒过来!”
“去你的!”MAY捶了我一拳。
“这床可贵呢,要一万多块!”菲菲笑盈盈地开口,“当初也是我死活要买,才咬咬牙买下来的。”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脸上有某种幸福的光泽,温和而快乐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这张婚纱照很漂亮!”我指着床头正上方悬挂着的那张硕大无比的婚纱照——女人都愿意别人夸自己漂亮。尤其是当新娘子的时候。
果然,菲菲立刻笑逐颜开。
“我那儿还有好多婚纱照呢,拿过来给你们看!”
菲菲走过去,从床头柜里拿出来一大摞照相本。于是,我们就坐了下来,欢欢喜喜地翻看照相本。
一面看还一面啧啧地惊叹。真漂亮,真不赖,这张照得好,那张照得妙……总之除了坏话,什么话都说。
这时,有个刺耳的音乐突然鸭子似地嘎嘎叫了两声。我和MAY吓了一跳。同时抬头四下张望。
“没事,没事,”菲菲笑,“是我老公的手机短……”
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一个球一样的黑影已经如飓风般一下扑至床头柜前,以电光火石的速度一把拿起手机噼哩啪啦地狂摁按钮。
三人目瞪口呆!
“嘿嘿,没事没事!是我的手机。”猪头对着我们呵呵地笑。一手拎着穿了一半的裤子,一手抓起手机扬了扬。
我无语。
菲菲轻声怪责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家里还有客……”
还没等菲菲说完话,MAY已经忍无可忍地暴跳如雷!
“哇靠!你个死胖子!你就不能穿好裤子再出来吗?就为了这么一个破烂短信,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了!你还是人吗!你恶不恶心哪?知不知道丑啊?刚才那个什么短信,哪个女人发的?快拿过来给你老婆检查!”
相反于MAY的怒不可遏,菲菲却平静异常,只是忽然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他已经删掉了。”面无表情。
此言一出,如同炸雷。
我和MAY疾速把头转向菲菲,发现她平静得仿佛一面镜子。任何来自外界的光线刺激都被她折射抵挡回去,竟动不了她分毫。
6
回来的路上,MAY一路走一路骂:“我受不了了,我快疯了!这是什么世界!什么男人!简直太让我恶心了!我差点没有当场吐出来!那只该死的贱猪,居然还好意思对着我们笑!真想冲上去暴打他一顿!”
“好啦,好啦!”我试图安抚她,“就算真要暴打他,也轮不到你来呀!人家主角都没吭声呢,你那么义愤填膺做什么!”
“我就是受不了菲菲!我真搞不懂!她也没长得满脸麻子,缺胳膊断腿呀!干吗非要吊着这只死肥猪不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知不知道,上回菲菲告诉我,那只死肥猪带着他们家的小狗出去溜狗。结果,七点半出去的,十二点半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溜狗都溜到人家楼上小姑娘的家里去了!——你说说,这种男人还有什么希望?菲菲跟着他,以后真的会苦死的!这害人的死胖子!怎么也不早点死?”
“好啦,好啦!你就别再喷口水了。再这样下去,我看他没死,你倒要先失水过多而死了!人家自有人家的生活。你没看见菲菲刚才那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么?我早就说过了,她能跟他相处到现在,还嫁了给他,这其中必有道理。旁人是管不来的。”
“什么××道理?”MAY依旧愤恨难平,“什么道理能让一个女人这样忍气吞声地糟蹋自己?”
我淡淡地笑了笑,吐出两个字:“生活。”
7
事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叮当听。叮当跟我持同一观点。
“有些人就是有这么一种偏执的心态,偏执到近乎病态。”她说,“他们总是认为在一个地方扎根就一定要嫁一个或者娶一个那地方的人——这样才算完全地融入,才算扎下了自己的根基——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虚荣心态。‘上海人’这三个字总是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微妙的东西潜伏在里面——能让人骄傲,也能让人痛恨——而这种痛恨又正是来自于这种骄傲。”
我叹了口气:“嫁个上海人!——只因为如此,就得忍受一切的不平吗?——如果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嫁娶,那么她的未来又怎么还会有好日子过呢?真是个没有大脑的女人!”
“那也不能就这么说,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可我们并不是她。怎么就知道她不以此为乐呢?或许她根本就没有认为这一切有什么不平。或许她就是很开心,认为这很公平——她得到她想得到的上海人。而那个上海人呢?当然也有权利去追逐他想要得到的自由和放肆。”
“这听起来简直像一个令人发指的等级制度,”我叹了口气,“某些等级高高在上。而某些等级,永远诚惶诚恐,委身于下。”
“别这么消极!这只是一种病症。某些人就是得了这么一种病症,‘嫁个上海人’症候群!哈哈……”叮当笑了起来,“得这种病的也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我就认识一个外地来的男孩子。青梅竹马又漂亮又能干的女朋友他不要,非要立志找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做老婆。结果,找来找去,不是嘉定的就是松江的,要么就是南汇的……”
叮当还没说完,我就已经先哈哈大笑了起来。
“还有这么不走运的傻瓜呀!”我说。
“当然有了!”叮当一贯淡淡地笑,“我什么人没见过?——我见过的人,太多太多了……上海这地方!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