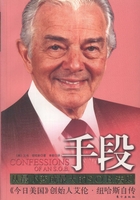前言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那些磨难给了我坚忍不拔的心灵,现在想起这一段,我不再不平衡了,相反有些感恩,有些怀念那些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的执拗的岁月。
而那段被哮喘折磨的岁月,也增强了我生命的承受力。呼吸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患上气管炎,可想而知,一呼一吸之间,都在痛苦间煎熬,这使我在面对身体不适时更有耐力。风浪、严寒、睡眠不足、湿疹折磨,我能做到种种挑战自身体能极限的事情,都是幼年经历的馈赠。
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你的一样东西,必定会补偿你另一样东西。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受过磨难,就永远不会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1.被哮喘折磨的童年
我不愿去回想我的小时候,因为那种状态太封闭,太孱弱,太自卑;但我时常又下意识地想起那段时光,当我驾着船驶过赤道,看着漫天繁星时,当我在寂静得令人发疯的大洋上时,童年的一切都会浮上脑海。童年是一段亏欠,它并不美好,让我备受折磨;但是童年又是一段蕴藏,没有那样的忍耐、坚持和爆发,我也许至今庸庸碌碌,直到终老。
一切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
我是一个矿工的儿子。1968年11月1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叫做新汶矿务局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矿产的原因,父亲给我取了个“墨”字,他或许没想到,几十年后,我真的变得像墨一样黑,但我皮肤的墨色里,是蕴含着太阳的能量的,是多少年曝晒在大海里储存的太阳能。
我们这里解放前叫新泰,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有一条柴汶河在这里流过,所以煤矿取名“新汶”。自我懂事起,我的视线里就充满了开矿扬起的灰尘,以及那些现在看来陈旧落伍的工程车辆、挖掘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至今还常常回荡在我耳边,相伴随的,是我自己咝咝呀呀的喘气声。
我的父母已经有了五个儿子,但他们意犹未尽,又再接再厉把我给造了出来。轮到我的时候,大概“原材料”已经没有最开始质量那么好,而且矿上的空气、环境情况可想而知,所以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身体就不好,从小嗓子里就呼哧呼哧的,只要稍稍运动就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都说我这是哮喘,也可能是气管炎。这是我五个健壮的哥哥没有的毛病。所以从小父母和哥哥就给我特殊待遇,他们的眼神里常常流露出对老幺的怜爱之情,但男子汉是绝不需要那种眼神的,那反而让我更自卑。
母亲对我很好,好得有些过分。她最怕我感冒,因为一旦伤风着凉,我就会剧烈咳嗽,然后开始哮喘,咳得母亲焦急不安、心神不宁。为了给我治病,她带我跑了不少地方。先是上大医院去看,大医院治不好,又去乡里搜罗那些土方偏方。只要听说有什么法子能治哮喘,不管有没有科学依据,母亲都要逼着我试一试。
记忆中最荒诞的治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特殊的方式来吐痰,就像《神雕侠侣》里的裘千尺吐枣核钉一样,把痰含在嘴里酝酿好了,再瞅准一个目标,爆发力十足地喷出去;还有一种是把明矾化在醋里,让我一仰脖喝下去,那怪味直熏得我恶心反胃,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儿,跳着脚转圈……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后来上中学时读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我当时那个后怕呀,暗暗庆幸母亲没读过鲁迅小说,不知道华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痨病的事,否则……想到这里我就寒毛直竖。
童年的我身上一年四季都弥漫着一股中药味,这是一种自卑的气味。哥哥们被熏得不愿靠近我。可这种气味越来越浓烈,身体却也没见好起来。秋冬寒风一起,我又开始咿咿呀呀地“拉二胡”。
晚上睡觉也是母亲陪着我,因为哥哥们都不愿意跟我睡。我总是带着吱吱呀呀有如二胡一样的声音进入梦乡,这让他们不胜其烦。有时候他们会过来推我一把:“老六,闭嘴!”直到我尴尬地醒过来。
为了我的病,母亲以泪洗面,我见她悄悄捶着胸口跟父亲抱怨:“对不住老六,不该带他来世上受苦,他这身子骨,将来可怎么找工作怎么娶媳妇……”父亲鼻子里哼一声:“哭什么?老六要真是个熊包,我养他一辈子!”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父母的话让我无比地恨自己。那时候我还小,还想不到娶媳妇那么遥远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明白:因为是老幺我最受宠,可是又与别家的老幺不同,这种宠爱不过是一种可怜罢了。想到这里,我又开始激动地喘起来。
六岁那年,我上小学。上学第一天,母亲带着我去见了班主任。只见她和班主任耳语了几句,班主任的眼睛扫过我的面庞,似信非信地点点头。
当孩子们一窝蜂冲向操场时,我便被老师拦住:“你娘说了,要我好好照顾你,这些活动你都可以不参加,就在场外休息吧。”滚铁环、扔沙包、打弹弓,都没有我的份,看着男同学们滚打在一起,我只能在操场边装作毫不在乎地望着天,或者蹲在角落里数蚂蚁。
和同龄的孩子打闹是被禁止的,其实哪怕出去转转,母亲也会担心我中途出事。“翟墨,过来,我们踢球少一个人!”“翟墨,你有没有弹弓,打鸟去!”每当有孩子在我家门口发出这样的召唤,母亲就会非常委婉地帮我拒绝:“翟墨他身体不舒服,你们去吧!”
1975年冬天,特别冷,母亲到学校来看我,见我有点哆嗦,便径直走向了班主任办公室。第二天老师就调动了座位,在同学们注视下,炉边的温度把我的脸烤得发烫。但我很清楚,绝不是炭火让我的脸发红。
此后的每个冬天,火炉边的位置肯定是为我留的,我觉得连班上的女生看我的眼神都不对。“翟墨,你是个弱者,你他娘的是个弱者!”我一边骂自己没用,一边用铅笔在作业本上无聊地划动,只感觉一股热血在往脑袋上涌,眼睛都有些发酸发胀。每次听到有人在说,某某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时,我就会下意识地想到是我,就会不自觉地躲闪别人的目光。
教室里的冷清和操场上的喧腾被玻璃隔成两个世界,阳光映照着孩子们脸上的欢笑,是那样美好。而我被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抛弃,只能做一个病弱的旁观者,默默躲在阴暗的角落承受着孤独和寂寞,心情像溺水一样沉到谷底。而在上课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会条件反射般迅速离开窗口,回到座位上拿起书,背挺得笔直,脖子骄傲地高昂着,装作一门心思温习功课,无视陆续走进来的同学们。
多年以后,我一个人在海上航行时,有时几个月时间见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甚至见不到一只动物,那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按照父母的说法,我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就已经该谢天谢地了,怎么还敢去孤身冒这么大的险呢?当我在海浪中摇摆、挣扎过后,偶尔也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但是我更加相信,正是童年那种病痛和心态,让我有更多的耐力和韧性,去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事业。
2.自闭在画中
借着保护我的名义,所有人都在和我疏远。
哥哥们都让着我,可也不愿意带我玩儿。他们把我当弟弟看,但是却没把我当作一个男孩,没把我当作跟他们一样的哥们,可以翻墙上树、调皮捣蛋、共同进退的兄弟。他们总是摸摸我的头,说:“快快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兄弟六个睡在一张大炕上,可他们五个宁可挤在一块儿,也不愿挨着我。后来哥哥们陆续当兵,离开了家。那张大炕上的人越来越少,睡的地方也越来越宽松,可我的心也越来越空空落落。
在学校,我很受老师们的照顾,可恰恰也是这种特殊照顾,让我显得那么不合群。
有一天,体育老师把我叫过去,用很委婉的口气告诉我,如果我觉得实在不舒服,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因为即便是上,我也不过是带着一张假条来走个过场。
我并不觉得自己孱弱到连操场都没有资格踏入的地步。“老师,我觉得我身体没什么问题,可以上课的。”我争辩道。但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你身体不好,就不要硬来嘛!”他的目光一下子散开,“就这样吧,从明天起,体育课的时候你到教室里面读书去。”
同学们渐渐地也不待见我了,谁愿意和一个跑不动、跳不远,走两步就喘粗气面色吓人的孩子玩呢?谁愿意和一个什么球类运动都不会的孩子玩呢?谁又愿意和一个“老师面前的红人”、“受宠的孩子”玩呢?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也在疏远所有人,画画成了我唯一可以自豪的“长项”。
那时父亲工作之余有两个爱好,一是打猎,二是钓鱼,在当地,这也是“引领时尚”的两个爱好。要搁现在,没准他老人家也能评个“绿色生活领袖”、“蓝调生活家”什么的。
打猎危险,要翻山越岭钻丛林,子弹也不长眼,再说我也跑不动,父亲从不让我跟着。但钓鱼是个安静又安全的活动,父亲怕我一个人在家呆着闷,有时也会带上我。和父亲出去钓鱼简直成了我的节日,其实去了我也只是在旁边呆着,拿着树枝和石块在地上乱画。
这天阳光灿烂,父亲戴着一顶大草帽,抽着烟拿着钓鱼竿,悠闲地等待鱼儿上钩。我看着他专注的样子,觉得挺好玩,拿起树枝随手在地上把他画了下来。画完之后,我又换了几个角度,画他各种各样的动态。
等父亲收拾渔具回家时,突然发现了我的“杰作”。他惊讶地看了看,问:“老六,这是你画的?”我点点头,父亲像不认识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一拍肩膀:“嘿,小子,行啊!”
过了几天,父亲拿回来一张画板,还有一些水彩颜料,说:“既然不用上体育课了,老六可以学一下画画。”家里人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兴趣,没有一千米长跑,没有跳远和扔垒球,我需要做的就是和平常一样节奏的呼吸,然后在画纸上创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
我开始画画,跟老师学,有时候也自己创造。画跑动的人物,画大自然,画孩子们嬉戏打闹,画家人,我的画里充满了动态的东西,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我最喜欢画的就是正义的侠客把一帮强盗打得满地找牙,父亲经过我身边时,端详一下画板上的东西,然后就敲我的脑袋:“打你个鬼画桃符,打你个不专心,再不好好画老子揍死你!”
画上的世界刻意和我保持距离,尽管我是那么想融入其中。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自闭,但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如此,我不再搭理同龄人不怀好意的召唤,我总是觉得他们企图嘲笑我。我就和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伴,和一个幻想的世界为伴。在画纸上,我描绘过大海,太阳悬在海上,朵朵白云,海鸥飞翔,一艘轮船冒着烟驶向远方。我不知道真正的大海是不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哮喘病,以及为了排遣这种病带来的烦躁而画画,都成为后来鼓起那面风帆不可缺少的风。海上你永远不会知道将发生什么,你可以做的就是去接受、去忍耐。就像忍耐漫长而孤独的旅程,就像忍耐狂躁而恐怖的风浪。每次与大海搏斗结束,我内心回归宁静,就像一幅画一样。那时候我就会庆幸,自己曾经拿起过画笔。
而父亲也没想到,他老人家为了让幼小的儿子打发寂寞而画画,却成了我多年后谋生的一项本领。当我在法国和新西兰办个人画展时,回想往事,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奇妙。
要不怎么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少年时期定下型来呢?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那些磨难给了我坚忍不拔的心灵,现在想起这一段,我不再不平衡了,相反有些感恩,有些怀念那些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的执拗的岁月。
3.想当“坏孩子”?没门!
也许是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小时候,但凡见到我,不论家里人还是邻居,都会称赞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邻居们常批评自家孩子:“啧啧,看看人家翟墨,一放学就回家,从不上外面野,瞧瞧你这个没出息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在我“好孩子”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坏孩子”的心。坏孩子并不是真的坏,而是想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少年时的我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再告诉自己是个弱者,我希望能够证明自己。
因为绘画,我在学校里逐渐找回一点自信,美术老师时常拿着我的画,在班上表扬我。每当大家的目光投向我时,我故意装作面无表情,其实心里乐开了花。
可这一点点自信是那么的不够,随着年岁成长,我更加渴望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女孩子们的关注。到十二三岁,同学们都渐渐萌生了性别意识,开始对异性充满好感,男孩子们故意找借口和女孩子们搭讪,女孩子们也常围成一圈,聚在球场给男孩子们加油。每到这个时候,我会更加落寞,因为我永远也成不了球场的主角。可我也希望,女孩子们的目光能在我身上停留。
就像苏童在某篇小说里写过的一样,当时住在铁路边的矿上少年,最“拉风”的就是穿上流行的喇叭裤、提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到处乱晃。录音机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少年们摇摇摆摆地踩着舞步,走到哪里都能吸引女孩们的目光……
我多么希望成为这些少年中的一员,多么希望能成为那个发号施令的孩子头。可当时,在孩子们的游戏中,我连参与权都没有,更别提话语权了。
这些穿喇叭裤提录音机、爱玩爱闹不好好学习的,被老师看作“坏孩子”;而那些埋头学习、经常受老师表扬的,被认为是“好孩子”。我因为身体不行,跑不了走不动,只能乖乖留在教室里,被人错划为“好孩子”一派。可天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做一个受人关注的“坏孩子”!为此,我和五哥一起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砸碎了学校所有教室的窗玻璃。
起因是那天五哥受了点委屈,被老师批评了,为了表示抗议,放学后他偷偷砸了教室一块窗玻璃,我也捡起石头“哗啦哗啦”一路砸下去。
这起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案件”很快被破获了,第二天,母亲被叫到学校,我和五哥被拎到老师办公室。我低头站着,心里有些惶恐也有些兴奋,甚至隐隐有些期待,期待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心想,我一定要像个爷们,像故事里那些坚强的共产党员,父亲和母亲怎么揍都咬紧牙关不投降。
谁知,我和五哥一起闯的祸,到最后根本没我啥事。五哥被罚写检讨,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念,还差点被开除学籍。回家后,他又被父母好一番胖揍。而我在一旁站着,直接被所有人忽略,老师、父母仿佛都忘了我的存在。五哥一时成了风云人物,成了全校调皮捣蛋孩子们的偶像,而我,这个主犯之一,却压根儿没有人想到要惩罚我!
嗨,我哭笑不得,就像一只极力要弄出点动静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小老鼠,却屡屡失败。我对自己说,翟墨,你太弱小了,弱小到天塌下来都没资格去撑;弱小到自己闯了祸,却要借哥哥的肩膀来承担后果。这种被忽略的痛苦,对我来说,比体罚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