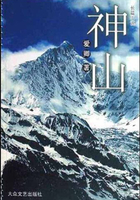最有趣的当数拜堂娶亲的游戏。那时节,优雅年轻的陆英还在。仆人用竹片扎了个小花轿,小佳人们便兴冲冲将家里的洋囡囡穿上滚了花边的衣帽,安坐在小花轿里,保姆走在前面“哐哐”地学着敲锣声,张家的小姐弟则抬着花轿,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花园那边。那情景,真是娇憨可爱得惹人畅怀。
后来,玩得不过瘾,三姐妹便将六岁的大弟打扮成新娘,从母亲房中取来胭脂花粉刨花水,搽得大弟小脸儿红一块白一块;母亲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上四根朝天辫,又取一块绸手帕,塞在他的小裤带上做花裙……直到像个俊俏的小新娘了,便请来二弟当新郎,与小新娘拜堂成亲。一本正经地拜了祖先、父母、客人,磕好头爬起来时,小新郎一不小心,踩掉了小新娘腰上别着的那块手帕裙子,一屋子人便再也憋不住地哄笑起来。委屈的小新娘瘪瘪嘴想哭,大姐一把搂在怀里哄:“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花园里的花厅,是三姊妹读书的地方。书房门前有两株玉兰树,一株紫玉兰,一株白玉兰。一到春天,便开了满树灿烂花朵,似乎闭上眼都是一树一树的花影。实在是美丽得过了分,姐妹们会捡来落了满地的玉兰花瓣,求伙房的厨子放在油锅里炸来吃,又脆又香,居然是爽口的美味。
彼时,最爱这快乐城堡的,是兆和小姐。人生无常又有常。这位名门闺秀的童年,除了像男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玩耍,竟没有半点名媛的影子。而远隔湘江沅水的沈家少年,也只在逃学撒谎中懵懂长大,没有丝毫后世人眼中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的迹象。
也许,这便是前世注定。人世间相遇,忽然间一见钟情,或者忽然间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从对方眼眸中,蓦然发现了似曾相识的气息,恍如隔世,似乎在哪里见过,便勾起了你冥蒙如初的记忆,于是那亲切幸福的感觉,让你再也不愿放开。
多年后,当沈从文疯狂地爱着兆和小姐,也许正因了冥冥中那一丝久违的相似气息,使得兆和小姐周身散发的气质,那样灿烂迷人,恰如他别离已久的曾经。
童年的张兆和虽不像沈家少年那样四处疯野,在张家,却也是出了名的调皮。从小,她便不十分文静,也不喜欢女孩的小玩意儿。曾经,她用自己的小凳子将泥娃娃砸个粉碎,又赤手空拳将一个布娃娃撕成了碎布。后来,领教过她厉害的父母给她买来个橡皮娃娃,她只研究了一会儿,便找了把剪刀,喀嚓一刀,就干净利落剪掉了娃娃的头。
即便坐在花厅的书房中读书,她也并不安分。一边朗声念着先生教的课文,一边侧耳聆听后花园的声音。果实成熟季节,后花园的核桃树、杏树、枣树和柿树,时不时“扑扑”地落下果实,她暗暗记下果实掉落的方位,下了课,便和姐妹们飞快地跑去花园,抢着去捡。
童年最安静的时光,是她傍晚和父亲一起出门散步,和姐妹们坐在一起读经书,是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地临帖练字,那一刻,她名门闺秀的优雅韵致,才微微地露了一丝端倪。
从曾祖张树声开始,昆曲一直是张家不离不弃的挚爱。这古老声腔的魅力,也一样让张冀牖醉心钟情。早年搬到上海,张冀牖曾长年包下戏园子第三排整排座位,带着全家老少,去看戏台上的红脸关公和美貌温静的杜丽娘。
水软风轻的苏州,本就是昆曲的发源地,走在苏州城,似乎每一条街巷,每一处水榭亭阁,都有昆腔的低吟浅唱。张冀牖历来志趣高雅,他觉得,家里的几个女儿,应从昆曲艺术中得到熏陶,这优良传统的古老艺术,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她们高贵不俗的气质。
全福班名伶尤彩云,是张冀牖为女儿请来的启蒙昆曲师傅。初时学曲极为辛苦,甚至大年初二,也要关在父亲书房中咿咿呀呀地学唱。小姐妹们想偷懒,父亲总是连哄带劝:“好好学,以后我替你们做花花衣服上台演戏,多好玩!”
许多年后,父亲应该可以为当初的决定抚掌含笑了。张家四姐妹长大后个个高贵典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声誉,仅次于“宋氏三姐妹”,是张家的良好家风和教育方式,成就了这些优雅的闺秀们。
小时候的兆和,似乎是姐妹中最懵懂的一个。她不太喜欢昆曲中娇弱忸怩的丫环小姐,不习惯那拖长音调的唱腔,每回分角色演出,她要么粘上假胡子演老薛保,要么就将脸上画得乱七八糟,演滑稽戏中的“万能博士”、“天外来客”,倒演得异常开心。有一次姐妹们演《风尘三侠》,她分的角色是李靖。那时她还小,坐在“龙椅”上,两只脚够不着地,悬空荡来荡去,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弄得大英雄李靖像个没断奶的孩子。
除了兆和,张家另三位姐妹的一生都与昆曲有关。大姐元和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最后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的夫婿是语言学家周有光,她一生酷爱昆曲,一九五六年与俞平伯在北京创立昆曲研习社,后来担任社长,为弘扬昆曲艺术功不可没;四妹充和嫁给美籍德人傅汉思后,长年在耶鲁、哈佛等大学教授昆曲和书法,2004年回国举办书画展,即兴清唱了一回《琴挑》和《惊梦》,那份知性优雅的古典美,让人叹为观止,被誉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后的闺秀”。
尽管,兆和不似她的三位姐妹,沿袭和传承了整个家族对昆曲的热爱,但她的人生,有另外的戏份。冥冥中,这是一种命定。在遇到沈从文之前,命运带给她的所有特质,所有喜好,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一场相遇而筹备,直到所有这些特征,组合成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她,让另一个人着迷;直到生命中注定要到来的那个人,出现在她面前。
恰是幼年这一份不太细腻、稍嫌粗粝的性格,才使她多年后面对世上最炽热缠绵的情书,居然雪封冰冻,无动于衷;也恰是这一份不过分敏锐的温厚,才使她最终接纳了与她家世悬殊的沈从文——那个未曾受过良好教育、浑身散发苗乡的朴野、充满自然灵性的才子,作为她的终生伴侣。
她只是按照命运安排的方式在成长,选择了一条能与他相逢的路,山环水绕地向前走,直至找到他的方向。
张冀牖投资的乐益女中建成后,张家老少从寿宁弄8号搬进了五卅路的九如巷3号。此后,关于张家姐妹,就有了叶圣陶著名的那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而叶圣陶,曾在乐益女中教过书。
苏州的烟柳画廊,长亭短亭,一回回在春光里醒转;苏州城里最优雅的女子,也一天天在长大。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苏州更适合张家的闺秀们,它的小桥流水、曲榭回廊,以及吴侬软语、短棹轻歌,是一幅写意水墨,是一卷长轴,一曲昆腔,多少世纪过去,也一样不疾不徐,缓慢舒展最优雅的江南风韵。
身处那样的水墨江南,伴着那样的杏花春雨,从那样幽深小巷走出的名门淑媛,必是最温婉蕴藉、古韵流芳的女子,是一个世纪的惊鸿丽影,绝代传奇。
在苏州长大的三小姐兆和,从她懵懂淘气的童年,走向她一生最灿烂的年华。她在成长,打开一道门,又一道门。进了苏州女子职业中学,又进了乐益女中。数年后,考取了位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她打开了最后这道门,瞬间,一片辉光耀眼。一个等待了她许久的崭新世界,伸开双臂,拥她入怀。
她十八年无拘无束的时光,至此忽然变得美妙而轻柔。那样长久的准备,只为着这一刻。她美丽的人生,此时才真正开始。中国公学,万流汇聚,而她,是千万朵浪花中的一滴,却带着使命而来。
此刻,她已蜕变成清丽脱俗的女子,是一朵长在春风崖畔的黑牡丹,那样显眼,那样特别。她绽放的青春在等待一场传奇。
人生的舞台,已准备就绪,接下来的时光,她将是无与伦比的主角。
有翅膀的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没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飞入你的心里。
我不必问什么地方是天堂,我业已坐在天堂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