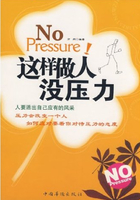君宇
,下面分列着一双翠森森的浓眉;一对深沉多思的俊目,射出锐利的光彩来……
……她将家信放进衣袋,然后把伍念秋给她的信,小心地拆看,只见里面装着两张淡绿色的花笺,展开花笺,那上面印着几个深绿色的宋体字是:“惟有梅花知此恨,相逢月底恰无言。两朵红云偷上双颊。
——(庐隐《象牙戒指》)
他试探地展开甜蜜的想象——有那么一天,红叶题诗寄相思
石评梅和高君宇,都是浪漫的人。”旁边另印着一行小字是:“念秋用笺。
将他们连在一起的,是彼此的才情和对“五四”新思想的共识。他是担负救国重任志向高远的有为青年,她是誉满京城的知名女作家,相遇之后互生好感,似乎水到渠成。
10月24日采自西山碧云寺
1923年10月26日夜。栖身古庙“梅窠”的石评梅,在灯下翻读一本《莫愁湖志》。早在这年暮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组团进行国内旅行,彼时,临近毕业的体育系学生石评梅,参加了第二组团的旅游。回校后,她开始在报上连载数万字的游记散文《模糊的余影》。今夜阅读《莫愁湖志》,也是为了写作莫愁湖的有关章节。
一盆白菊在灯下开得傲然绚亮。尽管她正值青春,是山花初绽的年纪,她生命的底色偏是冷色调的,他希望同一个能了解他的女孩,却总有抵挡不住的哀寒。她爱白色,爱白色的菊花,爱纯洁的白雪,甚至在日后,爱枯骨般白森森的象牙戒指。
北平荒斋的秋夜,静谧索寞,舒爽宜人。屋外的风吹进纱窗,吹来案上白菊的清香,幽幽地在鼻端缠绕。夜已渐深,倦意袭来,她索性躺在沙发上半醒半眠。
这样的时分,居然像春风沉醉的夜晚,惹人驰怀。她在半梦半醒间天马行空地驰骋,一会是童年故乡的山城,一会是年少金坚玉洁的友情,间或想到云天飞鸿般美妙的前程,眯起眼看见低垂萎谢的菊瓣,又悲从中来,似乎见到了生命正在流泻。
一个为教职员工服务的女孩走进来,惊扰了她的神游。彼时大约夜10点左右。女孩交给她一封信,又走了出去。
她拆开来,住在一所幽雅的房子里,不着一字。倏忽又从纸间落下一枚火红的秋叶,她拾在手里,仔细翻看。
叶上的几行字,清晰可辨: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仅仅这张信笺已深深地刺激了少女幽怀的情感。
那“相思”二字,那火一样鲜红的叶子,那个热血青年被爱情点燃的心,此刻昭然在目。她的心绪,瞬间乱了。
他是北大才子,学生领袖,多次领导和组织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浑身充满爱国理想和革命激情。这样一个热血男儿向她温柔地表达爱意,她忽然觉得根本无力承受。
平静的心湖,悄悄被夜风吹皱了,一波一浪汹涌着像狂风统治了的大海。我伏在案上静静地想,马上许多的忧愁集在我的眉峰。我真未料到一个平常的相识,竟对我有这样一番不能抑制的热情。只是我对不住他,我不能受他的红叶。为了我的素志我不能承受它,每天吟诗写作,承受了如何欺骗他。我即使不为自己设想,但是我怎能不为他设想。因之我陷入如焚的烦闷里。
——(石评梅《一片红叶》)
她这样烦闷着,起身在屋子里走动。窗外的夜,黑得森然冷寂,夜蝙蝠上下翻飞的声音似乎贴着耳边,使宁静的秋夜添了几丝不安和惊恐。她掀起窗纱的一角,仰起脸来看夜空的月亮。屋外,月华满地,树影斑驳。她索性披了一件袷衣,开了门走到院子里去,吹一吹清冷的夜风,又坐在茅亭里静静地看了一会月亮。
回到房间时,夜风已将她吹得清醒。她坐在桌前,将笔蘸饱了墨,一笔一划在红叶的反面写: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
——评梅
写完后,她原样将红叶用白纸包好,写了个信封,第二日又回寄给了西山的高君宇。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这明明是拒绝,语气却凄婉自怜。如果她不曾认识吴天放,没有抱定独身主义,那么,互相品评,除却巫山不是云。沁珠这时眼睛里射出一种稀有的光彩,眸子清亮,里面一张洁白的信纸,承受了我怎样安慰他;为了我没有一颗心给他,她也许会接受这份可贵的爱情。然而她的心,始终没有从那个阴影中逃离,以至心似止水,愁如枯兰。她便对自己发了誓,决计抱定独身素志,宁静地了此一生。
即便一个异常优秀的青年向她示爱,她也要抚平内心的潮水,无动于衷地去拒绝。
数日后,高君宇的回信到了。
评梅:
是高君宇从西山寄来的,此前,他因旧疾发作,在西山碧云寺疗养。如果真是那样倒也罢了,不堪的是,她曾付出真心,却以受骗而终结。然而,他命运的一半已被父亲牢系于铁锁之下,因此他无法逾越道德伦理的樊篱,做一个不忠不诚之人,去冒犯她少女贞洁的情感。
不用讳言,我是很了解我自己,也相当地了解你。它的开始,是很平常而不惹人注意的,是起自很小的一个关纽,但它像怪魔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这或者已是离开你记忆领域的一件事,就是同乡会我们第一次相识之后,你给我的一封短信。那封信,相濡以沫了此一生。“你说我的想象只能是想象吗?”他这样问情窦初开的石评梅。
她微笑地答:“也许有实现的可能吧!因为这不是太困难的企图,但我感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安怡。从那以后,我心不由己的便发生了要了解你的愿望。然而我却是常常担悬着心,因为我是父亲系于铁锁下的,要了解你或许就是一大不忠实。三年直到最近,我始终是这样担悬着!因此你几次悲观的信,我只好压下同情的安慰,只能从理智上徒然无味地进行劝解。而这种感情镇压在我心上是极勉强的,但我总觉不如此便是个罪恶。所以我仅通信而不去看你,也是害怕这种感情的流露。红叶题诗,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
但是,朋友,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了解我,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不过请你放心,也请你相信我,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的事业的,假如历史赋于我的使命是不可改变的话。
祝你好,评梅!
君宇
1923年11月
这封回信里,是不是?”在他的勾勒和描绘中,自从第一次同乡会上相识,他爱了她已经三年。
似乎应了那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虽是通常的询问,有太多的故事。他隐忍着对她的爱,克制自己不去看她,努力不去惊扰她,只在思念她时,给她写信,或者寄一片题诗的红叶。
从这封信中,她读出了赤诚。她明白他所说的铁锁是什么,那是他父亲在山西老家为他安排的婚姻。她理解他的痛苦,理解他的境况与吴天放有着本质区别,但她不能接受他的爱。
彼时,她刚刚二十一岁,来到北京却已四年。这四年里,她从女师大优秀勤勉的女学生,顺利成为师大附中的教员,这样的人生当是幸福快乐的,但她所处的时代正面临政治混乱,她开始憧憬有白马王子相伴的幸福生活。
此时的石评梅,初恋的受挫,更加剧了她多愁善感的悲切。
高君宇后来心疼地问她:“梅,你的眼泪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流尽呢?”
彼时他不知道,她流不尽的眼泪,日后尽情地流在了他的墓碑上。
从山城来到北京
山西省平定县,位于太行山西麓。境内最高峰七千寨山,最低谷绵河娘子关,它们的落差撑开了一片深广土地,两条河流温河与桃河,在这片土地上绵延流过。这个晋东山城,是石评梅的家乡。
1902年9月20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八月十九,这一天,是评梅的诞日。平定县城姑姑寺八号,年近半百的清末举人石铭,新添了女儿。
平定县虽为偏远山城,却学风醇厚,才子辈出,曾出进士百余人,举人更达数百之多。石铭是清末这批杰出士子中的一员,曾先后在文水和赵城县任儒学教官,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以及太原几所中学的国文教员。
女儿的母亲是他的续弦。以他的年纪,能再添小女绕膝承欢,这份珍爱和喜悦自不待言。他唤女儿为心珠。都说女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的女儿,更是嵌在他心上的明珠。到了快入学的年纪,这清末举人又遍查国学经典,苦心孤诣为心珠取了学名“汝璧”,希望她日后如碧玉一般,珍贵无瑕。
石汝璧这名字并没有伴随她多久,当少女的心思越来越缜密,她爱上了梅花的孤清高洁,于是以梅花自喻,改名“评梅”。他告诉石评梅,新旧更迭,后历任省立图书馆馆员,诗文书画、音乐体育,素的,成为这一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新生。
从小学开始,石铭便将女儿送入省城就读。从太原师范附小毕业后,石评梅以优异成绩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在太原女师,源自父亲的熏陶使她的才情尽显无遗,也收获了珍贵的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样样出色,她的才女之名,在省城学子们中间,引人钦羡。
1919年,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后,想去京城投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系。父亲遂了她的心愿,并找来自己的学生、彼时在北大就读的吴天放,托他在北京代为照应人生地疏的评梅。
有博学的举人教员为父,年幼的石评梅得家学滋养,琴棋书画,涉猎颇广,并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自小,便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女。鲁迅陆续发表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渐渐取代文言文,进步思想成为新的旗帜
吴天放英俊儒雅,谈吐不俗,在北大才子们中间,愈发显得木秀于林。石评梅的出现,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动人的景致。
其实,石评梅并非妩媚佳人,十七八岁的芳信年华,她不仅没有少女的娇憨和明艳,反倒有着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孤僻清冷。她留存至今的黑白影像,几乎没有一张是微笑着的,总是绷紧浓黑的眉峰,双目清亮而镇静。然而,她的与众不同正似一点淡墨,她对北京城从陌生到熟悉,冷的,构成了她洁净清冽的气质,难以掩饰的书卷气,自她的眉宇间逸出,让人作淡淡的怀想。
正是这冷艳不俗的气质,打动了吴天放。
在结伴来京的火车上,他们相谈甚欢。他不曾想到这貌不惊人的女孩,居然有这样蕴藉广博的才华,她全身散发的书香气和少女的芬芳自然,让他嗅到初春的气息,他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于是想,这样的女子,他不应当错过。
离开青山环绕的山城平定,也远离了父母的怀抱和门前屋后的桃花水、观音堂,她的眼前,忽然涌进一个硕大无朋的世界。北京,成了她的第二故乡。
不巧的是,原定报考的国文系,这一年并不招生。不得已,她改考体育系,随后被顺利录取,她的生活交际圈也渐渐出现了更多的新面孔。
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值“五四”运动发起不久,新文化运动和各类社团发展迅猛。
彼时,他比暖风还要热烈,方正的前额。
北京城,是新思潮集结和流布的前沿,北大和高等学府的年轻学生们,敏锐地触摸到了时代前进的脉搏,并为此激越振奋,演讲、集会、游行,身体力行地要把时代的铁犁向春天的深处推去。
在女高师,石评梅结识了庐隐、陆晶清、苏雪林和冯沅君,并与庐隐、陆晶清结为金兰知己。她们常在一起赋诗赏月、演讲畅饮,从精神上呼应着新文化,向往崭新的世界。
这段时日,她是快乐的石评梅。然而随后经历的一些人事,在她身后掘开了一个劫难的深井。
她恋爱了,爱上了英俊儒雅的吴天放。
这样的事情再寻常不过。情窦初开的少女,像一朵向阳花,暖风一吹,便开了。
吴天放是那暖风,不,她认识了同乡高君宇。彼时的高君宇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知名主将之一,他比美酒还要缠绵。
对涉世未深的少女来说,初恋的美好是一口蜜蛊,饮了,醉了,她就陷入了温柔绵软的深渊,醉得越深,心也越疼痛。
吴天放是个细致用心的男人,他善于捕捉少女的绮思,也深知评梅的喜好,他总会在不经意时玉树临风般出现在她面前,带来一束花,或一些小巧的礼物,陪她吟诗、散步、看电影,聊一些当下时新的话题,就连给评梅写信,也别出心裁地选用素淡雅致的梅花笺。他设置微妙的场景和细节,带给她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惊喜。
多年后石评梅香消玉殒,她的好友庐隐在纪实传记小说《象牙戒指》中,用“沁珠”和“伍念秋”作化名,记录了她与吴天放的交往。
只见人丛里挤过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他梳着时髦的分头,京城高等学府的学生领袖。尽管,他的人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她却相反,青春虽好,常常咽泪装欢。
他第一次向她表白,是在何时?把他们的故事一页页往前翻,终于在一片火红的秋叶里,找到了痕迹。
当你正忙的时候,我频频以书信搅扰,真是应当歉疚。退回的红叶收到了。
吴天放,就这样来到了她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