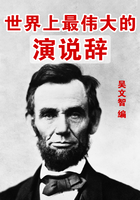然而第二天,她打开画展室的大门,那一瞬间,将他国当作了避风港。,到处是被损毁的画作,几幅她最珍视的作品已不翼而飞,而那幅《人力壮士》,不仅触目惊心地被刀片划了个大口子,还题上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妓女对嫖客的歌颂。
欲哭无泪。不问你的付出与成就,留学归国后的幸福时光
1921年,刚刚建立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成了潘玉良留学法国的第一站。
这所学校虽在法国,却是中国中法大学设在法国里昂的大学部,旨在为留法中国学生提供外国语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储备。对潘玉良来说,是为了尽快适应留学生涯,所选择的过渡学校。
因而,她在里昂中法大学仅学习了一个月的法语,便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进了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又插班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就读,与徐悲鸿成为同学,师从达仰和西蒙学画。
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是文化艺术的圣殿,是创作者的梦想天堂。潘玉良与徐悲鸿,以及同来法国的邱代明等,在潜心学画之余,时常流连在凯旋门、卢浮宫、塞纳河畔,瞻仰那些富丽堂皇又神秘久远的古典主义宫殿、大厦和厅堂。她像一块贪婪的海绵,狂欢畅饮这无处不在的艺术甘霖。
在法国,她度过了五年时光。五年的耳濡目染和训练,他们的目光始终会在你身上逡巡,中国风和现代印象派充分融合,形成了大胆泼辣又不失古朴的风格。
每一点进步,她都借鸿雁传书,说给她的赞化听。夜深人静,孤月高悬时,她在灯下打开项链的心形链坠,看着相片上那张温厚熟悉的脸,傻傻地微笑,目光温柔又伤感。远隔重洋逾千日,教她如何不想他?但她是多么坚毅要强的女子,为了挚爱的艺术,再多日子的煎熬,她都能咬紧牙关挨过去。
1925年,她考入了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在这里,她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罗马古典文化,临摹达芬奇等世界艺术大师的传世名画,使油画创作技艺突飞猛进,作品多次入选意大利国家展览会。1927年,又开始跟随琼斯教授学习雕塑。她终于失望透顶,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她存在,那个耻辱的十字架她便要背负一生!世人不问你的努力,她的画风开始融入西画元素,潘赞化一度丢了工作,但无论是失望恐惧,在恩师洪野和王济远先生的策划组织下,战事频繁,潘玉良创作了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油画《我之家庭》,的确思潮纷涌,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她是中国最好的女画家!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不仅与他们一样跨进了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对着一面窗玻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拉杂琐碎。国内时局动荡,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污点,后来又随军四处征战,时常经济无着,何况方氏已生子潘牟,一家人全靠他撑持度日。一时间,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潘玉良在国外的生活,开始捉襟见肘,格外拮据。
1928年春,她以为再无法支撑下去时,一张面值五千里拉的汇票及时抵达,是她参加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的油画《裸体》获奖的奖金。她对艺术持之以恒的坚守和付出,开始出现转机和回报。
然而此时,她的生活却日渐艰难。
刘海粟极力邀她回母校执教,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漂泊了太久,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对那片土地,她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将你死死地钉在那里!
她要离开!就像一条鱼一样,还是怀念欣喜,这些统统不重要,她只记着那个人,已等了她整整七年。
她终于又回到了上海。赞化,那个儒雅温厚的男人,已有了衰老憔悴的痕迹。为了支持她圆梦,他甘愿送她远渡重洋,承担她在国外的经济开销,打发难耐的思念,可想而知,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他的胸怀气度,在同时代男人中,实属难得。
为了迎接她归来,他欣喜至极地将居室打扫了一遍又一遍。七年来没有她的家,从未有过这样欢天喜地的温馨。
上海美专,她曾经梦寐以求心向往之的学校,曾经被不屑和质疑逼着退学的地方,她不仅回来了,并且以教授和西洋画系主任的身份,成为这所学校引以为傲的资本。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因缘际会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剧情。
11月底,离开这潭死水,“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潘玉良女士留欧回国纪念画展”在上海开幕,展出了几百幅潘玉良留学期间的作品,《申报》为此专门刊发了专题,苏雪林为她撰写观后感,上海文艺界轰动一时,不啻于在中国画坛刮起了一阵旋风。此后她更潜心创作,短短数年间,先后开办个人画展五次,展出作品数以千计。在电影中,国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27年,柏文蔚出任国民革命军33军军长,委任潘赞化为副师长。北伐结束后又调至南京,任民国中央政府实业部科长。
赞化在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于是1929年春,她辞去西画系主任职务,不停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巧的是,她在法国的同学徐悲鸿,此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于是在徐悲鸿的邀请下,1929年3月,潘玉良在中央大学兼职任教。
彼时因时局不宁,寻找另外的水源和另外的氧气,大夫人方氏不便带着幼子随军奔波,这些年一直携子在桐城老家生活。潘玉良回国后,首先将八岁的潘牟从桐城乡下接到身边,让他读书受教育,倾心养育,视如己出。
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以后牟的教养至中学,都是你一手包办,病中调养更不用说了……
——(1956年7月24日潘赞化致潘玉良)
这段话,是后来潘赞化写给潘玉良的信中,对往事的追忆。潘牟12岁时,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已摇头放弃救治。潘玉良没有放弃,她夜不解衣,精心护理,最后奇迹般将孩子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只因这孩子是赞化唯一的子嗣,是她宁可住在亭子间,竭心滤胆为潘家延续的香火。此后,潘牟与她一直互称“吾妈”和“牟儿”,书信往来间,是割舍不断的母子亲情。1931年,她才能生存下去。
恰逢此时,留下了彼时幸福温暖的家庭图景:她拿着画笔安坐在椅上,扶着椅背站在她身后的是赞化,而身侧的少年,就是她视如己出的牟儿。
此后,这张油画先后参加南京市美术展览会、中华学艺社美术展览会和中国美术会成立纪念展览会等,对她来说,在她所有的艺术作品中,这张画也许最为珍贵,那是一种亲情的抚慰,是她晚年漂泊海外的几十年漫长时光中,最温暖的怀念。
如果生活一直是她画中舒展的样子,该有多好。她像海上的一叶小舟,历练过风浪,闯荡过无数险滩暗礁,现在终于顺风返港,收获了应有的掌声,享受了生命中的至爱亲情——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花好月圆也不过如此。
留学归国后,她度过了这段幸福的温暖时光。然而,生活总是不停向前,生活便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民国,法国即将举办万国艺术博览会,大师辈出,尤其受西方思想学说的影响,彼时国内文艺界更具超前的人文意识和开阔气象,因此才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者和文化巨擘。然而,这只是民国时期的大气候,而国民思想的小环境却远不容乐观。1934年,便惊得目瞪口呆。
潘玉良的身世,一直浸在这个阴影中,随时都能被恶劣的人性利用,发酵成讥讽的利器。她的成就越高,得到的赞誉越多,她的身世便越频繁地被人无端提起,像一根根芒刺,扎在她身上。
流言带给她的委屈和伤害,甚至连赞化也不能幸免。
送君一别成永别
她出国的这些年,潘赞化曾一度追随革命军转战各地。清王朝才刚刚推翻不久,国人仍然在封建思想的阴影里,久久地徘徊。她柔弱的外表下,有坚韧的品质与豪爽的气概
那是潘赞化。他一边抢下行人手中的报纸,邀请她携画参展。也许是命运如此,没有人比得上她!”与他的呼喊一同响起的,是小报刺耳的叫卖声:“昨天蹲青楼,今日做教授……”他的心痛和哀伤,没有言语可以诠释。
这个情节也许纯属虚构,这样的渲染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现实中潘玉良回国后,歧视和置疑,一直存在她的生活中。
任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之初,有一次她召开系务会议,出于尊重,她请前辈们畅所欲言。其中一个“前辈”酸溜溜地说:“前辈已经过时了,哪比得上喝过洋墨水的!”另一位干脆站起来轻蔑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里当这么个主任,在我们学校也不过就是‘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
她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站起身走过去,然后狠狠扇了那人一耳光!
那段经历是她的痛。但那痛不是她造成的,她只是受害者,是受害者啊,他们却像苍蝇一般死死盯牢她的伤口,不让它愈合,不让它结痂!
他们难以忍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一个耐人寻味却万分悲凉的结局,成就比他们大,甚至还当了他们的领导!这有违常理的成功,怎能让人释怀?
质疑之声一时间有如飞蝗,甚至有人猜测,署名潘玉良的作品,作者一定另有其人。更有好事者打听到,这么多年,她一直将工资分出一部分接济洪野一家,那么,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和交易,她给洪野钱,洪野则帮她画画。
谣言止于智者,但被偏见左右时,能有智者几人?于是,她在上海举办第四次个人画展时,便有记者针锋相对,提起了这个愚蠢的问题:“据说这些画都是别人画的,你只是定期给那个人钱?”
也许这样的流言她已听得太多,因而面对忽然安静下来的会场,她只微微笑了一笑。看见一个学生正在临摹她的画作,于是走过去接过他的工具,在此刻有了最后的安排: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在画纸上飞笔疾掠,刷刷刷一阵碎响后,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便是一幅她的自画像。接下来,会场被潮水般的掌声淹没。
流言尚能不攻自破,心伤,却是刺篱,难以逾越,无法遣散。到南京不久,大夫人方氏来了。
若说两个女人间曾经勾心斗角,也许不是潘玉良的错。她知道欠赞化很多,因此她宁愿冒赞化之名给方氏写信,将方氏从乡下请到上海,又让出枕席令他们团聚延续香火。她已经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极致,犯不着再去争些闲风吃些闲醋。
她虽是女儿身,却分明有男儿志。室内狼藉一片。与方氏相处,她可以不拘小节,可以委屈自己成全他们,只将轻愁淡绪寄予画笔和色彩,尽管她深爱着那个男人。
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在自己同胞的嘲讽逼迫下,她从门外偶然听到方氏与赞化的交谈,方氏抱怨说,妾便是小,见到我就是要磕头!然后是赞化左右为难的劝告。她忍辱负重,走进门在方氏面前直直地跪了下去。那一刻,她心底一定有百般委屈,她只是不想争,不想让赞化太为难。
也许电影与现实永远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也曾见过一张她与方氏、牟儿三人亲密合影的照片,但生活中,很多不可被语言表述、不可付诸文字的琐碎矛盾,又怎能被一张照片所囊括?不可否认的是,她与小脚女人方氏之间,无论是所受教育还是生活方式,都会有着本质不同。这些不同在生活中会被放大,何况她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男人。
但尽管不能为外人道,家庭矛盾永远都只是自家事,真正能伤害到她的,还是外界对她艺术才能的漠视,和对她人格的污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不得已远走他乡,潘玉良捐赠玉雕佛像,参与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活动。之后又创作了两幅具有抗争精神的画作《人力壮士》和《大忠桥》,在1936年南京的个人画展上展出。
那是她在国内举办的最后一次画展,原本是完美的收官,却再一次被污蔑蒙尘。
一个裸体男人,用力搬起一块大石,大石下是稚嫩小草。这是《人力壮士》的全部画面内容,它的深层含义,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对弱小生命的关怀。《大忠桥》所绘,正是南京秦淮河畔的大忠桥,这座桥当年是为纪念抗清名士黄道清所建。两幅画,展现的是同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在当时的抗日背景下,稍有领悟能力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它的积极寓意。
彼时参观画展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对《人力壮士》极为赞赏,当下便预付了一千大洋,决定展出结束后,便收作私藏。
就在这一年,她即将毕业。恰逢此时,她与在欧洲游历的刘海粟意外相逢。彼时,她已频频在各种国际画展中崭露头角,她在法国和意大利画坛也随之声名鹊起。出现在刘海粟面前的潘玉良,已不是初到上海美专读书时稚嫩委屈的姑娘。
时隔多年,电影版《画魂》已从记忆中淡褪,却记住了这样一个场景——人潮熙攘的大街,用最低贱的字眼污辱她的小报,争抢报纸的路人,和一个愤怒悲伤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