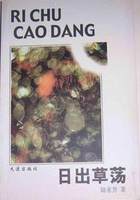雪花的快乐
关于陆小曼,梁启超的一番话说得真是透彻。他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破天荒地将二人训斥了一顿,随后将此事写信告诉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忠说:“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那人当头一棒,盼望她能觉悟(但恐也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梁先生的担忧绝不是多余,事实上,他的当头棒喝并未阻止事态的发展——徐陆婚姻不仅成了他们爱情的坟墓,也确实带给徐志摩无限痛苦,甚至,最终导致了英才早逝的悲剧。
梁启超对陆小曼的印象,简直差到无以复加。不能怨老先生刻板严厉,恕我直言,徐志摩身边的三个女人,我最不愿付诸笔墨的,也是陆小曼。
诚然,她也算是绝代女子,知性妩媚、风姿绰约,还有一颗灵敏的艺术之心。1903年11月她出生于上海,世代书香,父亲陆定为北洋政府赋税司长,自小便熟读经典,精通英法语言,在绘画、戏剧、音乐等领域造诣颇深。
她与林徽因一样,是上流社交圈叹为观止的奇葩,但林徽因更具大家闺秀的内敛含蓄之美,可以高贵若明月,也能低调如尘芥。陆小曼缺少的,是一份沉静矜持,和坚守的韧性。
她喜欢热闹,耐不住寂寞,喜欢众星捧月繁花似锦的生活。林徽因考察各地建筑时历尽艰辛吃尽苦头的日子,若换作陆小曼,很难想象她能坚持几日。她为交际而生,说白了她其实就是一朵交际花,当时有一句评论是:“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也就是所谓以美艳著称的“南唐北陆”。甚至她在北平与徐志摩的邂逅,也始于一场热闹的舞会。
因而1924年底徐志摩与她的相遇,该是一场错误的邂逅。彼时,失恋的徐志摩遇上了耐不住寂寞的陆小曼,他们爱情的根基能有多牢固,只有天知道。
她结婚已两年有余,夫君是当时的军界才俊王庚。王庚,字受庆,先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8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在北洋陆军部供职,并成为梁启超的学生。1922年,陆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庚结婚。
应当说,嫁给王庚,对陆小曼来说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她与徐志摩的婚外恋闹得满城风雨,直至离婚与徐志摩结婚,王庚都显示了包容忍让、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从性格志趣,到气质态度,她与王庚都明显不同。王庚是有为青年,醉心于事业,少了些儿女情长;陆小曼正相反,她沉醉于浪漫狂热的爱情,追寻甜蜜诗意的人生幸福。徐志摩的出现,正好与她两相契合。但生活,又岂能分分秒秒都在蜜罐里泡着。
同样师从于梁启超,王庚与徐志摩算是同门师兄弟。认识陆小曼时,徐志摩回国已有一年多时间。梁思成携林徽因出国留学,他心仪的女子留给他的,是一个永不转身的背影。他孤独痛苦,又正逢单身,于是便常去陆家找王庚。
王庚总是很忙,便对徐志摩说:“我今天比较忙,让小曼陪陪你吧!”逢到陆小曼要他相陪外出,王庚也总说:“我没空,让志摩陪你去吧!”这王庚,也真是榆木疙瘩一块。他看不透徐志摩的孤单,也读不懂陆小曼的寂寞,因而他和陆小曼婚姻的失败,谁对谁错,都谈不上绝对。
陆小曼后来回忆与徐志摩的相恋,强调了当时志摩积极阳光的精神力量,对自己的照拂与吸引。
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在骗人骗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
——(陆小曼《爱眉小札·序》)
1925年,王庚调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离家北上赴任。他走后留下的自由空间,像熏风撩拨的原野,火速催生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对徐志摩来说,他一直以来飘荡无着的情感,终于有了依附,得到最完美的释放。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飏,飞飏,飞飏,——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凉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飏,飞飏,飞飏,——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飏,飞飏,飞飏,——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在与陆小曼恋爱时创作的诗,《雪花的快乐》算是比较纯净的一首。也许,陆小曼是他经历的所有女人中,最能迎合他热情的一个。张幼仪是封建婚姻下他娶回家传宗接代的女人,他浪漫的心从未向她敞开过;而林徽因,是最能与他灵魂共振的红颜知己,却如一朵高山雪莲,始终与他若即若离;只有陆小曼,像一团火,妩媚地接纳他的热情,从灵魂直到肉体。因此他们之间的相恋,使他明白了“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他充满了感恩的快乐。
郁达夫曾评价他们的恋情:“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偶合在一起,自然要发出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一个风花雪月的单身男子,一个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他们的恋情一开始便不被祝福。
大约彼时陆小曼在坊间的名声并不太好,风言风语四处飘散时,便格外不堪入耳。热恋中的情侣管不了这些,徐志摩以为,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他的“小龙”,只要她奋发,那么她要获得艺术成果,只如探囊取物,到那时,一切流言都只是庸人自扰。
从一开始爱上陆小曼,他便存了激励她的心。她美丽温婉,富有才情,这是他爱上她的理由。他相信爱情的力量会让她觉悟,假以时日,他们会各有进步,那么这段被人诟病的婚外恋,便有了积极意义。
现存徐志摩最早写给陆小曼的信,大约是1925年2月2日的那一封。他在信中说:
龙呀!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的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的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的势利的(一般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等到那一天实现时,那不仅是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荣耀哩!聪明的小曼,千万争这口气才是!
——(徐志摩致陆小曼)
“翡冷翠一夜”,应是他们最初的定情时刻。多年后他们情感龃龉不合,徐志摩痛心地写信问她:“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彼时的松树胡同七号,也是新月社的活动场所。那一夜他们在墙角的“亲别”,是最浓酽的烈酒,即便有毒他们也尝了,尝了便再也不愿丢开。
纸包不住火,王庚到底还是知道了真相。对于博学多才、年轻有为的警察厅长王庚来说,这自然是一桩奇耻大辱。无论王庚有怎样的涵养,争吵总是无可避免,这段婚外恋情于是彻底曝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文化圈,简直是头号新闻。徐志摩为避风头,也为了践行与泰戈尔的邀约,于3月10日启程赴欧,开始了历时数月的出国旅行。
对徐志摩的思念,让陆小曼度日如年。这段日子的分离,徐志摩与陆小曼饱尝了相思之苦,往来书信也越发忧伤缠绵。
真的龙龙,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遍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咳,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药在近旁,此时你我竟许早已在极乐世界了。说也怪,我真的不沾恋这形式的生命,我只求一个同伴,有了同伴我就情愿欣欣的瞑目;龙龙,你不是已经答应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吗?我再不能放松你,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诗;你完全是我的,一个个细胞都是我的——你要说半个不字叫天雷打死我完事。
——(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致陆小曼)
这恼人的春色,更引起我想你的真挚,逗得我阵阵心酸,不由得就睡在蔓草上,闭着眼轻轻地叫你的名字(你听见没有?)。我似梦非梦地睡了也不知有多久,心里只是想着你——忽然好像听得你那活泼的笑声,像珠子似的在我耳边滚,“曼,我来,”又觉得你那伟大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往嘴边送,又好像你那顽皮的笑脸,偷偷的偎到我的颊边送了一个吻去。这一下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喘,难道你真回来了么?急急的睁眼一看,哪有你半点影子?身旁一无所有,再低头一看,原来才发见,自己的右手不知在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左手,身上多了几朵落花,花瓣儿飘在我的颊边好似你的偷吻似的。
——(1925年5月11日陆小曼的日记)
——咳,我这一想起你,我唯一的宝贝,我满身的骨肉就全化成了水一般的柔情,向着你那里流去。我真恨不得剖开我的胸膛,把我爱放在我心头热血最暖处窝着,再不让你遭受些微风霜的侵暴,再不让你受些微尘埃的沾染。曼呀,我抱着你,亲着你,你觉得吗?
——(1925年6月26日徐志摩致陆小曼)
然而此时,事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已调上海任职的王庚,发来了一封“爱的美敦书”,声称如果小曼再不肯去上海团圆,便永远都不要去了!他爱陆小曼,只是爱的方式与徐志摩不同,因而在痛苦的抉择后,他向陆小曼下了最后通牒,希望她尽早与他团聚,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
面对父母的催促,她决定以死相逼,可是父母早有准备,只一句“好的,要死大家一同死!”便将她的意志全部摧垮。无奈之下,她只能向父母屈服,流着泪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诀别信:“你我的一段情缘,只好到此为止了,此后我的行止你也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你只要记住那随着别人走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1925年7月底,徐志摩终于回到了北京。权衡再三,他请刘海粟出面当说客,替他向陆家父母及王庚争取小曼的自由。
9月初,陆小曼一家南下不久,徐志摩也去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刘海粟便在功德林餐厅摆了一大桌,宴请小曼母女、王庚、志摩以及唐瑛、李祖法、杨杏佛等人。这场宴会别具深意,彼时,唐瑛、杨杏佛、李祖法,同陆小曼、王庚、志摩一样,都是三角恋情的主角,一眼便知,这是一出撮合一对便要劝散一对的情感大戏。
刘海粟拿捏得极有分寸,巧妙委婉地让大家讨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的问题。这个话题摆在桌面上说开来,虽然各人心思有别,却都默认了刘海粟的说法,彼此相持不下的情感僵局,也有了缓和的趋势。
10月,徐志摩回京接编《晨报副刊》。某天清晨,陆小曼忽然出现在他办公室,气喘吁吁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志摩,我和王庚离婚了!”
那一刻,仿佛天地轮转,世间什么样的幸福,都比不得这对情侣苦尽甘来,得偿所愿。
但幸福,往往只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才最刻骨。当水到渠成,所有艰辛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最美丽的一朵,余下的时光,便是萎谢和老去。
1926年,硖石镇徐家为徐志摩婚姻的变故,分了家产,最终也同意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把喜讯报给在北京的陆小曼时,徐志摩抑制不住激动在信中附了一首诗:
我心头平添了一块肉,这辈子算有了归宿!
看白云在天际飞,听雀儿在枝头啼。
忍不住感恩的热泪,我喊一声天,我从此知足!
再不想望更高远的天国!
——(徐志摩《再不想望高远的天国》)
张幼仪作为当事人之一,彼时也去了徐家。后来她回忆说,她看到徐志摩手上戴着一只醒目的翡翠戒指,那是陆小曼送给他的定情物。当徐申如征询她的意见,是否反对徐陆结婚时,她沉默片刻,说了句:“我不反对。”徐志摩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就在那一刻,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忽然飞出了窗外,他匆忙下楼去找,却再也没有找到。
无论如何,这个小插曲对这段新恋情,总有着不吉的暗示。一丝预感藤蔓一样在张幼仪心底往上爬,她恍惚觉得,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也许并不能如意终老。
爱情被婚姻逼进了坟墓
婚姻,是徐志摩与陆小曼情感生活的分水岭。
之前,他们艰难地爬一座山,那么高那么远,看不到峰顶,可是他们心甘情愿牵牢了手,彼此不弃不离;如今翻越了山巅,阅尽了旖旎风光,便是下山的时候了。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可悲的,竟是那么恰切。
1926年10月3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了艳极一时的婚礼。现存的一帧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上的合影,已光影斑驳,一对旧时光中的新人仍然是醒目的主角。陆小曼手捧鲜花欠身而坐,长长的披头纱轻轻曳地;她身侧,站着长袍马褂的徐志摩,嘴角有淡淡笑意。
那一刻的幸福毋庸置疑,但婚礼前谁也不曾料到,证婚人梁启超会用那样出格严厉的证婚词,将二人训斥了一顿。
做这对新人的证婚人,梁启超一定很不情愿。他对陆小曼没有好感。徐志摩虽然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却追求过他的准儿媳林徽因,不能说他一点都不介怀。但徐申如当时给出的结婚条件是,必须由胡适当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因此,尽管梁启超并不赞成他们的婚姻,到头来却抹不开情面,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但有些话,他憋着难受,作为梁启超的恩师,他也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学生说一番掏心掏肺的真心话。
梁启超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这是一篇空古绝今的证婚词,当时宾客的反应,正如梁启超给家人信中所写那样,“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梁启超对徐陆婚姻一定是不满到了极致,因而在写家信时,痛惜忧愤仍未平息:
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作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那人当头一棒,盼望她能觉悟(但恐也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怕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了。……品性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
——(梁启超致子、媳)
他训斥的是徐志摩,其实他更想骂的是陆小曼。一个彩蝶儿般周旋于社交场所的女人,他不屑而厌恶。此刻我想说,老先生真是眼光独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担忧的结局,几乎都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