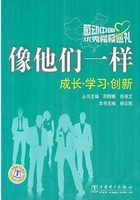我的人,倘若这时节我在你身边,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想起你种种好处,我自己便软弱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你生了我的气时,我便特别知道我如何爱你。”现在你并不生我的气,现在你一定也正想着远远的一个人。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1934年1月15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
念着他生命中深爱的女人,漂流在生命中重要的水上,这种境遇,多么令人感慨。十多年前,他走出凤凰小县,经由这条水路来到了外面的世界。那时,他身无长物,前路未卜,只有忧愁和不甘。而今,漂流在同一条水上,他已不是从前那个愁绪满怀的少年,他有了取暖的文字,他有了三三。
风大得很,我手脚皆冷透了,我的心却很暖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心里总柔软得很。我要傍近你,方不至于难过。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机会。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三三,一个人一生最美丽的日子,十五岁到廿岁,便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你想想看,是怎么活下来的!万想不到的是,今天我又居然到这条河里,这样小船上,来回想温习一切的过去!更想不到的是我今天却在这样小船上,想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且这个黑脸的人儿,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着我!我的命运真太可玩味了。……爱我,因为只有你使我能够快乐!
(1934年1月16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
1月18下午,沈从文终于抵达辰州,离凤凰更近了。辰州对他有不一样的情感,这片土地接纳并埋葬了他的年少时光,他的人生从这里起航。在辰州,他做过很多泡沫般的梦,包括将来当一名将军,包括为白脸女孩写诗。十多年后,他却成了一名作家,并痴狂地爱上了一个黑脸女孩。人生,有多少玄妙的联系?
三三,我已到了“柏子”的小河,而且快要走到“翠翠”的家乡了!日中太阳既好,景致又复柔和不少,我念你的心也由热情而变成温柔的爱。我心中尽喊着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儿,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我到家中见到一切人时,我一定因为想念着你,问答之间将有些痴话使人不能了解。也许有人问我:“你在北平好!”我会说:“我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平也很好!”
三三,昨天晚上同今晚上星子新月皆很美,在船上看天空尤可观。我不管冻到什么样子,还是看了许久星子。你若今夜或每夜皆看到天上那颗大星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粒星子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了一些。因为每夜这一粒星子,必有一时同你眼睛一样,被我瞅着不旁瞬的。
(1934年1月19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
一段情,历经时光烟尘而犹显珍贵,可作见证的,情书便是回忆的镜子。1929年,鲁迅曾向许广平引用过韦丛芜的传言,说起作家高长虹追求冰心,“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真让人莫衷一是。
心悦君兮君不惜,即便如此,也请怀一份珍重心。可以不惜那个爱你的人,又何必将那人的情书作为表忠心的筹码,交给自己的男人当作笑话欣赏,又像扔垃圾一般弃之大海?世间万般皆因果,面对一段情缘,哪怕非己所愿,也用一颗低婉沉静感恩的心,尊重那颗心的付出,且如慈悲佛,去作善意的消解。清风长天,无碍无牵。
所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是命运对彼此的恩赐,两情相悦,相伴终生,多么美好。尽管生活有这样那样的插曲,尽管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只是童话的虚构,但人生从来就不是独幕剧,一段情感,只有经历悲欣交集,跌宕起伏,沉潜下来如深流的静水,才是最可靠的浪漫。
此后他们的日子,虽是四季轮转,却总有一个春天,始终在那里。
为了与你接近,我同这个世界离开
她最初是被他的情书打动。当然,如果这也算一种设计,那么也许,中一万次这样的设计她也愿意。
毕竟,人世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将文字当作温柔的利器。
而最为关键,是他们对彼此的情感,没有人可以替代。
她曾是中国公学夺目的奇葩,彼时追求者众,包括王华莲所透露“一个国民政府派出留学日本”的优秀青年,还包括吴晗——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她只接纳了沈从文,是被他的执着深情感动,也因爱了他的才华,他文字中的富有让她动容。
他的文章是要给全世界人读的,却只款款深情为她一个人写情书。自然,这样的人,连孤傲的名门闺秀张兆和都可以征服,不可能没有人爱。即便在他自甘沦为奴隶,疯狂追求他的黑脸美人时,也有女孩甘愿为他做奴隶。
后来,他遇到了高青子,和生命中的几个“偶然”。她们无一例外仰慕他的才华,况且他又那么儒雅潇洒。当文学女青年高青子刻意模仿他小说中女主角的穿着,含羞站在他的面前,那一刻,他有瞬间的迷失。甚至,这杂草般生长的复杂心绪影响了他彼时的创作,因此有了《看虹录》和《水云》中的“偶然”。
有人说,有了婚姻,便没有了爱情,说原本有爱的人一旦长相厮守,不过是相濡以沫,相厌到老。但人生处处有相逢,不可能永远如初见。真正的情感,必是经过了险滩,才有资格说浪漫。
紫陌红尘,婆娑世界,许多嫣然诱惑,是多情人的劫。几十年的婚姻生活,时光会淡褪了初始的颜色。但即便瞬间分心,他顷刻也会像茫茫人海迷路的孩子,惶恐而无措,他怕从此丢失了他的女人。这个世上,哪怕只有一条坎坷小径可以通向爱人,他也会从千万条路中纷披而去,跋涉到她的身旁。
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接下来的日子,是生活最朴素的样子,柴米油盐,生活开销,外出谋生,当然,一旦分开,便是情深意切的家书往来。
只是这平静也变成了奢侈。抗战爆发,满城硝烟,每日身处危城,生活只剩下安全地活着,满纸柔情也转成琐碎叮咛。他被迫外逃,她则滞留北平,带着孩子,在刀锋上煎熬。那段日子,今日的我们不可想,活下来,已是万幸,她却在写给二哥的信中,只为毁于战火的情书叹息。
生活,将他的小女人,变成了“小妈妈”。尽管花期已过容颜渐老,这情,却始终是温暖的。当初明烈的痴狂,如已逝的青春,不再光泽耀眼,然而在岁月中淬火的爱,合成了包容、患难、亲情、关怀和精神共鸣,倒比激情更长久,比狂热更深沉,变成了历久弥坚的一份柔韧。
战争,让他们天各一方分离了一年多时间。1938年11月,逃出北平的张兆和终于在云南与丈夫团聚,此后直到1946年回到北平前,昔日张家的三小姐变成了最坚强的主妇,使危城之下的小巢,总有家的温暖。沈从文回忆在云南呈贡时的生活曾说:
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抗战结束,沈从文从昆明转到北大教书,一家人的生活也渐有起色。但更大的劫难转瞬即至。1948年,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斥反动文艺》,给沈从文贴上“桃红色作家”标签,指责他“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全面否定了沈从文创作的意义和成果,是一次彻底的批判和颠覆。
心情极度苦闷,这年暑假,沈从文与友人在颐和园附近的霁清轩度假。书信,再次成为二哥和三三倾诉的通道,和彼此的慰藉。
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
我回到中老胡同,半夜睡不着,想起许多事情:第一是你太使我感动,一切都如此,我这一生怎么来谢谢你呢?
……
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要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真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
……
小妈妈,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更感动的是在云南乡下八年,你充满勇气和精力来接受生活的情形,世界上那还有更动人的电影或小说,如此一场一景都是光彩鲜丽,而背景又如何朴素……
(1948年7月29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
影响沈从文一生的,若论伤害最大,当属郭沫若。那篇批判文章发表后,在左翼思潮狂热高涨的形势下,沈从文首当其冲成为批判对象。最令他心痛的,是他教过的学生在校园内张贴标语,抄录郭沫若的批判文章,口口声声要“打倒”他。
沈从文一生情感丰沛,对事物的感知充满敏锐的灵性。他的文章极少涉及政治,他只抒写内心情感、乡土自然和人间真情,他不明白,曾有那么多爱他的读者,为何转眼间他就成了被批判的反动作家?他开始精神恍惚,几近崩溃。
在梁思成的建议下,征得家人同意,他搬入清华园调养。前途未卜,生活也愈发艰难,张兆和强忍压力,频繁在信中劝慰安抚沈从文。
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
(1949年2月1日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的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溃,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的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1949年2月2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
此时,在一位时任东北野战军将领、张兆和昔日校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张兆和决定去华北大学进修学习,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精神恍惚的沈从文听此消息,无疑是惊弓之鸟,他以为,连他最爱的女人,也将抛弃他了。
他可以经受物质的山穷水尽,唯有精神的折磨,能击中他的要害。记得十多年前的初秋,彼时他身在青岛,心却留在了苏州,那脸儿黑黑的小女人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他多么幸福。他想歌唱,便将心底的歌写在了《月下小景》中:
有翅膀的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没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飞入你的心里。
我不必问什么地方是天堂,我业已坐在天堂门边。
现在,他觉得是时候放弃生命了,他认为只有自己解脱,一家人才有生路。此刻,他想念生养了他的湘西土地,想念沱江和沅水,他想带着人世的爱,重回天堂。
3月28日,处于崩溃边缘的沈从文一边喃喃自语:“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一边用剃刀割破颈部和手腕脉管,之后又喝下了煤油……
他未能自杀成功,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救了他。醒来后,精神的恐惧和恍惚也愈发严重。他最担心的,就是张兆和会离开他。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