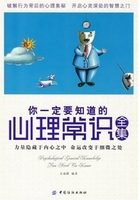三、清除孝道文化中的糟粕及负面影响
现在,我们还处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观念,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不能割裂传统,都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推进社会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伦理文化,而“孝”,又是中国全部传统道德的根本和核心。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过去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作为工具利用时,已经被政治化了,异化了,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与孝的最初的提倡者的初衷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天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缺陷是那样的明显。因此,我们必须清除孝文化中的糟粕和负面影响,吸收其有益的精华成分,传承和发扬民族孝道文脉,以建立当代新型的孝道文化,使之服务于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张岱年提出,评价学术思想包括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有两条标准:第一,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第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天对孝道文化的评判正是运用这两条标准去进行的,既注重伦理道德本身的标准,又注重社会历史的标准。其实,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开始了对旧道德的猛烈抨击,其中又主要是对“三纲”的批判。***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总出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是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孔门的理论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们自己以奉养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又说:“中国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之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北京大学教授吴虞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家庭制度和孔子孝道学说:“孝教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他指出“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认为“儒家之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封建统治者竭力倡导孝道,他们自己并不认真执行,为夺皇位弑君弑父的事并不少见。朝廷上,白发苍苍的老臣俯首躬腰,听命于稚气十足的幼主,幼主视老臣为奴仆,十足地表现了统治者提倡孝道的虚伪性。汉代以后,历朝统治者对孝都过于强调服从。他们强调忠君,强调统治阶层的绝对权威,“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民只有尽忠尽孝的职责,只能遵守繁缛刻板的礼仪,“孝”多流于纯粹的形式而失去初始的本意。古代社会的养老敬老,涉及的对象局限于那些退休的达官显宦、耆旧老臣,而不能普及到一般百姓,这就使“孝”打上了官本位的阶级烙印,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秦汉以后,“父慈子孝”的美德由于父权思想至上,“父为子纲”的伦理逐步掩盖了“父慈”,到了宋明时期,孝而必须顺从的思想又有了大发展。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只有不是之儿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鼓吹“愚孝”的教条,便散播于天下。这种教条片面要求儿女辈尽孝,而父辈则享有绝对的尊严,长辈要求晚辈绝对服从,百依百顺,表现为家长专制主义。在父权至上的社会制度下,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是权威式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单方面的,不但严厉,而且苛刻,子女对父母往往是敬畏多于敬爱。在早期儒家思想中,父子双方都承受着道德义务,双方分别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大学》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这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礼运》亦言:“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思想到后来都因“治天下”的需要,被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家们改造了。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封建的孝道观,认为这些旧观念禁锢了青年的思想,违背了人的天性。“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鲁迅对此评论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由于“三纲”的倡导和实行,在古代中国社会和家庭中,长期以来缺少平等民主的意识,父母忽略了两代人生命进程的差异和个人意志的独立性,以过来人和智者的姿态,对子女管束太多太严,子女的个人自主性在家庭中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有志气有己见的子女想要尽孝道,就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里”。
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顺手偷羊,子女不可揭发而要尽力掩饰隐瞒,父子相互隐恶,孔子认为这是一种“直率”。《礼记》也宣扬对先辈要绝对盲从,隐恶扬善。《礼记·檀弓》中有所谓“事亲有隐无患”的原则,《礼记·祭统》对此又有更明白具体的阐述:“先祖才,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这实际上就是把隐先祖之恶、扬先祖之善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孝子孝孙、是否是贤者的标准。为了“孝”,人们可以徇情徇私枉法,而牺牲国家和他人利益,这其中隐喻着人们必须接纳、宽容某种丑恶和阴暗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情怀,它影响着民族的文化心理。隐恶使父子均“陷于不义”,应是不孝;顺从父母,不能是无原则歪曲事理的绝对服从。中国过去是一个人情社会,如今要成为法制社会,人情,包括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必然要面对法制的挑战,具有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服从真理和法律,这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伦理化,把世间一切问题、一切是非判断都归之于伦理纲常,太强调孝道,过犹不及,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礼记·祭义》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敬,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孝”成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一个人能尽忠职守,遵守一切道德礼教,便是孝子,否则便是“非孝”;“孝”成了一切道德的总汇,也成了人们沉重的精神负担,因为孝与忠相连,不孝也就不忠,最终成为“不忠不孝”之人。顺从父母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也算是一种孝行,如清初魏禧说:“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这就叫“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父母有随意处置生命之权,并且要求“子不当怨”,这完全没有把子女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一个“人”来看待,当然更说不上人权和人的尊严。尊敬父母,讨父母欢心是人之常情,但变态的“悦亲”、“娱亲”又是令人反感的孝行。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虽然你的行为对象不是父母,但只要令父母悲伤难过,就是“不顾父母之养”,都是不孝。所以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感慨:“少小时,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做孝子,比想象“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鲁迅说,在《二十四孝图》这本孝子的教科书中,他最不解和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行孝是这样地“妨碍生命”,这些孝子故事又是“如此虚伪”,“本来谁也不实行”。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商代以来,孝文化中强调“厚葬”,大肆铺张,繁文缛节,其陈规陋习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孝的词语与葬俗有关:如孝子、孝服、孝衣、穿孝、戴孝、披麻戴孝、吊孝、挂孝、执孝、哭孝、守孝、重孝、脱孝、谢孝、出孝等等,一个“孝”字,成了对长辈丧葬及哀悼的代名词。这与西方丧葬文化中的简约形成了鲜明对比。厚葬,除了远古时代形成的“灵魂不死”观念外,儒家孝道和先人荫庇后代之类思想也起了明显的作用。丧礼是否隆重和符合旧规,是衡量子孙尽孝与否的标志。舆论、习俗的压力使丧葬礼仪复杂铺张。显然,“厚养薄葬”是应该继续倡导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