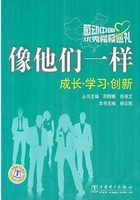与庄存与的整个经学思想相应,《春秋正辞》所说的圣人之道也就是尧舜之道。庄存与说:
然则《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乐道尧舜之道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天子辞第二》卷二。)《春秋》制义,以继王迹。(庄存与:《春秋正辞·禁暴辞第七》卷九。)
《春秋》之义就是承继尧舜诸圣王之迹,阐发以文王为代表的尧舜三代圣人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就其内容而言,不过是规范君臣父子伦理的礼义,故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一再声称《春秋》是礼义之大宗:
君子作《春秋》,起教于微眇,其奚待流逴荒亡,为诸侯忧,而后讥其重乎?故曰礼义之大宗,所为禁者难知矣。(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中》卷四。)
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伦,要在于《春秋》,故曰:礼义之大宗也。(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
《春秋》礼义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
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其说出自西汉的司马迁。而司马迁之说本于董仲舒。(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春秋之时天下大乱,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绝于书,故《春秋》不是正面地阐述礼义,而是“所记败乱多矣”(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一,第2页。),“《春秋》诛乱贼,义有所辟,辞以诛之,未有但已者”(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春秋》考成败,录祸福”(庄存与:《八卦观象解下》,第22页。)。《春秋》主要是对当时各种违背礼义的言行的批评,并且通过诛讨乱臣贼子来说明礼义,故对《春秋》的理解要从孔子所讥来认识,所谓“《春秋》乐道尧舜之道,察其所讥,尧舜之道存焉”(庄存与:《春秋正辞·禁暴辞第七》卷九。),而“不知孔子作《春秋》,何以为王者之事?何以为乐道尧舜之道?”(庄存与:《系辞传论》,第41页。)孔子正是通过对乱臣贼子的诛讨,阐明了他所要说明的圣人之道以及君臣父子所应遵守的礼义大宗。所以,庄存与不仅在书中以诛讨乱臣贼子为中心内容,而且专列《禁暴》、《诛乱》二篇,再三强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者,必陷篡杀之名”(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要求君臣父子都必须以《春秋》为教科书,从中体会礼义的规范,领悟圣人之道,才能不失为君臣父子;否则,就将有君臣父子之间的篡杀等种种恶行发生。他对《春秋》的这种基本认识,与董仲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公羊》学认为,《春秋》的圣人之道是通过孔子的特殊笔法来体现的,要了解《春秋》的圣人之道就必须明白圣人的笔法。自《公羊传》以后,董仲舒、何休及其后儒对《春秋》的笔法都多有发明,但是,用所谓《春秋》笔法并不能对《春秋》的所有内容一一作出令人满意的解说。如,《春秋》昭公十三年,“冬,十月,葬蔡灵公”,蔡灵公有弑君父的大罪,“般也生死无所容于天地”,按照《春秋》笔法对蔡灵公是不应书葬的,但这里却有书葬之文。《公羊传》无解,何休虽然对此有所解释(何休的解释是:“书葬者,经不与楚讨,嫌本可责复仇,故书葬,明当从诛君论之,不得责臣子。”《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23页。),但是,庄存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之所以书葬是因为“蔡不可绝,故过而予之也。《春秋》有过辞乎?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春秋》之过,虞帝之过也”(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在这里,庄存与承认《春秋》的笔法有所谓“过辞”,也就是承认言辞总是具有不能穷尽义旨的局限性。承认《春秋》有“过辞”,而不是把《春秋》之辞与圣人之道牵强附会,这是庄存与的高明之处。因此,较之许多《公羊》学家尤其是晚清的《公羊》学家,庄存与对《春秋》的解释较少有附会的成分。
庄存与承认《春秋》有“过辞”,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春秋》之道的绝对性。他提出《春秋》之法与其所表现的圣人之道之间,有有穷与无穷的区别:
《春秋》……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
《春秋》讨贼也,正名而已矣。我无加损焉。名穷于不可正加一辞焉,而弑君之贼无所容于天下万世,故曰:法可穷,《春秋》之义则不可穷。(同上。)
《春秋》用来诛讨乱臣贼子的笔法、文辞有限,因此,难免有“过辞”,但是,孔子却通过有穷的笔法、文辞,阐发了无穷的圣人之道。即使是《春秋》的“过辞”,也不是真正的过错或是对罪过的肯定,而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类的虞帝圣人之过。这种所谓“过辞”,实际上是圣人在特殊情形下,以“不经”的形式所表达的圣人之道。因此,绝不能因《春秋》的笔法、文辞有穷,有所谓“过辞”,而怀疑圣人之道的无穷。较之某些《公羊》学者甚至将《春秋》的文辞也说成绝对完美无缺,庄存与的说法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而他所说的圣人之道无穷,包含时空的双重含义,从空间说适用一切国家,从时间上说万世通用,故庄存与说,“《春秋》万事之权衡也”(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能够传之万世而不乱。这种肯定《春秋》之道或是《春秋》之义无穷的观念,使《春秋》学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对现实指导意义的永恒价值,为《春秋》成为万古不变之经提供了理论依据。
3与《公羊》学的异同
《春秋正辞》的基本思想是以《公羊》为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要真正理解《春秋正辞》,必须具体地说明《春秋正辞》究竟吸收或舍弃了《公羊》学哪些思想,其吸收有何不同之处,其舍弃有何意义等。我们可以从由构成《公羊》学哲学的孔子改制说、政治学的大一统说、历史学的三统说三世说这三大内容来作一分析。
首先,关于孔子改制说。汉代《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由三个论点组成,一是孔子素王说,以孔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二是孔子王鲁说,以孔子缘鲁以言王义;三是《春秋》新王说,以《春秋》为改制的“俟后”之作。而庄存与对这三个论点几乎都没有吸收。
庄存与虽然承认孔子受命于天的圣人,但却不讲孔子素王说。他说:
大哉受命!钊我至圣,弗庸践于位,皇惟飨德,乃配天地。(庄存与:《春秋正辞·叙目》。)
庄存与承认孔子受命于天,具有德配天地的崇高地位。可是,他只说德配天地的孔子为至圣,即圣人之极,而不说孔子是受命于天的素王。只称孔子为至圣,而不说孔子是素王,是庄存与与《公羊》学在孔子素王说上的区别。
对于王鲁说,庄存与在释隐公七年“滕侯卒”及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时说:“滕侯、薛侯,《春秋》当新王也,滕子、薛伯,亲周也,《公羊》家识之矣”(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这里虽然有涉及《公羊》学的王鲁说的含义。但是,庄存与只是说《公羊》家有此一说,而没有明确刊登其说。而他在许多《公羊》学讲的王鲁地方,都不仅不采其说,反而予以否定。如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附盟于篾”,何休是用王鲁之说为解,认为此条是孔子王鲁的笔法体现,而庄存与则是用隐公有违孝道来解释,认为是孔子对鲁隐公的批评(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中》卷四。)。又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何休说:“所传闻世,外离会不书,书内离会者,《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庄存与则说:“欲公修鲁公之法,而谨诸侯之度也。实逼处此,度外置之,治内治外之谓何也?”(庄存与:《春秋正辞·外辞第六》卷八。)认为此条之义不是说王鲁,而是要求隐公谨诸侯之度。又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说:“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庄存与则说:“《春秋》之辞,于我君曰公薨,于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于君亲,而不贰其敬,义之大者也。岂曰托王于鲁哉?”(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以为此条之义也非王鲁说,而是讲的亲亲之道。这说明庄存与对王鲁说,基本上是予以否定的。
庄存与有“《春秋》当新王也”(同上。)之说,但此说是以《春秋》继承了尧舜三代圣王之道,而使后世新王有所遵循的万世不变的大法,所谓“当”只是“相当于”之义,而不是《公羊》学说的《春秋》是孔子以素王身份,为继周的新王所立之法。同是《春秋》新王说,《公羊》学强调的是《春秋》改制的意义,而庄存与则讲是对尧舜三代圣王之道的总结。他说:
《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孟子有言《春秋》为天子之事,故此处“舆”字疑为衍文。)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观焉。(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卷一。)
愒训为贪。《春秋》新王说,发端于孟子的《春秋》天子之事。但是,庄存与认为孟子之说,只是从孔子受天命而制作了治万世的王法而言。这个王法也就是尧舜三代的圣人之道,而不是汉代《公羊》学的王鲁说与所谓为汉制法。他在论说夏征舒弑陈灵公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卷一〇。)
在庄存与的思想中,能用来“正本”的只能是圣人之道。不仅如此,庄存与还特别强调只有君王才能改元立制,否则,就是篡杀之诛,死罪之名,“惟王者改元立号,庶邦丕享,则爵命诸侯,天子之事也云而。苟非其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不免于篡杀之诛,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因此,他解释隐公七年,滕子卒,《春秋》书“滕侯卒”,只是因为“以其子来朝,恩录其父王者,所不辞也”(同上。)。从书法说,是“贵贱不嫌者同号”,“齐亦称侯,滕亦称侯”(庄存与:《春秋举例》。),并没有《公羊》学的孔子自己改制立爵,将滕子变为滕侯之义。所以,庄存与并不把《春秋》看成改制之作,而认为是一部拨春秋之乱、反圣人之道的著作:
《春秋》考成败,录祸福,讥世卿最甚。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赐之福,其作汝用咎。以此为上帝之大禁也。(庄存与:《八卦观象解下》,第22页。)
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拨乱反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中》卷四。)
《春秋》不过是“教之孝弟”的著作,而非为所谓后王改制立法之书。所以,庄存与讲的《春秋》天子之事,不过是说孔子的《春秋》集合了尧舜三代圣王之义。他的“《春秋》制义,以继王迹”(庄存与:《春秋正辞·禁暴辞第七》卷九。),就是对此的明确说明,与《公羊》学的《春秋》是孔子为新王所立之法含义大不相同。
同时,《公羊》学的《春秋》新王说,是与黜杞、新周、故宋的三统说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休解释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就以“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为说。没有黜杞、新周、故宋,所谓《春秋》新王说就不能成立。而庄存与在论说此条时,虽罗列了《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与董仲舒、刘向诸家之说,(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卷一。)却唯独没有一点黜杞、新周、故宋的发明。因此,庄存与的《春秋》新王说与《公羊》学的说法是有根本区别的。
可见,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没有孔子素王说、王鲁说等说,虽有《春秋》新王、《春秋》天子之事之说,但与《公羊》学之义实有不同。因此,可以说《春秋正辞》基本上没有孔子改制说的发明,而晚清讲《公羊》的学者,无不以孔子改制说为其发挥理论的根据,这是庄存与虽重《公羊》而与晚清讲《公羊》者在理论上的重大不同。
这一理论上的不同,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要求社会变革、革命的理论。它在先秦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要求建立大一统的时代要求,在汉初又成为汉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依据。理论只有合乎时代需要,才能成为时代的显学。当运者王,《公羊》学所以能够在西汉取得最为显赫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此。这样一种理论,在社会变革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时代需要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以后,它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公羊》学在汉代以后两千来年虽也时有人提起,《公羊传》也一直被作为经典受到推崇,历代也有人利用孔子改制说为其寻求合法性,但是,《公羊》学在总体上却默默无闻,几成绝学,孔子改制说更没有成为时代理论的热点。只有当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已经被提出,而崭新的时代变革理论又没有出现时,《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才能再次成为社会的时髦理论,而被人利用来为社会变革作理论上的论证。
其次,从三世说、三统说来看,庄存与也只是在形式上接受了《公羊》学的说法。对三统说,庄存与将其作为“奉天辞”中的第四项内容,并在后面有所论说,但也只是引用何休、刘向之言及孔子之言予以证明,而他只是从历法、天命授受方面引用何休等人之说,丝毫不及何休等人的三统说,至于黜杞、新周、故宋的三统说,庄存与丝毫没有采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董仲舒也有三统说的专论,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庄存与论《春秋》本来是主要据董仲舒为说的,但是,庄存与却不引以为说。这是因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就是“改制”说,或者至少是与“改制”密不可分的。可见,庄存与的不引董仲舒之说,是要刻意避免“改制”之义。言三统而无三统更替的改制之义,是庄存与三统说与《公羊》学的区别所在。
而对于三世说,庄存与虽然以其为“奉天辞”的第9项内容,但在后文却没有专门的论说。他在《春秋正辞》的其他地方,也有关于三世说的言论,如于《春秋》隐公七年,释“滕侯卒”说,“滕,微国也。所闻世始书卒,所见世乃书葬,曷为于所传闻之世,称侯而书卒”(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又如“小国如曹,所传闻世已书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则书自所闻之世;如薛如许,则书以所见之世;至所见世,舍莒皆书葬矣。”(庄存与:《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卷七。)然而,这些说法只是取《公羊》学的《春秋》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及其三世不同笔法亦异之说,而根本看不到他对《公羊》学三世说最有价值的据乱、升平、太平之说的任何发明。他在论“张三世”时,似乎有这方面的含义:“据哀录隐,隆薄以恩,曲伸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卷一。)这里虽然有拨乱、升平、太平之语,但是,并没有将所传闻世三世与据乱三世相联系。从语义与语法上说,“拨乱启治”即拨乱反正之义,尔后的升平、太平不过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因此,他的拨乱启治与升平、太平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语句,而不是三世说的拨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并列递进关系。再结合庄存与其他言三世只言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无有拨乱、升平、太平三世的迹象来看,他的“张三世”根本没有“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解释三世说”(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68页。)之义,而只是说孔子在《春秋》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三世十二公中寓含的圣人之道,可以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并使人类社会进入升平、达到太平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