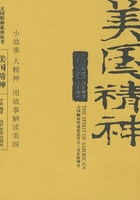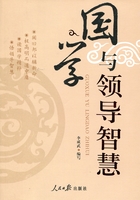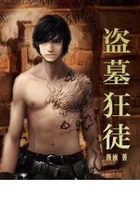這個由內廷強力支持、遭到士大夫激烈反對、以書畫辭賦作者為主構成的社會群體參與到漢末的政治鬥爭中來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一嚮為社會所輕視的“文學”及從事“文學”的“文士”,藉助“鴻都門學”這一機緣突出到政治前臺來,雖然其遭到的激烈反對說明其社會認同依然很低,但無論怎樣,他們畢竟依靠政治的強力第一次被提升到政治前沿,即使是有限度的,“鴻都門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學”及“文士”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認同度的提高。
如果說“鴻都門學”所造成的事實及影響由於其存在时间的短暫還没來得及充分展開,那麽它所引領的歷史趨勢就是由後繼的曹魏來發展完成的。曹操藉鑒了“鴻都門學”的經驗。曹操出身閹宦,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立身行事與傳統士大夫不同,基於現實及形勢,其政權的發展壯大也不得不走一條與士大夫勢力不同的發展路徑,代表閹宦勢力利益及文化傾向的一面決定了曹操對傳統士大夫勢力采取兩面政策,即利用與打壓並重。有所打壓必亦有所樹立,曹氏所樹立者,諸藝之士也,曹氏陣營對諸藝之士的吸納、搜羅形成了鮮明的態勢,其諸道求賢令的發佈正與此有莫大關係。經由曹操的大力搜羅、積極引導,“文士”已成為曹氏思想陣營中的重要成員,並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這在曹丕、曹植集團爭立太子的政治鬥爭中有集中的體現。由於曹氏“尚文辭”的策略及傾向,“文學”的“小道”色彩及意味變淡,“文學”得到重視與提升,可略攀孔氏之業。曹氏陣營“文士”會集及“尚文辭”的傾向造成了這樣的歷史影響:一、“文士”正式躋身到上層文人的行列,其身份、地位可略攀“儒士”而與之等;二、“文學”得到尊重,恃之亦可以立身,而不一定必得專依儒學,“文士”的文化品質得以提升。
與上述態勢相應,傳統文學在曹魏時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首先,文人開始積極、普遍、大規模地作詩。在漢代,來自下層的歌詩創作,文人不屑為之,而傳統以來的四言詩又因《詩經》經典化、神聖化而形成的特定“禁忌”,不好任意施為,所以造成了文人詩作很不發達的文學局面。曹魏文人打破了上述傳統,曹氏父子大量擬作樂府,帶動文人們大規模地進行五言詩創作,至此詩歌體式成為傳統文學的大宗,五言詩更是成為詩歌創作中的主流樣式,傳統文學發展面貌為之一變。其次,曹魏文學創造了文學史上第一個具有獨特風格涵義的創作樣態——“建安風骨”。其所以為歷世所推重,就在於其第一次成功地把積極的經學精神——家、國之思與強烈的個人情感以文學的方式完美地結合起來,因而在傳統文學中成為經典的創作範式,永為後世批評家所讚譽,这實際上開啟了後世文學一種基本的創作表現模態。再次,文學的核心要義——文學的“人本”精神在曹魏文學當中全面普及開來,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文學的人本精神而不是經學的教義開始成為文學最鮮明的特徵。
西晉的文學態勢繼續深入發展。西晉文學最顯著的風貌是它的“雅化”特徵,這既表現為四言詩創作的遽然增多,乃至成為上層文人創作的主流,又表現為西晉文學創作流露出鮮明的“雅”風格色調,反映了與曹魏文學迥然不同的風貌特徵。西晉文學這一風貌特徵的出現有特定的社會歷史原因。與自身集團的文化趣向密切相關,曹氏集團最鮮明的文化傾向是“尚文辭”,通過政權及骨幹成員的長期經營,重“文辭”已在社會上鋪衍開來,成為人們逐漸接受的社會存在事實。代表經學士大夫勢力的司馬氏代魏,必定会有一個對曹氏文化趣向予以顛覆、進行改轍的過程,從而反映並強調自己勢力集團的文化傾向及利益。故針對曹氏文化偏重“世俗”的傾向,司馬氏以“雅化”改造之,這一舉動在司馬氏立國之後政策的調整、日常文學活動中來自宮廷的垂範、上層文人創作當中的自覺認同、文學批評之中的總結與推闡等方面清晰可見。西晉文學“雅化”導致的創作成績雖歷來頗遭詬病,不過這一舉動仍有它特殊的歷史意義,如果說曹氏父子兄弟的提倡對曹魏文學發生實質性變化起了關鍵性作用,那麽來自司馬氏政權的影響對西晉文學的深入、普及發展同樣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如果說曹魏時期上層文人中“文士”與“儒士”還是明顯兩分的話,那麽西晉時期這一界限已模糊不清,“作詩”成了幾乎所有上層文人的普遍行為,這衹要翻檢一下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便一目瞭然。西晉文學的“雅化”事蹟也意味着文學發展的深入化、普及化,這不能不說得益於上層統治者的推動。而文學的深入、普及,又構成了下階段文學新進程的發生前提。
東晉最突出的文學事實是玄言、山水、田園詩的出現,它們的興起都與玄學密切相關。玄學從曹魏後期開始,漸趨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玄言詩可以說是用文學反映玄學的結果。用文學對主流思想進行表達,此前衹在經學身上發生過,不過經學“大一統”時期,文學尚不大有資格對經學進行深度介入,此次以較為獨立、自主的姿態對主流思想介入表達,玄言詩可稱為第一次,它反映了文學進程的某些重大信息。山水田園詩是玄言詩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如果說玄言詩還側重於以“理說”的方式“言道”,那麽山水田園詩主要是通過具體的山水田園物象來以“意會”“悟道”,這中間引入了“物象”、“境象”的要素;而且,山水既然“以形媚道”,那麽由“形”到“道”之間的參悟又強調指向主體內心之所感,因而最終指向個體對自然生息之意的體悟、對人與自然冥合精神境界的追求。如果說曹魏及西晉的文學還深深地受着經學精神或經學規範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本书把這一類型的文學稱為“經學模式”的文學,那麽東晉文學則更多地表現為受道家思想影響——與“經學模式”相對,暫稱之為“道家模式”的文學。前者的成熟模態以“建安風骨”為代表,其體現着儒家積極的濟世情懷,往往蘊含着強烈的家、國之思,反映着作者的社會、天下意識;後者更多地反映着個體擺脫世俗羈累、追求澄靜適意的自我情懷,其理想的、適宜的方式就是通過山水田園文學觀照、靜求、體悟個體的內在精神世界,以求與自然化合、融通。一動一靜、一“入”一“出”、一外在一內在、一積極一自守構成了文學精神的兩種基本表現模態。
應該說,到了東晉,傳統文學基本的表現樣態及精神內涵都已大致確定下來了,後世的文學發展,無論表現出怎樣的成熟面貌,但就基礎的表現模態而言,並没有超出上述的兩種範式。
兩晉文學的成熟發展要求人們對之予以確認。首先是“文才”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甚至可以與玄談能力一道成為“名士”的重要文化素養。當然,兩晉時期對文學予以確認的最大也是最實質的舉動,是“四部”分類的確定。“四部”分類的成立,以文學的充分發展為前提(本书僅就文學而言)。《七略》或《漢書·藝文志》中的“詩賦略”尚鮮明地體現着以經義為剖判的內在邏輯,其仍是經學“大一統”之下的臣民;《中經新簿》及《晉元帝四部書目》中的“四部”,其“甲”、“乙”、“丙”、“丁”之目或亦有主次、輕重之分,不過四部類之間更大的意義在於四者獨立分列,而不再體現某部“含有”或“統馭”别部之意。
“四部”分立的歷史意義非同凡響。傳統文化嚮“道”的體性使各文化類别以向“道”皈依為終極指向。在傳統文化中,“道”具有抽象的終極所指,不過先人們似乎並不汲汲於對抽象的“道”的追索,諸家紛紛所言之“道”並不抽象,而是直接指向現實的“治道”,所以傳統文化現實功用的色彩非常濃厚。漢代“獨尊儒術”,儒家之“道”成為現實政治的指導術是傳統文化“道用”觀念最集中的反映,後世言“用”述“道”多與現實關懷聯繫在一起,这正與傳統及漢代奠定下來的文化傳統有關。傳統中早期的文化類别區分與後世所謂的“目錄學”並不是一回事,主要文化類别的劃分與成立,通常與這一文化類别的功能及其在現實中的應用情況密切相關——“經”、“史”、“子”、“集”之分無不是這一觀念滲透下的結果,所以雖都是客觀的文化存在,卻在社會現實當中具有高下之分、尊卑之别。傳統文化的這一內在規定及現實社會中實際的取用要求,使“文學”這一以娛心悅志為基本特徵、頗與現實功用相妨的文化類别,頗受政治主流人士排斥。從這一角度講,傳統文學史上存在着一個“文學自覺”的歷程是成立的,也是必然的,這是由傳統文化的基本特性決定的。文學獨立地以自身體性进行自足的發展,必定要經過一個逐漸脫去文化層累在其身上的諸多附加因素而逐渐純化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並不衹表現為對外在因素的剔除,或者說更重要的還是文學要在遵循傳統文化基本特性的規定、並在發展中融會這一特性從而形成自身特徵的邏輯中完成自身的自足發展。這一過程經過漢末曹魏的推動發展,到兩晉時期已基本確定和完成了,後世文學發展的基本格局在兩晉時期已基本定型。從外在來看,“經”、“史”、“子”、“集”四部類趨於分化獨立,“集部”得到確認;從內在來講,“經”、“史”、“子”、“集”的文化結構模式開始形成,“經”、“史”、“子”、“集”不僅僅體現了文化部類的分化,也是人們文化知識結構的實際劃分與形象說明,從此之後,四部類內容開始在人們的知識結構中融會(這衹是相對而言,並不是說此前人們的文化知識結構中就没有這樣的文化內容或構成,不過人們一般習慣於抓住具有標誌性的特徵來言說事物,故這裏如是說。),其中尤以“經”、“文”兩方面最為突出,傳統的士人無不受“經學”的影響,而又幾乎普遍性地“擅文”,這固然與唐宋之際科舉以“經”和“詩賦”取士的現實有關,但如果就這一傾向出現的苗頭與實際事實来看,兩晉不能不說是其奠基時期。
綜合上述情況,可以說“文學”在漢末魏晉時期走向了“自覺”。言其“自覺”有這樣幾個重要標誌:一、文才”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成為人們顯示才華、恃以驕人的重要文化素養;二、全社會都普遍地參與文學創作,文學成為一種社會普及的文化內容及文藝樣式;三、文學的基本表現模態趨於定型;四、社會基本的文化類别劃分、人們基本的文化結構的構成內容初步確定,文學成為其中重要而穩定的成分,後世文學處身其中、賴以生存發展的整體文化格局基本穩定。具有以上特徵或標準的文學發展纔稱得上是“自覺”了,唯有如此,“文學”纔可能真正走上“自覺”的發展道路。至於說文學作品的抒情性增強、文學的審美性增加、五言詩創作興盛、人的生命意識覺醒、文學理論大量出現等,確實可以說是重要的文學變化,但與其說這些是“文學自覺”的決定要素,不如說它們衹是“文學”在走向“自覺”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某些表象變化,並不能充分顯示或代表“文學自覺”進程的一些基本環節。